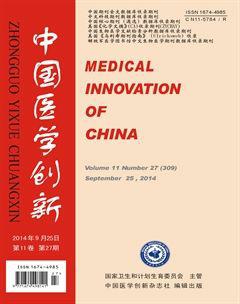冠狀動脈心肌橋的臨床診療與分析
王松濤 竇克非 張彬 常瑜 李獻良 梁磊 姜先雁 崔美平 蔣文彬 張慧 路長鴻
【摘要】 目的:探討冠狀動脈心肌橋的臨床診斷及治療。方法:對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接受冠脈造影的1506例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均采用右側橈動脈穿刺途徑行選擇性冠脈造影。結果:共檢出心肌橋54例,檢出率為3.6%,均位于前降支。46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胸悶、胸痛,5例以心悸為首發癥狀就診,2例因查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就診,25例心電圖有靜息狀態下ST-T改變。53例患者選擇藥物治療,僅1例行外科肌橋松解術,所有患者隨訪癥狀均明顯緩解。結論:冠狀動脈肌橋多發于前降支,可導致胸悶、心悸等臨床癥狀,治療上可用β受體阻滯劑和/或非二氫吡啶類鈣離子拮抗劑,嚴重者可選用支架植入術或外科肌橋松解術。
【關鍵詞】 心肌橋; 冠狀動脈造影; 臨床診療
冠狀動脈心肌橋(心肌橋)是一種先天性冠狀動脈發育異常。臨床中,肌橋患者大部分無明顯癥狀,僅有少部分患者有胸悶、胸痛、心律失常等表現,與冠心病鑒別困難,較容易被誤診、漏診。近年來,隨著冠狀動脈造影的廣泛開展,心肌橋的檢出率不斷增加,其臨床意義也越來越受到關注。本文回顧性分析了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接受冠狀動脈造影的1506例患者病例資料,對其中檢出的54例心肌橋病例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心內科共完成冠狀動脈造影1506例,其中檢出心肌橋患者54例,檢出率3.6%。患者年齡37~72歲,平均(57.6±8.7)歲;其中男38例(70.4%),女16例(29.6%)。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經右側橈動脈穿刺途徑進行冠狀動脈造影。左冠狀動脈常規采用蜘蛛位(左前斜45°,足位30°)、左肩位(左前斜45°,頭位30°)、頭位(正頭位30°)、右肩位(右前斜30°,頭位30°)、肝位(右前斜30°,足位30°)5個投照體位。右冠狀動脈造影常采用左前斜45°、右前斜30° 2個投照體位。以造影劑充盈冠狀動脈3個心動周期作為判斷,懷疑冠狀動脈痙攣者經造影導管推注硝酸甘油100~200 ?g后,重復造影予以排除。
1.3 肌橋的診斷標準 至少一個投照體位發現冠脈于收縮期管徑狹窄,而舒張期管徑正常,呈“擠奶效應”(milking effect),診斷為心肌橋。根據收縮期狹窄程度Nobel等方法將心肌橋分為3級:1級收縮期狹窄<50%,2級收縮期狹窄50%~75%,3級收縮期狹窄>75%。
1.4 治療方法 有10例因癥狀輕微,僅給予阿司匹林口服;34例給予β受體阻滯劑聯合阿司匹林治療;4例采用了β受體阻滯劑加鈣離子拮抗劑,聯合阿司匹林治療;5例采用阿司匹林聯合鈣離子拮抗劑治療;1例行肌橋松解術。所有患者均進行隨訪6個月。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1506例患者中檢出心肌橋54例,檢出率3.6%。所檢出的肌橋均位于前降支,其中位于前降支中段的51例(94.4%),位于前降支遠段的3例(5.5%)。Nobel分級:1級狹窄16例(29.6%),2級狹窄22例(40.7%),3級狹窄16例(29.6%)。肌橋長度5~23 mm,平均(12±5.2)mm。造影合并冠心病的18例(33.3%),其中單支病變13例(24.1%),雙支病變4例(7.4%),多支病變1例(1.9%);合并瓣膜病2例(3.7%);造影完全正常34例(63.0%)。
2.2 臨床表現 46例(85.2%)心肌橋患者因發作性不同程度的胸悶,胸痛而就診;5例(9.3%)以心悸為首發癥狀就診;2例(3.7%)因查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就診;1例(1.9%)患者因突發暈厥就診。其中合并高血壓病患者32例(59.3%),合并糖尿病者7例(13.0%),合并血脂異常者34例(63.0%)。
2.3 心電圖特點 所有患者均行心電圖檢查,其中25例(46.3%)靜息狀態下心電圖有ST-T改變,7例(13.0%)表現為T波改變,合并房性早搏或室性早搏各3例(5.6%),合并永久性房顫者2例(3.7%),陣發性房顫者1例(1.9%),1例合并有短陣室速(1.9%),2例合并完全性右束支傳導阻滯(3.7%),1例合并I°房室傳導阻滯(1.9%)。
2.4 超聲心電圖特點 所有患者均行超聲心動圖檢查,其中33例(61.1%)未見明顯異常,19例(35.2%)患者合并舒張功能不全,5例(9.3%)合并室壁運動異常,2例(3.7%)合并心肌肥厚,2例合并不同程度的瓣膜病變(3.7%)。
2.5 隨訪結果 所有患者均隨訪6個月,全組無死亡,所有患者胸痛癥狀明顯緩解。
3 討論
冠狀動脈心肌橋是指冠脈某一段或其分支的某一段走行于心肌纖維中,被形似橋的心肌纖維所覆蓋,在心臟收縮時出現暫時性管腔狹窄甚至閉塞,該心肌纖維束稱為冠狀動脈心肌橋(簡稱心肌橋,myocardial bridging,MB),而穿行于該段心肌下的冠脈稱作壁冠狀動脈,也叫隧道動脈[1]。MB的影像學表現為該節段舒張期造影顯示無異常,而收縮期漸進性縮窄,顯示表現不清,即所謂的“擠奶效應”[2]。因此,MB解剖學上表現為冠狀動脈走形的先天異常,其在冠造中約0.5%~16%被發現,在尸檢中有5.4%~85.7%被發現[3]。本組患者檢出率3.6%,與文獻報道一致。
由于MB的位置和解剖結構的特殊性,導致嚴重的心血管事件不斷被發現,因此,近年來認為MB并非是一種良性病變[4-5]。有學者將肌橋分成2型,分別為“表淺型”(主要走行于室間溝內)和“縱深型”(主要走行于靠近右心室的室間隔內)[6]。冠脈血管被表淺型MB壓迫的程度小,因此心急缺血的程度不嚴重;而縱深型MB可扭曲前降支血管,影響收縮期同時,可使舒張早、中期的血流減少,從而顯著減少冠脈的血流儲備。心臟收縮力的增強加重了對MB的壓迫,同時也增加了心臟負荷。隨之引起心率增快,舒張時限縮短,心肌灌注時間減少,最終導致心肌缺血。壁冠狀動脈較其他血管更容易發生痙攣與之反復受壓或扭曲有關;而其近段多發動脈粥樣硬化的機制可能與其近段血流動力學紊亂有關。急性冠脈綜合癥(ACS)即是在上訴基礎上發生的斑塊破裂、出血及血栓形成和血管痙攣。總之,MB引起心絞痛、心肌梗死、各種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等心血管事件有多種途徑。目前臨床上診斷MB主要依據冠脈造影和血管內超聲檢查。以下幾個方面決定了冠脈造影是否能使MB清楚的顯影:(1)MB的厚度、寬度和走形的長度;(2)MB與壁冠狀動脈等關系,特別與包裹它的結締組織或脂肪組織的多少有關;(3)對藥物的影響,如血管擴張劑或收縮劑;(4)患者體位及術者等經驗等[7-10]。有時還需要將硝酸甘油類藥物注入冠狀動脈內才能發現。本組患者中既有46例(85.2%)發作性不同程度的胸悶、胸痛而就診,另外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其他器質性心臟病,臨床表現較為復雜。endprint
無臨床癥狀的MB目前認為無需干預治療,合并有臨床癥狀,狹窄較重的患者可酌情采用藥物保守治療、內科介入治療或外科手術治療,其中前者在臨床中更多被選擇。目前,治療MB常用的藥物有β受體阻滯劑(β-blockers)、鈣離子拮抗劑、抗血小板聚集藥物等。β-blockers具有負性肌力及負性變頻作用。負性肌力作用能減輕MB對壁冠狀動脈血管的壓迫作用;而負性變頻作用可減慢心率,延長舒張時限,大大增加冠脈血流儲備,從而達到改善臨床癥狀的目的。對于不能使用β-blockers或存在血管痙攣的患者,首選非二氫吡啶類鈣離子拮抗劑,同樣可以達到使心肌收縮力下降,改善冠脈痙攣,延長舒張時限,抗缺血的目的,因此,它被認為是治療MB的另一特效藥物。另外,由于MB內冠狀動脈血管經常受到擠壓,內皮細胞比較容易受損,這使得局灶性血栓素β2水平上升,可導致血小板的激活進而血栓形成,因此諸如阿斯匹靈等抗血小板藥物的使用可防止血栓形成[11-12]。
經過藥物治療后仍有癥狀,Nobel分級收縮期狹窄>75%,臨床有明確心肌缺血客觀證據者,可行經皮冠狀動脈內支架植入術(PCI)或心外科手術治療。通常選用比較柔韌且具有較強支撐力的支架,而藥物洗脫支架(DES)被認為或許可使遠期再狹窄率降低[13-14]。但由于MB的擠壓作用使得支架容易被擠壓破裂,因此再狹窄率高。而心外科手術治療MB的方法主要有2種:肌橋松解術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經心外膜超聲常被用在術中來定位MB和壁冠狀動脈。但心肌橋松解術風險較大,因為冠狀動脈在肌橋內的走形是不可視的,有時需要切開較深的心室肌,可能會導致冠狀動脈受損、心臟破裂、術后室壁瘤形成等風險。術后襲擊瘢痕形成也可以重新壓迫冠狀動脈,因此應認真權衡術后風險,嚴格掌握手術指征[15]。如壁冠狀動脈近段存在固定狹窄、有典型臨床癥狀者,選擇CABG可避免松解術導致的斑塊不穩定等不良合并癥。
總之,心肌橋的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故容易被誤診而使病情延誤甚至加重惡化,尤其在有冠心病易患因素的中老年人群中。因此臨床上如患者出現心絞痛癥狀而常規的治療方案效果欠佳時,應考慮到心肌橋的可能,此時應及時行冠脈造影檢查,明確診斷,給出及時正確的治療。
參考文獻
[1]馬小林,李鎮,章敬水,等.28例冠狀動脈肌橋患者的冠脈造影特征分析[J].遼寧醫學院學報,2013,34(2):49-50.
[2]劉春光,王穎.多排螺旋CT冠脈成像、心電圖及冠狀動脈造影對冠心病臨床診斷價值的對比分析[J].中國醫學創新,2013,10(5):98-99.
[3]Mohlenkamp S,Hort W,Ge J,et al.Update on myocardial bridging[J].Circulation,2002,106(12):2616-2622.
[4]Ferreira A G,Trotter S E,Konig B,et al.Myocardial bridges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J].Br Heart J,1991,66(5):364-367.
[5]馮仕勇,許勇.冠狀動脈心肌橋與急性心肌梗死關系的初步探討[J].山東醫藥,2011,13(11):332.
[6]李玲,朱文玲.冠狀動脈心肌橋研究進展[J].北京醫學,2006,28(7):437-439.
[7]戶學敏,朱坤,許乘志,等.冠狀動脈肌橋12例臨床分析[J].中華全科醫學,2009,7(9):967-968.
[8]劉文旭,李治安,楊婭,等.經胸彩色多普勒冠狀動脈血流顯像技術對冠狀動脈前降支心肌橋的初步研究[J].中華超聲影像學雜志,2006,15(9):646-650.
[9]楊帆,寧新惠,向小平.64層螺旋CT冠狀動脈血管成像診斷冠脈支架內再狹窄的臨床價值[J].中國醫學創新,2012,9(27):142-143.
[10]劉衛金,戚躍勇,鄒利光,等.心肌橋的冠狀動脈造影影像特征及臨床意義[J].第三軍醫大學學報,2002,24(6):696-698.
[11] Bourassa M G,Butnaru A,Lesperance J,et al.Symptomatic myocardial bridges:overview of ischem ic mechanisms and current diagnotic and treatments strategies[J].J Am CoLL Cardiol,2003,41(6):351-359.
[12] Ng E,Jilaihaw I H,Gershlick A H.Symptomatic myocardial bridginga niche indication for drug-eluting stents[J].Int J Cardiol,2005,99(11):463-464.
[13] Soran O,Pamjr G,Erol C,et a1.The incid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myoeardial bridge in a prospectively defined popula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coronary angriographyfor chest pain[J].Tokai J B Clkn Ned,2000,25,(2):57-60.
[14]戴汝平,支愛華.提高對冠狀動脈肌橋及其臨床意義的認識[J].中國循環雜志,2007,22(5):321-322.
[15]陳勁進,肖穎彬,陳林,等.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治療冠狀動脈肌橋9例分析[J].局解手術學雜志,2011,20(5):486-487.
(收稿日期:2014-05-21) (本文編輯:蔡元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