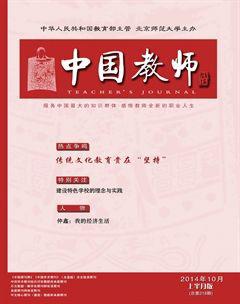徐梓: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增進傳統文化的興趣,提高傳統文化的素養
傳統文化教育貴在“堅持”
編者按: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數千年沉淀下來的精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且愈益勃發的力量源泉。國家提出要重視傳統文化教育,本期《熱點爭鳴》特邀多年來一直從事傳統文化教育與傳統文化研究的學者、教授與一線教師,聚焦于傳統文化教育的價值進行探討,以期廣大教師對傳統文化教育有更為全面與深入的認識,從而在自身的課堂教學中借鑒。
《中國教師》: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各種思想文化與觀念形態的歷史積淀,一脈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理應在各個時期都得到重視,但為什么當前我們要突出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您認為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徐梓: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社會方面的原因,又有學術方面的原因。作為一名學者,我將政治、社會方面的原因歸結為外部原因,學術原因歸結為內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百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充當了經濟落后的“替罪羊”,主流意識形態對我們的傳統文化采取的是鄙薄、仇視和批判的立場。針對這一情況,有人說“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挖出了自己的心,用自己的雙手割斷了自己的臍帶”。從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破四舊”,可以說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做得這樣決絕,和自己的傳統過不去,和自己的祖宗過不去。我們一直是在激烈地反傳統,將我們現在生活的不如意歸罪于我們的傳統,把我們今人的不作為諉過于我們的祖宗,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出在傳統的“根”上,是傳統文化造成我們近代的屈辱和現今的種種不如意。然而,20世紀60、70年代,屬于漢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興起,特別是改革開放的30多年間,我國經濟大踏步式地高速增長,躍居到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這時,我們發現將經濟落后歸罪于傳統文化的外部條件消失了,激烈地反傳統實在過于魯莽,因而很多人開始對傳統文化有一種溫情與敬意,也就是勢所必然。
第二,持續地、極端地、無條件地反傳統,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種植下這樣一種意識,那就是傳統文化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是現代文明的絆腳石。在這樣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下,傳統文化的價值被完全否定,傳統文化的地位被徹底貶斥,傳統文化的面貌被全盤抹黑,造成傳統文化的花果飄零,后繼乏人,以至于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無論擁護還是反對國學教育,大都沒有多少傳統文化的素養可言,很多人甚至連祖國語言也不能有效地使用。現在,我們提出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出于彌補百年來激烈地反傳統所造成的鴻溝和傳統文化的斷裂。
第三,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并逐漸深入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進入了轉型時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現今中國社會轉型的速度、廣度、深度、難度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深層處的變化派生出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一方面,舊有的社會規范對很多人已經失去控制力,但還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另一方面,新的社會規范正在建立,但尚未得到普遍認可。在這種情勢下,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城鄉之間乃至醫患之間的各種社會沖突經常發生,政治上的行賄受賄、貪污腐敗、濫用職權,經濟上的制假造假、弄虛作假、欺瞞詐騙,道德上的不孝父母、見義不為、見死不救等社會失范現象頻發。要想解決當今社會的亂象,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就有必要為各行各業的人們奠定一個共同的文化基礎,確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立足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人們才有共同的價值和規范,有共同的愿景和追求。而這個基礎中最能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的,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或者說,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
第四,科技,特別是通信領域科技的迅速進步,使得經濟全球化或世界一體化已初現端倪,各個國家的開放、各個民族文化的交流,更成為不可逆轉之勢。而且,我們要認識到,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多元化之間并不必然是對立的關系。相反,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世界的一體化,正在于民族的多樣化。如果全球化的終極指向是各民族文化的完全一致,那將是可怕的。每一種文化都是在應對自然、社會環境挑戰時人類獨特性、創造性智慧的體現,都有存在的理由和獨特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尊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認識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內涵的“文化自尊”,與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尊重其他文化多樣性的“文化尊重”同樣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國家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豐富遺存,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如果我們只是向外國學習,從國外引進,而沒有文化的傳播和民族文化的貢獻,兩手空空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是與我們的悠久歷史、豐富遺存和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美國化,可以不顧歷史文化傳統,也可以不顧現實環境而推廣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是一種其他文明都必須降服的主流文明,中國靠上去、貼近它、融入其中就行了的看法,不僅是對民族文化獨特價值的放棄,更是對這種獨特價值內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價值的放棄。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表達出我們民族對人類文明應該也能夠作出貢獻的心聲。
從學術方面來說,我認為傳統文化主要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經典文本、文化知識和技能技藝。對教育而言,就是要教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內容。那什么樣的知識對我們來說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呢?在我看來,就是各個民族,并且首當其沖的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經典。因為民族文化的經典是那些歷史上具有最聰慧的頭腦、最偉大心靈的人們的產物,是他們智慧的結晶。《四書五經》的內容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今天依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國學經典教育就是最優質、最有價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是通識教育,是人文教育,是素質教育,而且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和不二法門。我在演講中經常強調這樣的一個觀點:通過傳統文化教育,才能使我們的后代掌握優雅、精致的祖國語言,成為一個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才能使我們的后代走進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親近、認同這個家園,并有能力參與到這個家園的建設過程之中;才能讓我們的后代將自己生命的根須,扎植于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把自己從一個自然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中國人,變成一個自覺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
《中國教師》:在教育領域,您認為我國傳統文化怎樣教學才能充分體現其價值?
徐梓:無論在大、中、小學,我認為經典誦讀就很值得提倡。根據甘陽先生的說法,美國的通識教育有兩門核心課程,一是人類文明,二是經典研讀。人類文明課程會講述世界各個民族的歷史,而經典研讀課程則是對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羅蒂等人的一系列經典原著的研讀。作為中國人與中國學生,我們有必要學習我們民族的經典,即國學經典。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但要學習民族文化、國學經典,而且也要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經典。就我個人而言,我對西方的文化也很感興趣,平時主要讀兩種書,一種是外國人的著述,一種是古代典籍。
我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還可以體現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對大學的通識教育,有很多人在探索,有多種模式,我贊同甘陽等人的一些說法與做法,如我們不能將通識教育完全變成概論式的(如“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等),流于表面。我認為有必要從經典入手,甚至一部經典可以開設成一門課程,能夠上一個學期。10多年了,我一直在學校給學生上一門公共選修課——傳統蒙學與傳統文化,就是將蒙學讀物作為一扇了解各個時期文化風貌的窗口,從最初的《史籀篇》、《倉頡篇》,一直講到后來的《弟子規》、《教兒經》。這樣做雖然能讓學生了解啟蒙教材發展的階段及階段性特征,了解其各種類型,但還是太散,不聚焦。如果就其中的某一個文本,比如《幼學瓊林》,進行專門的講授,講授一個學期,傳統文化的價值或許會更加凸顯。
《中國教師》: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經典誦讀”的培訓班或“讀經”活動,您是怎樣看待這種現象的,您認為這對學校教育工作會產生哪些影響?
徐梓:體制外的私塾和書院的“讀經”活動,應該說對當代的傳統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功勞和貢獻。這項活動從20世紀90年代前期一直持續到現在,已有20多年。對此,我們要了解它們為什么會出現,為什么家長不將自己的孩子送到體制內的學校,而是送到體制外的私塾和書院。許多家長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當前我們體制內的學校不能滿足他們的教育需求,或者說,他們對我們的學校教育很失望。我曾經說過這么一段話,傳統文化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們的民間力量在努力,是廣大的家長們在努力。它表達的是家長們對現行教育改革失望之后的一種無奈之舉,是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家長們的一種自救與自助。
然而,這些體制外的教育機構,也的確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沒有一個整體的擘劃,沒有科學的設計,易于出現跟風、攀比的情況,學習的計劃性和連續性不強,不能循序漸進和按部就班地實施教育活動。另外,還會出現低俗化的情況。一些培訓班會迎合社會上一些人的需要或興趣,以占卜、算命、風水、測字等為主要的培訓內容。還有功利化的問題,為了賺錢,傳統文化教育的功能被無限地夸大,并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向社會宣示和傳播。這不僅會給國學教育的健康發展埋下隱患,而且還對當前的國學教育造成嚴重的傷害。
體制外的私塾和書院之所以有市場,主要是因為在學校教育中,傳統文化教育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分量嚴重不足。所有的家長都想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優質的教育,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得到好的文化營養,但當前我們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應試教育的機器,而有些家長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為考試的工具,希望他們能夠真正地學到一些最有價值的東西。面對這種情況,要辦好人民群眾滿意的教育,滿足家長個性化的教育需求,我認為有必要改變一些現行的做法。比如,一方面,允許那些存在時間長、有影響,主辦者又有良好教育理念的私塾、書院存在,使其合法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送其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但與此同時又規定:“自行實施義務教育的,應當經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可見,我國的法律并沒有堵死自行實施義務教育之路,只不過是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批準。要給予它們一定的自主權,尊重其辦學傳統,在收費標準、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師聘任等方面,不必與體制內的學校強求一致。另一方面,學校教育應加大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設置專門的課程,這也是我一直在提倡和推廣的。但直到現在,全國只有山東省將其納入了必修課程,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教育現在主要還處于校本課程的層次,最多也只是屬于地方課程。
《中國教師》:一些學校會將《四書五經》、《弟子規》等國學經典帶進課堂,您是如何看待“國學經典進課堂”這一現象的,您認為這些活動會給學生產生怎樣的影響?
徐梓:我認為這很有必要,但現行的做法也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我認為問題的焦點不在于經典該不該進課堂,而是什么樣的經典、什么時候進入課堂,教的對象和學的主體是誰這樣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如何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學習相應內容的問題。這里,我堅持兩個基本的原則,一是不主張學習倫理道德色彩過于厚重的內容,如《二十四孝》,二是不贊同孩子們過早地接觸一些狹義的儒家經典,如《周易》、《尚書》等。我認為,應該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主要學習那些知識性強、具有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內容,如《聲律啟蒙》、《幼學瓊林》等啟蒙讀物和唐詩、宋詞等。
傳統文化教育的內容組織和設計一定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這是被傳統教育證實了的行之有效的一項原則,這一傳統甚至比讀經的傳統還要悠久,因而也被歷來的教育家所強調。此外,要遵從古代知識之間的內在邏輯,注意完整性和系統性。在小學一、二年級時,學生可以學習《弟子規》、《小兒語》和關于兒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內容,養成他們良好的行為習慣。到了三年級以后,可以讀《三字經》、《聲律啟蒙》、《幼學瓊林》、《千字文》等。在小學階段,學生在各個年齡段都要讀一定的唐詩、宋詞。在初中階段,學生可以讀《四書》,是選讀而非全讀,到高中階段,可以選讀《五經》。這是我對經典誦讀所做的一個基本勾畫。或者說,在小學階段,學生閱讀的內容是蒙書、唐詩、宋詞,到了初中可以選讀《四書》,到了高中可以選讀《五經》。對大學生而言,則是要帶有研究性的學習,而且內容更加廣泛,除唐詩宋詞、《四書五經》之外,還要閱讀各種史書、諸子百家,著名學者或者著名文學家的文集等。
國學經典進課堂,我認為對學生素質的優化會有很大的幫助。比如,國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的學生掌握優雅、精致的祖國語言,成為一個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我國傳統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培養所謂的“君子”。傳統文化中的經典文本,大都有厚重的倫理色彩,有很強的道德說教,反復誦讀,引歸身受,確實可以強化學生的道德意識,加強自我約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國學經典教育也可以培養學生掌握和靈活應用優雅、精致的祖國語言。以蒙書為例,“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給人們一種很壯闊的氣勢,誦讀之際,可以培養人們的氣勢與氣韻。《千字文》只有短短的1 000個字,內在結構非常嚴謹,氣勢宏大,語言精致。它1 000字不多不少,也不重復,四字一句,押韻便讀,不能是文字的簡單堆積,而要表達一定的意義。可以說編《千字文》是“舞霓裳于寸木”,在一寸見方的木頭上,跳幅度很大的霓裳羽衣舞;“抽長絮于亂絲”,在一堆紛亂的絲中,將一根絲線抽得很長很長。在這里,我們可以體味到祖國語言的優雅與精致,感受其氣勢的宏大。再比如,《幼學瓊林》中有“疇昔、曩者,俱前日之謂;黎明、昧爽,皆將曙之時”,當我們在閱讀歷史文獻時,就會發現它的價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開篇說:“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在讀完《幼學瓊林》后,我們知道“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就會對歷史文獻有一個較好的理解。因此,即便是誦讀一些蒙學讀物,也可以掌握和靈活地運用祖國語言,感受漢語的氣勢和氣韻,可以自如地駕馭漢語,可以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所以我常說,當我們將高度凝練、爺爺輩的文言文掌握后,淺顯通俗、孫子輩的白話文就不在話下。
《中國教師》:您能談談當前學校校本教材的建設與傳統文化教育結合的情況嗎?
徐梓:我主編過一套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學教材,現在有很多的學校將它作為校本課程的教材在使用。但校本教材的開發,如果沒有特定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的參與,那也不具有校本教材的特質。如果校本教材面向全國,面向所有的學校,就會失去它作為校本教材的意義。校本教材要以學校為本位,由特定的學校自己確定,要有很鮮明的個性和特色。
現在,我正在和北京海淀區上莊學區的校長和教師合作,共同編寫一套《家訓與家風》的校本教材。《家訓與家風》校本教材分上、下兩冊,上冊主要講家及修身之要,下冊主要講家族與齊家之道,從社會的細胞——家、家族講起,再講個人修身,講治家原則。在設計德目時,既注重傳統的美德,也參照西方與現代的道德,并將中國傳統的家訓和古典文本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有關的知識與詩歌編入這部教材。根據上莊學區的計劃,這部《家訓與家風》的教材不但學生要讀,家長也要讀,以形成家校合力。在活動課環節,我們還設計了讓學生根據傳統的家訓,針對自家的實情,自己編制家訓,讓自己和爸爸媽媽共同遵守。此外,還有一些學校在和我聯系,希望我協助他們編輯《中華傳統美德》之類的校本教材。我舉這些例子是要說明,傳統文化在校本教材的開發與建設中大有用武之地。
《中國教師》:語文教學是傳播傳統文化的主渠道,您認為語文教師在開展傳統文化教育方面應該注意什么問題?
徐梓:在現階段,語文課確實是體制內學校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但靠這種滲透的方式,依然達不到傳統文化教育的目的。所以,我主張將中華傳統文化單獨設科。就當前的情況來說,除了在語文課中加大傳統文化內容的比重外,再就是要加強語文教師的培訓,使他們從偏重白話文教學,進而有能力從事文言文教學;從主要講述表淺的知識,轉向知識背后文化意蘊的挖掘。
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練、意蘊豐厚的文言文,而進入民國后,我們強調直觀教學,在啟蒙教育階段教給學生的主要是“小鳥飛,小狗叫,小兒追,小狗逃”、“大公雞,喔喔叫,小朋友,起床了”之類的內容,這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相比較,顯然人文意蘊淡薄,就像白開水一樣,王財貴先生形象地稱這樣的內容是有知識沒文化。我和一位老師曾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海外聽眾講《千字文》,1 000個字,足足講了40講,每一講要近半個小時,這是因為它具有豐富的人文意蘊可以挖掘,才可以講解這么長的時間。語文教師在教學時,不能單純地讓學生背誦和記憶,也不能只是解釋其表層意思,而是要盡可能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蘊。
此外,語文教師要特別注意孩子興趣的培養,利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和方法,讓學生對古代的文本產生興趣,而任何單純的背誦和機械的記憶都會讓他們對這些文本有畏懼感。教師除了適當的講解之外,還要通過一些別的方式,如與經典文本切近的故事、能夠啟發學生形象思維的詩歌,增加學生對經典的理解和認識,增進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我認為這是語文教師要特別注意的內容。
《中國教師》:那么對普通科任教師來說,他們應如何在自己所任科目中滲透中國傳統文化?
徐梓:每個學科、每門課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將其功能泛化,泛化之后,其自身的功能可能就發揮不了了。在現階段,在傳統文化還沒有單獨設科之前,在各個學科中加大傳統文化的比重,是一種可取的做法。比如說,很多學校會在綜合實踐課中,帶學生去學校周邊開展調查,參觀名勝古跡或名人故居,希望通過這些活動讓孩子進一步了解這些古跡的歷史,了解名人的成就,這也是傳統文化教育比較重要的方面。再比如說,一些體育課,也有諸如踢毽子、放風箏等兒童傳統游藝的內容。通過這些活動,可以滲透或體現傳統文化,但要想通過這種偶爾的“體現”、零星的“滲透”來實現傳統文化教育的目標,這是遠遠不夠的。我不是說這些課的任課教師做得不好,而是說他們有自己特有的功能,要著力于自己的主要目標,不能也不應該舍本逐末,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本來不屬于本課的任務上。
《中國教師》:您對傳統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語?
徐梓:我現在從事傳統文化教育,一直以實現這樣的目標為己任,就是想讓人們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增進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提高傳統文化的素養,這可以權作我對《中國教師》讀者的寄語吧。
(責任編輯: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