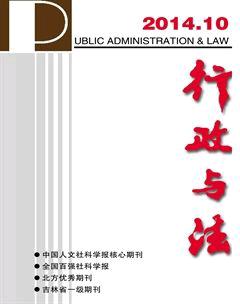民主鞏固與國家能力
袁則文
摘 要:在近代以來的多次民主化浪潮中,除少數國家之外,多數國家的民主轉型和民主化進程都是一波三折,民主鞏固艱難。其原因固然眾多,但缺少應對和解決民主化進程中所面對的一系列問題的國家能力顯然是其中非常關鍵的因素。本文認為,新民主政權只有有效解決轉型問題、控制轉型秩序、提升民主質量、促進民主文化形成,才能保障民主轉型,走向民主鞏固。
關 鍵 詞:民主鞏固;國家能力;民主化進程
中圖分類號:D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10-0011-06
民主化已成為當今世界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自19世紀初以來,世界已掀起至少三波民主化浪潮。但除了少數國家較為成功之外,多數國家(特別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曲折反復,不僅未形成穩定和高質量的民主,而且在其中備受煎熬。結果,“民主化往往不能成為國家建設的一個過程,反而是國家的毀滅過程”。這尤其表現于多民族國家。[1]因此,民主鞏固就成為近年來國際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問題。民主鞏固的原因和影響因素很多,國家能力即是其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新興民主化國家如果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有效應對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系列難題,保證民主化進程的有序平穩,那么民主將很難鞏固。
一、民主鞏固的進程需要國家能力的有力保障
關于民主鞏固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什么是民主鞏固?民主鞏固的標準是什么?國際學術界目前并沒有一個基本共識。多數學者根據自身的研究和思考給出了不同的界定,基本上可以分為四種:分別以制度、行為者和文化為中心以及從綜合的、宏觀的角度來界定民主鞏固。[2]其中,較為全面的當屬林茨和斯泰潘的觀點。他們從宏觀的綜合視角認為,民主鞏固意味著:⑴在行為上,沒有重要的行動者將運用重要資源去實施暴力、建立非民主政體或尋求外國干涉而達到獨立;⑵在態度上,絕大多數民眾都具有這種信念: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會集體生活最合適的方式,反體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或被孤立;⑶在制度上,全國范圍內的統治力量和非統治力量都服從于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特定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習慣于在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圍內解決沖突。[3]可見,他們對民主鞏固設置了較高的條件與要求。在他們看來,民主鞏固不僅需要民主制度在整個社會中成為惟一的政治游戲規則,而且需要絕大多數民眾在態度上認同民主理念,主要政治參與者不再從事以顛覆民主或分裂國家為目標的行動。簡言之,民主鞏固意味著民主獲得了持續生存和發展的較高程度的保障。
民主鞏固不是一蹴而就的。當新民主政權因為某種原因初建后,國家雖完成了制度形式上的轉型,但并不代表著它一定能夠持續生存,走向鞏固。亨廷頓曾指出,在19世紀初以來的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每一波都伴隨有相當多國家的民主退潮,因而民主鞏固需要經歷一個持續的過程。期間,民主體制不斷完善,民主質量逐步提升,民主認同日益廣泛。同時,民主體制也面臨著諸多挑戰,時刻經受著生存考驗,任何重要問題一旦解決不好都有可能延緩或顛覆鞏固進程,其能否生存和前行的關鍵在于其應對和處理挑戰的能力。林茨認為,歸根結底,民主崩潰的過程“始于政府的無能,以至于出現問題時,只能以不忠誠的反對黨的粉墨登場而告終”。[4]當國家長期沒有能力解決民主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時,民主就有可能被人們從主觀上主動放棄。①如二戰前,因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民主政權無能,即導致了人們質疑民主效力并轉而支持獨裁。而且,民主政權的無能也面臨著被反民主力量顛覆的危險或可能造成其它的“國家性”問題。蒂利認為,國家能力過低可能會造成內戰或一些不服從中央政權的小暴君們的分裂統治。19世紀的愛爾蘭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5]因此,在民主走向鞏固的進程中,國家能力至關重要。國家能力的狀況直接影響著民主化進程的每個階段及其走向。新民主政權如果能夠有效控制轉型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從容應對挑戰,不斷提升民主質量和民眾權益,就能夠有效遏制民主反動,保證民主化進程持續,進而增強民主的可信性,扭轉一些人的反民主傾向。
何為國家能力?斯考切波認為,國家能力即國家貫徹執行其政策、達致其目標的能力,特別是通過克服強有力的社會集團實際或潛在的反對或在不利的經濟社會條件下,來貫徹這些目標的能力。[6]而在米格代爾看來,國家能力是國家通過種種計劃、政策和行動實現其領導人所尋求的社會變化的能力,主要表現為影響社會組織、規制社會關系、抽取資源和撥款并以特定方式使用資源方面。[7]其集中體現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我國學者王紹光和胡鞍鋼認為,國家能力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它包括國家動員和汲取社會資源、調控社會、維護社會秩序和其統治地位以及塑造政治合法性的能力。[8]可見,國家能力即國家影響社會,調節和規范社會關系,有效動員和使用社會資源,以實現國家意志和目標的能力。其中,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和規制、調節和指導的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內容。
國家能力這一概念來源于上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國家回歸學派”。他們在反思和批判行為主義“過于關注對現狀的描述而非關注于現實問題的解決”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視角,特別強調國家與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認為無論在發達國家抑或不發達國家,國家在各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中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他們看來,現代國家作為一個有效的組織實體,必須能夠對社會進行政治統治、管理和服務,一定的國家能力是國家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前提基礎和基本屬性,也是國家服務和影響社會的基本要求。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要求國家必須能夠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調節和規范,維護社會秩序,推行必要的國家政策與法律。因而國家能力的現實狀況是解釋一國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
二、國家能力對民主鞏固影響的路徑分析
一般來講,新興民主政權的民主化從開始到鞏固的過程需要應對一系列難題。亨廷頓曾將其概括為三類:轉型問題、情境問題和體制問題。[9]所謂“轉型問題”是如何對待以前的威權官僚即“虐待者的難題”和如何減少軍隊對政治的介入以及建立以職業制為基礎的文武關系即“執政官的難題”。這實際上是消除民主中斷的威脅,保持民主的持續生存。所謂“情境問題”是產生于一國特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問題,與政治制度無關。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將影響一國的政治社會穩定。所謂“體制問題”來源于民主體制的運轉,即民主體制能不能產生民主績效,這對其民主發展和質量提升影響重大。與此同時,由于理性的民主理念和價值的廣泛認同對于民主持續運轉具有重大意義,因而在新興民主化國家,普及和傳播民主的價值與理念、培養民眾的民主信仰,對民主最終鞏固意義重大。由此可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能力的影響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
⒈通過對“轉型問題”的有效應對和解決促進民主鞏固。誠如前述,民主鞏固意味著在一個社會里沒有重要的行為者企圖顛覆民主政權,也沒有任何特定的集團超越于通過民主程序訂立的法律和制度之上并享有特定的非民主特權。然而,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大多數新興民主化國家基本上是由威權政權轉化而來的,許多威權統治者在退出時往往設定了許多條件,保留了許多權力自治領地和特權。這在那些由軍人政權通過協議主動或被動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體現得尤其明顯。如拉美的智利、巴西以及亞洲的韓國。許多威權政權的退出都是在交易與妥協中完成的,為了實現民主化,民主勢力不得不作出巨大妥協。因為“還政于民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威權體制退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威權統治者能夠得到何種程度的保障”。[10]這就產生了亨廷頓所說的“轉型問題難題”即“虐待者的難題”和“執政官的難題”。盡管在威權勢力特別是軍人勢力非常強大的情況下,在民主化初期對其作出一定的讓步,降低了其對文官政府的威脅,甚至有助于民主政權的持續。[11]但這些特權和自治領域的存在始終是民主政權的巨大威脅和民主鞏固的重大障礙。①因此,對于新生的民主政權來講,要想達到民主鞏固,必須正視的一個關鍵而敏感的問題就是如何清除威權遺產,取消威權特權和自治,使軍隊接受文官政府的絕對控制。
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如果新民主政權能夠平穩而有序地應對并解決這一問題,巧妙地清除威權遺產、消除特權、有效控制軍隊和武裝力量,它無疑將有可能進一步持續下去,民主化進程就能走得更遠。比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智利、韓國、西班牙等國家就都較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最終走向了民主鞏固。否則,民主化進程就可能因為威權勢力的卷土重來而中斷。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有許多曾經一度是民主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和巴西,但其民主都因為軍事政變而中斷。因此,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新民主政權能力的大小決定著其可能在多長時間內解決這一問題,決定著民主鞏固的程度和速度。如果新民主政權能夠抓住有利時機、采取有力手段,較為迅速地解決這一問題,那么,民主鞏固的時間將較短;反之則較長,甚至民主化進程會被中斷。
⒉通過對轉型期社會問題和秩序的有效應對與控制促進民主鞏固。任何一個國家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都會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和困難。其中,有些是一國特有的“情境問題”,有些是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普遍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在一定的時間內被有效地解決,直接決定著民主能否持續和走向鞏固。一般來說,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化初期往往面對著急迫、直接的反對與顛覆活動以及民眾的過高期望和激進訴求。前者主要源于民主化初啟,舊的反民主勢力還沒有被肅清或削弱,仍有一定的力量或影響;后者主要源于長期生活在非民主政權下的民眾對民主的理想觀念——民主能帶來社會公平與自由、提高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等。然而,這些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能實現的。當這些要求無法滿足時,常常會引發民眾的失望情緒,由豪情滿懷墜向“冷漠、挫折和幻滅”,導致不滿和怨恨,激起示威、抗議甚至是社會騷亂,而這又可能為伺機顛覆的反民主勢力創造機會。有關拉美民眾政治態度的資料表明,對民主體制的認可和擁護是有條件的并且波動很大。有相當一部分民眾曾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并對民主充滿期待,但很快又陷入了失望甚至幻滅之中,造成普遍的冷漠甚至“反體制”傾向,甚至組建或加入極端主義組織。[12]因此,新民主政權特別是那些從長期專制集權轉化而來的政權,在民主化初期社會往往容易動蕩和失序。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人不可以無秩序而有自由,[13]缺少穩定和秩序只會導致政治衰敗。因此,在民主化進程中,對激進的社會運動或訴求以及對反對或顛覆勢力的控制或緩和并保持一定的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若新民主政權能有效應對民主化初始進程中的各種問題與訴求,控制可能的反民主活動,穩定社會秩序,民主化進程將較為平穩,也能夠為民主制度的運行和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創造有利環境,并為進一步解決其它較為棘手的問題創造條件,從而形成良性互動,逐漸樹立民主制度的權威性,使民主政權的生命力不斷增強并走向鞏固。反之,若新民主政權在民主化進程中無法有效地控制社會秩序,其民主鞏固將步履維艱。韓國的民主化進程即清楚地展現了轉型期社會問題和秩序的控制是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的。韓國在1960-1961年短暫民主化的失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新政權國家能力不夠,未能有效地控制社會秩序。當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再次民主化時,新政府很好地與社會進行了互動、合作并相互克制,有效控制了社會秩序,為有序解決轉型問題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民主鞏固進程。[14]而印尼在民主化進程中,由于民主政權缺乏國家能力,未能有效控制社會問題和秩序,社會動蕩,種族——教派流血沖突時有發生,致使人們產生失望和懷舊情緒,期望國家出現一位強力領袖甚至是軍人總統。[15]當然,這一控制必須保持一定的“度”,不能采取或只依靠赤裸裸的暴力進行壓制。因為“由暴力產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來統治”。
⒊通過提高民主績效促進民主鞏固。正如有學者所說:“民主體制的確立和存續取決于政治因素,但民主體制的鞏固和質量卻嚴重受制于各種結構性因素(如貧困、不平等以及體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績效)”。[16]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如果不能產生實質的社會績效,那么,這個制度遲早要被拋棄或改造。因而民主體制要想長期維持下去,就必須有效并產生民主實績,促進人類精神上或物質上的自由和幸福。印尼上世紀50年代民主制度在內政問題上的失敗,是其未能生存和鞏固的主要原因。[17]同時,民主鞏固還是一個民主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一個從低質量的民主到高質量的民主的連續譜。”[18]因此,民主要真正得到鞏固,必須深化和提高民主質量。低質量的民主雖然未必會使民主政權陷入解體,但民主長期低質化肯定會損害民主政權的合法性。
因此,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完成后,即從形式上建立起了一個民主的政治架構,但這個政治架構必須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有效而且能夠產生民主績效。當新民主政權有能力既能夠通過完善政治制度、規則和機制,保障普通民眾的制度性政治參與機會增多,平等進行利益表達和爭取;又能夠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和社會調整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民主制度的權威性、可信性就會逐步提升,民主自然也就容易走向鞏固。①反之,如前所說,雖然民眾可能在民主化初期對民主低效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容忍和諒解,但當民主政權長期無法有效提升民主績效、提高民主質量時,就可能為反民主力量或為反民主創造機會,出現民主退潮。即使是在那些民主政權已經運轉相當長時間并相當鞏固的國家,也可能因其無能而崩潰。菲律賓戰后民主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菲律賓在1946年至1972年間,其民主體制政權轉移相當順利,曾被譽為“亞洲民主櫥窗”。但由于嚴重的政治分贓、政黨功能不足和政黨政治弱化,國家能力嚴重缺乏,致使經濟發展緩慢,社會秩序動蕩,貧富差距懸殊,人民生活困苦,政治寡頭化、王朝化等,因而人民對民主逐漸產生懷疑與悲觀情緒。當1973年民主陷落時,人們對此冷眼旁觀。[19]而1990年軍人還政后的智利在民主鞏固進程中,民主績效發揮了巨大作用,有效提高了經濟實力,減少了貧困,緩和了社會矛盾,暢通了社會利益和訴求表達渠道,從而保證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20]
⒋通過加速民主文化的形成促進民主鞏固。阿爾蒙德等人指出,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僅依靠其政府和政治結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依靠對民主的支持性的公民文化,否則,民主政府獲得成功的機會非常渺茫。[21]就是說,民主文化對維持民主政治的有序運行和穩定影響重大。沒有了支持性的公民文化,民主政治很難運作甚至很難生存。因而科恩指出,民主意識或民主習慣的培養和形成可能是民主制度運轉的最重要條件。[22]達爾甚至認為,只有民主價值的廣泛傳播和接受并形成民主文化,才能說明民主已得到了鞏固。這種文化為忠于民主程序提供了充分的情感和認知支持,并將幫助其渡過危機。[23]蒙古在落后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下,民主仍得以鞏固乃是源于其上至精英、下至民眾對民主價值的秉承與固守。[24]可見,“民主這種東西并不是只要制定了合適的法律就可以輕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才能得以繁榮,否則就難。”[25]民主的平穩運轉要求絕大多數民眾都認同民主規則,信仰民主理念,堅守民主價值。簡言之,民主的鞏固要求民主理念和價值必須被社會廣泛接受、認同和內化。對于新生的民主國家而言,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進行政治文化的重構。
因此,如果新興民主政權能夠加速民主文化傳播,促進民主價值與理念被廣泛接受,形成支持民主穩定運轉的社會意識,那么民主自然易于走向鞏固。事實上,國家在一個社會的文化形成中能夠發揮重大作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和現代的政治社會化理論都清楚地告訴我們,有效的政府能夠通過很多機制影響社會文化的導向。國家可以建構有效的宣傳機制,在社會中通過各種方式潛移默化和前后一貫地宣傳民主價值,傳播民主精神,促進民主認同的社會化,推動民主文化的快速形成。因此,一個有能力的新民主政權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促進民主理念、價值和制度的社會認同。當其加快了民主價值、理念的傳播,促進了民主文化的形成時,民主也就必然更快地走向鞏固。
當然,以上論述只是國家能力影響民主化進程的一些主要路徑,并沒有窮盡全部。并且這里所有的路徑都只是為民主鞏固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因為民主化進程是一個多階段、多面向且充滿荊棘的發展歷程,每一階段、每一方面的失敗都有可能導致民主化進程的中斷和民主鞏固的失敗。民主政權對每一階段、每一方面所面臨困境和問題的有效應對都為民主化的持續清除了部分障礙,創造了一個走向更加深入的機會。但這并不代表在下一階段或另一方面就一定能夠順利,下一階段或另一方面的失敗仍然有可能阻礙民主鞏固。而且如圖所示,它們之間也是相互影響、互為促進的。同時,民主化進程的順利推進、民主能否有效鞏固取決于包括國家能力在內的一系列因素,國家能力只是其中之一,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充分的條件。它在一定程度的存在只是為民主鞏固提供了可能性,是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而且國家能力和民主化進程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系,新生民主政權國家能力的強弱影響到其民主化進程和鞏固,能夠提高其鞏固的程度,改善其運作的有利環境;反過來又能夠進一步提升新民主政權自身的有效性和能力,而國家能力在民主化進程中的進一步增強反過來又進一步提高了新民主政權鞏固的可能性。因此,國家能力和民主化進程之間是一種多環節的累進式層疊促進的復雜關系。兩者在互動中都有可能不斷得到提高和增進。
三、結論:國家能力對民主鞏固的雙重影響
由上可見,國家能力的強弱對民主化進程有著巨大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民主化進程能夠走多遠、持續多久,深刻地影響著民主鞏固的過程。國家能力太弱,極有可能造成國家因無法應對民主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而被民眾否定或被反民主勢力顛覆,導致民主退潮;而國家若能有效地解決、應對這些問題或挑戰,無疑能夠增強民主體制生存和持續的可能性。然而,國家能力的強大也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并被致力于追求民主的勢力或集團掌握,毫無疑問會增強民主體制延續和走向鞏固的可能;反之,強大的國家能力也有可能導致其對民主的壓制,使得民主化進程倒退或停滯。一是在民主化啟動階段,威權政府的強國家能力無疑降低了民主化轉型的可能,使得民主或只是曇花一現或被扼殺于搖籃中;二是民主化進程中的強國家能力有可能誘使統治者無意與社會進行協商、脫離民主控制,并使國家權力轉向為個人謀利的政治腐敗。蒂利認為,在政府能力非常強時,政府代理人和其他現存社會不平等的既得受益者聯合起來,必然增加了權力尋租的機會和動機。[26]而且國家作為一種強制組織具有潛在的自主性,擁有著自身獨特的組織利益,不一定與社會利益相一致。[27]當這種自主性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國家權力的濫用也就成為必然,進而對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威脅。
可見,國家能力對民主的促進是有限度的。一定的國家能力是民主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強國家能力既有可能保障民主,亦有可能成為壓制、傷害甚至摧毀民主的工具。因此,國家能力太強或太弱都是對民主化進程的威脅。對于民主化中的國家來說,建構和增強國家能力是必須的,國家無論是提供服務、解決問題還是保持自身生存,都需要一定的國家能力;但同時也必須使國家能力受到民主程序和規則的控制,國家能力不能成為脫韁的野馬。
【參考文獻】
[1]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36.
[2]陳堯.民主鞏固學:民主化研究的新領域[J].社會科學,2007,(07).
[3][4][18](美)林茨,斯泰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6,168,7.
[5][26](美)蒂利.民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81,182.
[6]Peter Evans et.al,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9.
[7]Joel·S·Migdal,Strong Society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4-5.
[8]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M].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9](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聯書店,1998.262-263.
[10][12][16]張凡.當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41,65-66,80.
[11](美)海哥德,考夫曼.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13](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89.7.
[14]郭定平.韓國政治轉型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日)森山茂德.韓國現代政治[M].臺灣五南出版公司,2005;(韓)趙利濟編.韓國現代化:奇跡的過程[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5]莊禮偉.“弱國家”形態及其根源:對印尼的案例分析[A].李文主編.東亞:憲政與民主[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張錫鎮.印尼民主轉型和民主化軟著陸[A].李文主編.東亞:憲政與民主[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7]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M].臺北揚智文化公司,2000.55.
[19]陳鴻瑜.菲律賓史[M].臺灣三民書局,2003;周東華.戰后菲律賓現代化進程中的威權主義起源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
[20]袁東振編.拉美國家的可治理性問題研究[M].當代世界出版社,2010.
[21](美)阿爾蒙德,維巴.公民文化[M].東方出版社,2008.443.
[22](美)科恩.論民主[M].商務印書館,1988.173.
[23]朱德米.鞏固民主——對政治發展中“鞏固民主”的分析[J].重慶社會科學,2000,(05).
[24]祁玲玲.蒙古的民主化:政治精英的理性選擇[J].二十一世紀(香港),2012,(04).
[25](美)亨廷頓.文化的重要作用[M].新華出版社,2002.143.
[27](美)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33.
(責任編輯:高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