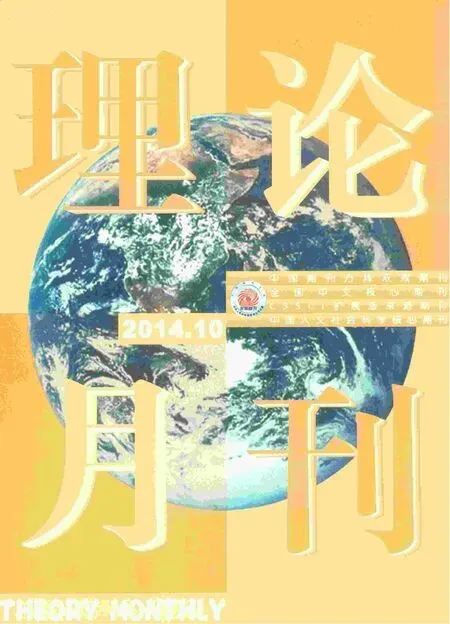論劉基的實學思想
李青云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071)
劉基(1311—1375),字伯溫,號犁眉,封誠意伯,謚文成,浙江溫州文成南田(舊屬處州青田)人,元明之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謀略家。以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而馳名天下。主要學術著作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經》等,均收錄于《誠意伯劉文成公集》。
近年來,在中國實學研究會以及一批實學研究理論工作者的推動與努力之下,“實學”的觀念已廣為學人所認可。一般認為,實學源于中國,中國實學實際上就是從北宋開始的“實體達用之學”。從內涵上講,它不同于佛、老的“虛無寂滅之教”,是由“實體”與“達用”構成的。由此界定出發,我們可以對劉基的實學思想做些探討。本文以為劉基實學思想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圣人作經以明道”的文學經世論,“儒者有用之學”儒家經世理念,以“切于民生日用之常”為選題而類編的《多能鄙事》。
一、文學經世:圣人作經以明道
劉基文學經世論主要包括三層涵義,詩歌經世論、文作經世、經文經世。
關于“詩歌經世”的主張,劉基在《照玄上人詩集序》文中提出:“夫詩何為而作哉? 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諷戒,莫不有裨于世教。”[1](P74)正是因為“先王陳列國之詩”的目的在于“驗風俗、察治忽”,詩歌創作應該發揮“美刺諷戒”的教化功能,直接為社會現實服務;從而反對“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的創作體裁與取媚于達官貴人的創作動機,“憂世感時”才是風雅之道所弘揚的時代主旋律。
劉基從傳統的儒家“詩教”觀出發一再強調詩歌有教化諷諭、美刺風戒的實際效用。[1](P4)詩作之辭絕非“誦美”阿諛式的“空言”,贈人之詩(序)應當“主于風諭”:“余(劉基)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獎之言,異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愿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后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與不朽,不亦偉哉!”[1](P76-77)這里劉基援引孔子儒家關于交友之“道”的論述,即《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可見,以“益者三友”、“以友輔仁”為交友原則為“準的”,與友人贈序詩文之作應達到“交相助而有益”的實際效用。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漢書·藝文志》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民間之“詩”如能被采詩官“采而用之”,在位者“觀民風、達下情”才成為可能,起到“諷諫君王”的政治效用,劉基作如是言:“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為無補哉!”[1](P91-92)不難看出,劉基詩作之論,堅持了“詩”作之本意,具有諷諫時政作用,即是一種典型的政論詩風格。對于詩作“好為論刺”、“直陳其事”以經世致用的創作宗旨,劉基在《王原章詩集序》中也有闡釋:“使為詩者俱有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于世事,王者當何取以觀之哉! ”[1](P76-77)為詩以濟“世事”,“有裨于世教”,這才是詩作的真實目的,這是一種批判求“實”的精神。
關于詩歌之所對“世事”所奏響的主旋律,劉基以“毛詩序”為文本,指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聲就是對世道治亂變化的真實寫照:“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1](P84)也就是說,文學詩歌創作的真實價值并不在于花前月下般地孤芳自賞,“措大事”,關注現實才是詩文的價值所在。申而言之,詩文創作與世事息息相關,這是一種以“文學濟世”為主旨的創作動機。此外,劉基在《題王佑軍蘭亭帖》中云:“王佑軍抱濟世之才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 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后世,悲夫! ”[1](P138)這里,劉基藉王羲之懷“濟世之才不用”,含蓄地表達了自己欲經邦濟世、有所作為的入世情懷。我們可以理解劉基的“詩歌經世”論其核心理念就是“詩政合一”,提倡詩歌之作為現實政治,即如何維護統治階級國家政權的長治久安服務;君王及各級官僚統治機構應該視上采之“詩”為制定國家施政策略的重要參考依據。
由“詩作經世”的創作理念為前提,劉基以為“文與詩”“無異”:“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衰,豈茍然哉!文與詩,同生于人心,……固無異也。”[1](P88)可以知道,以“時之泰否”為體裁且生于“人心”之文,應當以“國之興衰”為創作基調,關注現實社會。此外,劉基尚有經文經世思想,提倡經、文創作關注經濟民生、社會政事,直接為社會現實服務。劉基在《送高生序》文中明確提出“經以明道”、“文以經世”的觀念:
圣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于事,則偭焉而背馳,揭揭然不周于宜,則雖有班、馬、揚、韓之文,其于世之輕重何如耶?[1](P64)
這段話包含有兩層意思:第一,儒家圣人所創作的“六經”文本皆是“明道”之文,沒有任何炫耀溢美之辭;這也印證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的古訓,儒家之學為君子之學。第二,后世學者研讀、學習先賢圣人之經文大義,不應該局限于問答、識記的知識論層面“玄談空論”,應該貫徹“學以致用”的原則,“以見于行”、“驗之于事”。
總之,劉基的文學經世論,提倡托諷刺世,評議時政,以達上聽,反映民意,直接為現實服務。
二、儒學經世:儒者有用之學[2](P3792)
在傳統封建社會之中,諸生士子們把“讀書”作為博取功名利祿的“不二法門”,劉基以為這是“世儒”的一種迂腐短見,不可提倡。“讀書不可迂,檢身不可疏。勸子慎勿學世儒,躗言恥行名為愚。……才全德備稱大賢,報國榮親兩無愧。”[1](P299)讀書問學應以經邦濟世為己任,在掌握本領、練就才能的同時,必須努力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成為“才全德備”般的賢者。與此同時,劉基以為傳統儒家經世職志絕非以貪圖利祿、喪失人格為前提,從而突出了“以道事君”的君臣觀。這里,劉基樹太原閔仲叔的“節士”義舉為榜樣:“吾愛閔仲叔,幽居翳茅茨。應辟思濟世,利祿豈其私。進當致堯舜,退則老蒿藜。焉能犬馬豢,以為天下嗤。”[1](P320)閔仲叔的品行志節堪稱實踐儒學的典范,完全可以作為后世效仿的榜樣。
劉基《沙班子中興義塾記》(至正十一年,1351)文對“為學之道”予以解讀,“夫學也者,學為圣人之道,學成而措諸用。”[1](P68)在劉基這里,儒家的圣人之學就是“修己以治人”為標的學問,具有“修、齊、治、平”的社會效用。此外,劉基在《書善最堂卷后》文以為東漢東平王的“善最”之論就是“天下之格言”。查《后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 王曰:‘為善最樂’。”我們知道,孔子儒家證成“圣賢之道”的重要標志就是“善最”的圓滿與成就。劉基作為一代儒者,也知道行“善”不是口頭說教,唯有依“求諸實踐”之“方”,身體力行,才有可能實現“修齊治平”的宏愿與理想。“然‘善’之云,不過概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異也。”[1](P135)由此可知,道德修養就是一種以“善最”為追求而踐履實踐工夫的過程,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儒家以“希賢證圣”為職志的道德修養學說稱之為“道德實學”。
作為儒者的劉基畢生以傳統儒學“修己以治人”、“修己以安百姓”理想為追求,而劉基本人一生“剛毅慷慨,持大節,留心經濟”,[3](P272)所以留下了不朽的“經濟”名作《郁離子》與《寫情集》,葉蕃在《〈寫情集〉序》文中指出,“(劉基)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而詞作《寫情集》“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3](P273)
關于儒者劉基“有用之學”的言論即思想主張主要見于政論性寓言集《郁離子》十卷十八章一百九十五條之中。劉基門生徐一夔在題解“郁離者何”時,以為“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3](P274)為天下后世建言獻策即“矯元室之蔽”而作的《郁離子》,“詳于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明乎吉兇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吳從善在《郁離子序》文中對《郁離子》之“善”作如是解讀:“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辯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圣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1](P677)從這兩段書評之中,我們不難看出,《郁離子》的創作宗旨即是對儒家“修己以敬”、“修己以治人”、“修己以安百姓”理念貫徹與實踐,是對《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思想的發揮與運用。一言以蔽之,這是劉基自覺踐行“儒者有用之學”即“開物成務之學、經綸大徑之道”的理論成果。難能可貴的是,劉基相機而動,將《郁離子》之中各種理論主張“措用于”輔翊朱元璋開創大明王朝的政治實踐之中,在一定程度之上實現了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以“內圣外王”為追求的志業。所以,陳烈在《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后序》文中評價劉基“文章勛業”、“儒先理學”的業績之時,以為“樹開國之勛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杰兼休并顯于千百世之后,公(劉基)蓋出有所為而生非無意者矣! ”[3](P286-287)
此外,劉基在《贈弈棋相子先序》文中的“相子先兄弟皆于棋,人無敵焉”,劉基以為若僅以“奕”為娛樂之具,實乃“無用之伎”,即“其無益于用也”;劉基寫作該贈序之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勸誡相氏兄弟,領會“格物致知”的“類推”原理,善于融會貫通,活用弈棋之術所蘊涵的兵法之道,為制止、平息元季寇盜出謀發慮,消彌動亂,造福蒼生。[1]67這充分體現了劉基經邦濟世、勇于擔當的淑世情懷。正是因為劉基能夠把“儒者有用之學”成功地付諸于政治實踐之中,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認為劉基就是一位“學以致用的儒家”。[4](P1-3)
三、《多能鄙事》:切于民生日用之常
《多能鄙事》系劉基類編的反映其實學思想的代表作。
關于劉基匯編《多能鄙事》十二卷的時間與命題緣由,范惟一以為,“是書蓋公微時手輯,因題曰‘多能鄙事’,以自附于孔子‘少賤’之義”。[5]依范氏之論,“微時”即“微賤之時”,指劉基在未顯貴之時有是書。而,“多能鄙事”題稱源于孔子《論語·子罕》“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語。沿著范惟一提供的線索,筆者以為《多能鄙事》就是劉基年青時所匯編。理由如下:劉基晚年有《旅行五十首》之作,其一云:“憶年二三十,笑人不能勤。誦書欻萬言,落筆飛煙云。有朋自遠來,講論窮朝曛。一藝恥不知,高蹈未前聞。”[1](P374)通過這首詩我們隱隱約約可以看出《多能鄙事》的創作年限與背景,“憶年二三十”,劉基二三十歲時,系元至順元年(1330,時年20歲)至至元六年(1340,時年30 歲)間。檢索劉基生平紀年,可以知道:至順元年(1330)到元統元年(1333),為劉基讀書并參加科舉考試時期;至元二年(1336)到至元六年(1340)系劉基初涉官場并任職于江西高安縣丞期間。在這兩個時段之中,劉基或因舉業纏身、或因政務繁忙,基本無暇與友人談笑論道。而元統二年到至元元年這兩年間,劉基恰處于24、25 歲之時,與“憶年二三十”句相吻合。此時的劉基因中三甲第20 名進士而科場得意,在南田老家注官守闕、等待銓選,倒也清閑自在,“有朋自遠來,講論窮朝曛”就足以說明這點;總之,這時的劉基有時間、更有精力“誦書欻萬言”,以匯編《多能鄙事》。“一藝恥不知,高蹈未前聞”句包涵以下信息:漢儒揚雄《法言》有“通天地人曰儒”句,“儒戶”出身的劉基必須誦讀大量與農業生產、日常起居生活有關的各類書籍,才可以稱之為“儒”;又,劉基之所以與友朋“高蹈未前聞”,是因為中取進士以前劉基所閱書籍多為與科舉程式相關的儒家經典著作,不可能涉獵更多的雜家書籍。此外,少年劉基“博洽群籍”且有“過目洞識其要”的天賦,范惟一也指出:“(劉基)于學無所不窺,自天文經史以至九流百家之言,罔不泛獵其華而綴其指要。”[5]唯有“注官守闕”的閑暇之時,才有可能為劉基檢閱文獻、類編《多能鄙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總之,筆者不認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關于《多能鄙事》“體近瑣碎,……殊失雅馴……殆托名于基者”的不實之論;[6](P1725)判定 《多能鄙事》 系劉基于元統二年(1334)到至元元年(1335)間在南田老家守闕時所匯輯類編而成一部雜家書籍。
今傳世的《多能鄙事》版本有二:一是藏于上海圖書館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范惟一刻本(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收錄),卷首有范惟一“序”文一種;二是民國六年(1917)上海榮華書局石印本,首置嘉靖十九年(1540)青田儒學訓導浮梁魯軒程法“敘”文。關于《多能鄙事》最早付梓刊刻時間,根據上文提到的青田儒學訓導魯軒“序”文,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范惟一《多能鄙事·序》文提到的“往,余(范惟一)在京師,從友人所偶見二冊,非全書”。明隆慶六年(1572)何鏜《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文提到的:“先生(劉基)所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據此,我們可以判定,至遲于嘉靖十九年,《多能鄙事》 作為一部類書式雜家體裁的匯編集已經刊刻,并流行于世。
關于《多能鄙事》所輯主要內容,我們首先可以通過魯軒《敘》文了解:“所編之錄有曰飲食,所以衛性也;有曰服餙,所以華躬也;有曰器用,贍日給也;有曰百樂,防時虞也;有曰農圃牧養,則殖財之本根;有曰陰陽占卜,則演《易》之支流。凡若此者,皆切于民生日用之常,不可一缺者,事雖微而系甚大。”[7]范惟一《序》文曰:“其書凡飲食、服餙、居室、器用、農圃、醫卜之類,咸所營綜。其事至微細,若無關于天下國家。然跡民生日用之常,則資用甚切而溉益,頗弘其義,曷可少焉? ”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多能鄙事》十二卷,……是書凡飲食、器用、方藥、農圃、牧養、陰陽、占卜之法無不備載,頗適于用。”[6](P1725)茲筆者檢閱《多能鄙事》卷目內容:卷一至卷三為飲食類,有造酒法、造醋法、造醬法、造鼓法、造酢法、腌藏法、酥酪法、烹飪法、餅餌法、回回女真食法、糖蜜果法、活蔬法、茶湯法、老人療疾方;卷四為服餙類,有洗練法,染色法;卷五為居室、器用類,有住宅諸忌、收書畫法、文房雜法、制竹炭法、制油蠟法、冶器物法、合諸香法;卷六為百藥類,有經效方、辟蟲法、理容方、雜用方;卷七為農圃、牧養類,有作園籬法、種水果法、種藥物法、種竹木花果法、養六畜法、醫治六畜法;卷八至卷十二為陰陽占卜、占斷、十神類,限于文幅,茲不贅述。
從上述各種“序”文及卷目內容,不難發現,劉基《多能鄙事》一書選材體例主要圍繞“民生日用之常”而匯輯。正是匯輯《多能鄙事》的經歷使得劉基精通“雜學”,對飲食、器用、方藥、農圃等知識皆有涉獵,這也反映在劉基的詩文之中,比如劉基“避地會稽”之時曾參與種植勞作,有《久雨壞墻園蔬盡壓悵然成詩》等為證;[1](P355)又,為官京師時為宗侄劉彬所“戲作《菜窩說》”文中就關于種樹、稷黍、養魚以及種植瓜果蔬菜之法達二十余處之多。[1](P143-145)要之,《多能鄙事》的類編足以說明劉基對實用、實效、實學的重視,它是劉基實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林家驪點校.劉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裴世俊等選注.劉基文選[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
[4]成中英.如何理解及評價劉伯溫的歷史與學術地位、政治、思想、文學與傳說[A].何向榮.劉基與劉基文化研究[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范惟一.多能鄙事序[A].嘉靖四十二年刻本[M].上海圖書館藏.
[6]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97.
[7]程法.多能鄙事敘[A].民國六年石印本[M].浙江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