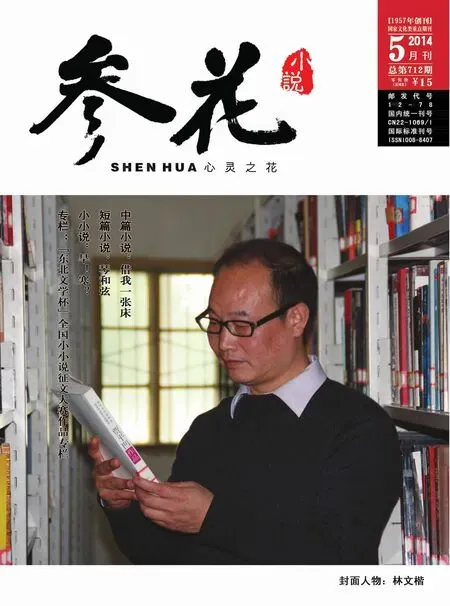孔子因材施教的情理動因之“君子”言行規范
——兼論“一葉知秋”式閱讀經典之法
◎賈 茜
孔子因材施教的情理動因之“君子”言行規范
——兼論“一葉知秋”式閱讀經典之法
◎賈 茜
“君子”是孔子思想中一個重要概念,《論語》對它進行了方方面面的闡釋,包括對待學習、道德修養、理想境界等。而孔子對其弟子“因材施教”式的教導,是建立在一種統一人格的基礎之上的,那便是“君子”這一人格楷模。因此,要想分析孔子是如何因材施教的,必須首先疏解他與群弟子對“君子”人格的規范。這種閱讀經典的方法是抓住一詞在一部經典中的出現語境,綜觀其旨歸,從而管窺《論語》體現的育人思想,可以稱為“一葉知秋”法。
君子 言行 禮 “一葉知秋”式閱讀法
“君子”一詞出自《易經》,班固解釋為“群大夫”《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漢代班固《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從孔子開始,“君子”一詞上升到士大夫及讀書人的道德品質層面。“君子”在《論語》中頻繁出現,內容涉及君子之學、君子言行、君子之志等方面。這些方面,尤其是君子言行可以用“禮”來統一,可以說,孔子與群弟子對“君子”理想人格的闡述呼應著克己復禮的思想,也成為他教育思想的基石,是“因材施教”的總前提。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篇》)“重”為“莊重”,“威謂”“威嚴”[1]。而君子之“重”的精神內核就是言行穩重。孔子對“言”與“行”的態度是更重視“行”,認為君子可以不善言辭但必須善于踐行,即“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行”在“言”先,少說多做,“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篇》),“君子恥其言而過其實”,反對言過其行,未行而言。可見,孔子所謂君子之重,不僅體現于儀表、知識,也在于言行的謹慎,正如子貢所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張篇》)這說明,孔子及其弟子對言的標準是,提倡真實而不虛浮,因此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衛靈公篇》)。既實事求是地看待人之言,也認真地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子路篇》)另外,孔子并非一味不信人言只重其行,又主張將言作為了解一個人的手段之一,正是“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從另一個角度講,恰當為言,可以使別人看到自己的美德,而虛浮為言,就會給人留下壞印象。
關于君子之行,在《論語》中是與“言”相提并論的。“子貢問君子。子曰:‘先其行而后從之’。”(《為政篇》)孔子及其弟子對于“行”十分重視。那么,他們理想中的君子之行又是怎樣的呢?首先,“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季氏篇》),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品德修養和公德規范,在實踐中才能盡量避免犯錯誤。其次,不僅在橫向的各個人生方面這般要求,在縱向的人生階段中也是以禮節之,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在孔子及其弟子看來,君子的儀表同樣能反映一個人的德行,因此對穿著打扮、儀容神態也十分講究。“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不亦威而不猛乎?”
可見,孔子及其弟子充分認識到內涵與外在統一的關系,如子貢所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顏淵篇》)
孔子及其弟子對君子行為的描述是溫文爾雅,重視外在與內在的統一,且“周而不比”(意思是廣泛結交而不結黨營私),莊重而不粗俗,這樣看來,禮的約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禮”又不是刻板教條的。他們并不忽視人的性情因素,認為禮緣情而設,在服喪期間,吃美味不覺得味美,聽音樂不覺得快樂,閑居也不覺得安適,實為情感使然:“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陽貨篇》)發乎情止乎禮,禮不是單純的規范,而是情感表達的需要。
另外,孔子及其弟子們也十分注重求實精神和堅忍不拔的品格,“躬行君子”(《述而篇》)“君子固窮”(《衛靈公篇》)推崇的就是這種剛健之氣。而這種剛健之氣的精神內核,是一種堅定的恪守,恪守君子應有的行為準則——“禮”。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之情發于衷心,而又約之以禮,使其成為一種謙謙君子的行為姿態,具有道德示范的社會效用。故曰:“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有了孝悌這個根本,民風純良,社會治安自然良好,在這個過程中,君子的行為具有社會示范的重要作用。
可見,君子居喪,發乎情而約以禮;君子尚德,求善于本心,以盡美于威儀,都是善于向自我約束和雕琢中達到人格的完善,可謂“君子求諸己”以至“泰而不驕”;君子“懷德”、“懷刑”通曉禮儀而又曠達于心,因而做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的內心世界是自由的、豐富的,又具有“約之以禮”的理性追求,因此體現于外在行止彬彬有禮:“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這種通達寬厚的處世態度,仁愛正直之心,必然要求實事求是,坦蕩為懷,正是“君子疾夫舍曰欲知而必為之辭”(《季氏篇》),意思是,君子痛恨那種不實事求是卻要找借口自我辯解的行為,光明磊落,是君子必備的行止準則,因而也就無所憂懼:“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篇》)
正因君子如此追求道德完美,所以在孔子及其弟子看來,禮遇君子是合情合理的:“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篇》)意思是君子可以去井邊救人,但不能自己也陷進去。人可以被欺騙,但不可以被無理愚弄。
孔子對君子行止的規范,根本在于孝悌,培養在于循禮,如此便可生仁愛之心,通達之氣,用孔子對后生子夏的一句勸勉來概括即:“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篇》)儒者未必是君子,儒者遵循以上行止才算君子。而對于“君子”道德行止的要求,也體現了“禮”在孔子思想中的貫穿。
[1]《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漢代班固《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2]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頁. 本文所引原文皆依據本書。
*本文為廣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社會服務能力提升建設項目“社會服務行動工程”開放項目《“城市書房”推動全面閱讀的戰略論證》(桂教科研【2014】2號)、廣西外國語學院校級課題《孔子因材施教的情理動因》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西外國語學院文學院)
(責任編輯 馮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