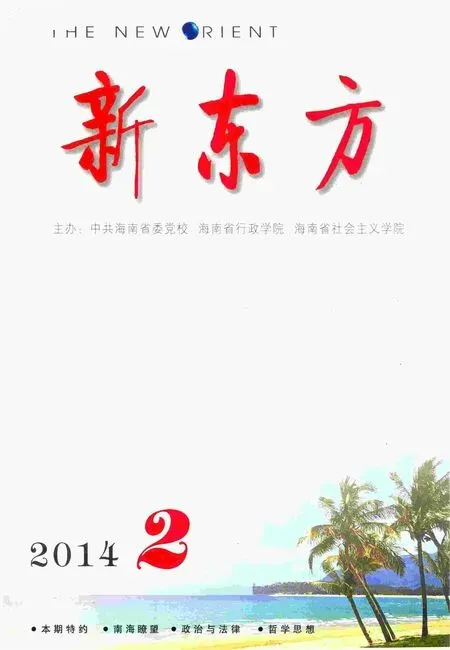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
遲福林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個歷史性突破:不僅牽動經濟體制改革,也將倒逼全面深化改革。
“市場決定”的經濟增長。我國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將取決于能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能否通過轉型改革釋放增長潛力。
釋放增長潛力關鍵在市場。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我國的突出優勢。
未來2~3年市場化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資源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要有實質性進展;壟斷改革應有重大突破;石油、電力、鐵路、電信、公共資源、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的水平將顯著提高。
“市場決定”的有為政府。“市場決定”不是不要政府,而是需要一個尊重市場規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政府。
建立公平競爭導向的宏觀調控體系。要把宏觀調控與行政審批職能嚴格分開,與財政金融體制改革有機結合,建立以獨立貨幣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盡快出臺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要以負面清單管理界定政府邊界,倒逼行政審批改革;中央政府應盡快制定和公布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先行試驗。
推動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主體回歸。明確把地方政府由市場競爭主體轉向公共服務主體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
“市場決定”的法治建設。重在把過多、過濫干預市場的公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
建設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盡快出臺國家層面改善法治營商環境的綜合方案;盡快形成相關的立法、司法改革的行動計劃,實質性提升投資者的穩定預期;盡快修改完善市場主體準入與監管的法律法規。
推進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變。要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改變以審批取代監管;有效整合市場監管的行政資源,組建權威性、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機構;把反行政壟斷作為實施《反壟斷法》的重點。
推動經濟司法“去地方化”。受地方利益驅動,地方政府干預經濟司法、導致司法不公的現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建議實行中央地方雙重法院體制:中央層面的法院體系主要負責經濟案件審理;一般民商事案件與治安刑事案件仍由地方法院審理。
“市場決定”牽動影響改革全局,并將伴隨著一場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它意味著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增長方式非改不可;它意味著權力配置資源導致機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非改不可;它意味著官本位、權力尋租、經濟特權的問題非改不可。我們有責任為推動這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全面改革竭心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