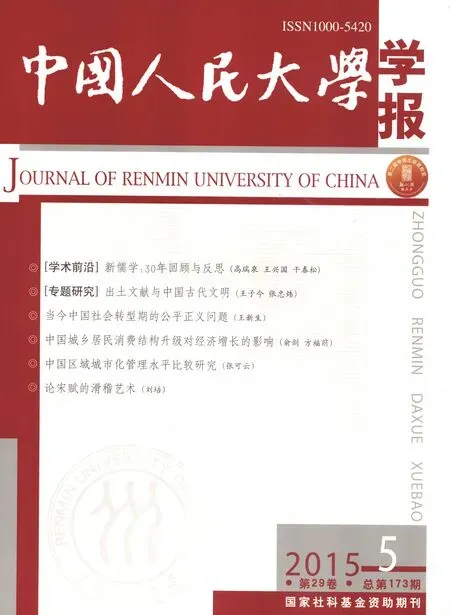變動的光譜*
——社會思潮研究視野中的現代新儒學
高瑞泉
?
變動的光譜*
——社會思潮研究視野中的現代新儒學
高瑞泉
隨著儒學復興運動的開展,“現代新儒學”概念的所指也正在擴展。在現代新儒學內部有不同的“道統”說,突破類似家譜的“道統”觀念,可以把現代新儒學的總體特征歸結為在回應和融攝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在經典世界有所根據而又適應現時代需求、希望能夠對治現代生活的理論。其歷史的起點可以追溯至以康有為等為代表的清末儒家精英集團的分化。而其現實則是: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包括激進主義的興衰,曾經是防御性的方位性意識形態的儒學,開始表現出改變現實的激進姿態,因而也使得現代新儒學的思想光譜大為改觀。
現代新儒學;道統;康有為;思想光譜
晚近三十年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大轉變是,隨著長期占據主流的激進主義讓位于保守主義,現代新儒學迅速崛起,有帶動儒學全面復興之勢。一方面,不但在學院體制內部儒學研究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而且民間的讀經活動,以及書院、學會、研究機構也不斷出現。另一方面,“重建禮樂”的嘗試也時有耳聞,盡管經過媒體報道過的總有變形之感;新儒學內部的派別之爭也已經出現,“政治儒學”VS“心性儒學”、“港臺儒學”VS“大陸儒學”,都成為媒體樂見的話題。這雖然是梁啟超所謂“思潮”作為“繼續的群眾運動”處于“生、住、異、滅”過程中而難以避免的[1](P1),但是也為哲學—思想史的研究拓寬了對現代新儒學作一種譜系學考察的空間。
一
較早提出“新儒家”或“新儒學”等概念的應該是賀麟先生。在1941年寫作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賀麟先生斷言“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現代思想的主潮”。[2](P4)它關系到民族復興的存亡大業,因為“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3](P4)在賀麟先生看來,新儒學或新儒家的內容至少包含哲學、宗教和藝術三項。事實上,20世紀30—40年代的“新儒學”主要的成就僅僅限于第一項:哲學。其路徑大致上按照賀麟先生所言:“必須以西洋的哲學發揮儒家的理學。儒家的理學為中國的正宗哲學,亦應以西洋的正宗哲學發揮中國的正宗哲學。”[4](P8)就大陸理論界而言,賀麟先生所述的具體情狀是四十多年以后才開始被重新認識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方克立教授主持現代新儒學的研究項目,采取了廣義的“現代新儒學”或“現代新儒家”的概念,與港臺及海外學者所說的“儒學第三期發展”局限于熊十力與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的學術活動不同,“把在現代條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價值系統,力圖恢復儒家傳統的本體和主導地位,并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實出路的那些學者都看做是現代的新儒家”。[5]
“現代新儒家”或“現代新儒學”概念的提出,與海外漢學家以往使用“新儒學”(Neo-Confucianism )專指宋明理學做了區別,不但由此激發了對于這一學脈中的人物與思想的研究,而且打破了門戶之見,將史學與哲學乃至在現代學院體制中幾乎廢絕的經學歸并為一體,比諸當時最主要的哲學史著作,擴大了人們對這一派的研究視野。*20世紀80年代有兩本最重要的近現代中國哲學史著作,都是著名哲學家所作。一本是馮契先生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書中對于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三位先生的哲學都有專論,對于賀麟、張君勱等也有涉及,注意到他們“都自稱接上了中國的傳統思想,以復興儒學為自己的使命。他們在學術上激發了民族自豪感,是有貢獻的”。但哲學路徑上則坦陳與其不同。(參見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載《馮契文集》,第七卷,619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另一本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曾經以《中國現代哲學史》在海外出過單行本,后來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馮友蘭先生將“接著”宋明理學說的現代哲學家劃為兩類:一是理學,有金岳霖和馮友蘭;一為心學,有梁漱溟和熊十力。(參見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十卷,543-650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相比之下,馮友蘭先生是從儒學內部劃分的,而馮契先生則是在整個20世紀中國哲學論爭的視野中既指出他們屬于東方文化派或玄學派,同時也以更哲學化的方式討論了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的哲學。不僅如此,我以為其更深層的意義在于超越了“道統”之爭。賀麟先生在敘述新儒學的系統時,已經用“正宗”來暗含了“道統”的意味。而他所謂的新儒學,在其《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被描述為“陸、王學派獨得盛大發揚”。[6](P18)牟宗三先生則進一步指出:“中國儒家正宗為孔孟……孟子為心性之學的正宗……陸王一系才真正順孟子一路而來。”[7](P69)而現代新儒學從熊十力到牟宗三,即代表了儒家之正統。牟宗三先生對朱熹則有“別子為宗”的評價,這理所當然會大有爭議的余地。港臺新儒家對馮友蘭先生一直頗有偏見,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也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接著”程朱講的馮友蘭先生進不了“道統”。當然,馮友蘭先生另有一種“道統”說,那就是:孔孟、老莊、名家、董仲舒、玄學、禪宗到程朱理學達到集大成。馮友蘭先生的使命是接著此“道統”而講“新統”。以上兩種“道統”說,形式上似乎只是從學理上梳理了各自的知識譜系,不過它是一種類似“家譜”的譜系,蘊含了超乎知識的意義,或者說“道統”論使哲學思想史的敘事發生了意識形態的變形。
正因為如此,對于“道統”說歷來就有各種批評。20世紀4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是從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的關系,根據政治正確的標準對其傾向提出批評*詳見周恩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載《周恩來選集》(上),142-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杜國庠在《論“理學”的終結》一文中說:理學除了道德性命之學說外,“還有所謂‘道統’的說法,以鞏固其壁壘,仿佛繼繼繩繩像真正的王麻子、陸稿薦似的,只此一家,并無分店。歷代帝王既利用它去鞏固政權,于是我們也就利用帝王這種心理去擴張勢力,而道統益見必要。” (參見杜國庠:《杜國庠文集》,3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還可見《杜國庠文集》中《紅棉屋雜存》十二,《玄虛不是人生的道路》等文章。;哲學上,有學者提醒要警惕“道統”論所可能蘊含的權威主義和獨斷論。在現代新儒家中人看來,這屬于外部批判,大可以忽略。不過,如果我們將批判儒學也視為廣義的儒學研究的話,那它也是現代思想光譜的一部分。從現象上看,以“批判地繼承”為宗旨的儒學研究,近年來似乎進入了潛流狀態。但是,我們現在比較多地強調“中西馬融合”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其實已經將前述態度視為一種預設。因為它首先要承認真理或傳統的價值并非可以由某一個或某一派儒者對于經典的詮釋所壟斷。
另一方面,現代新儒家內部批判同樣也指向了此類“道統”說,主要以余英時先生為代表。余英時先生有一篇長文《錢穆與新儒家》,中心是澄清錢穆與現代新儒家的干系,除了將作為“通儒”的錢穆先生與作為“別出之儒”的現代新儒家做了區分以外,還特別批評了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現代新儒家的“道統”論。他接著錢穆先生所謂“別出之儒因為受禪宗的啟發,發展出一種一線單傳而極易脆中斷的道統觀”的斷語,指出:“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種強烈的道統意識,但是他們重建道統的方式則已與宋明以來的一般途徑有所不同。他們不重傳道世系,也不講‘傳心’,而是以對‘心體’的理解和體認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得‘道體’。”[8](P202)以“心學”為正統,即必須肯定一個普遍而超越的“心體”對于一切人都是真實的存在。對于港臺新儒家樂于傳頌的熊、馮兩位先生關于“良知”是“假設”還是“呈現”的公案,余英時先生給出了另一個解答: “如果我們細察新儒家重建道統的根據,便不難發現他們在最關鍵的地方是假借于超理性的證悟,而不是哲學論證……只有在承認了‘心體’、‘道體’的真實存在和流行這一前提之后,哲學論證才能展開,但這一前提本身則決不是任何哲學論證(或歷史經驗)所能建立的。”[9](P204)所以,新儒家的“道統”后面實際上是“教”而非“學”,是宗教性的信仰,非理智與感官所能進達。換言之,它遵循了“要么全部,要么全無”的邏輯,不是我們通過論辯可以建立起的價值共識。余先生直截了當地說:“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制的哲學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10](P224)
當然,錢穆先生也有自己的“道統”觀,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是思想史家的道統觀,雖然著重要繼承的是北宋以來綜匯經、史、文學的儒學傳統,尤其尊重朱熹,但他視“歷史文化大傳統為真道統”。換言之,在錢穆先生這一系的傳承中,比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現代儒學的視野要寬闊得多、較少排他性。由于其學問綜合了經學、史學和文學,所以在現今的“國學”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像當初主張用“國粹”來激發民族意識的章太炎一樣,錢穆先生也主張“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國民對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11](P3)在民族意識高漲、歷史觀發生重大轉折的當下,以廣義的歷史連續性為“道統”的底蘊,較為容易被普通民眾所接受。當然,其困難在于歷史連續性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因而通史的敘事和歷史哲學的追問都是無法回避的。
二
上述所論,似乎是宋明理學“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在20世紀的延續與新演變。*余英時先生就評論過現代新儒家既有“良知的傲慢”,又有從“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不過,在牟宗三一系之劉述先先生看來,重點放在歷史文化方面的余英時先生,雖然不愿意承認自己屬于狹義的現代新儒家,但卻不在廣義的現代新儒家之外。參見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237-238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如果放寬眼界,即從整個20世紀中國思潮運動的視域來考察,則他們之間的“同”大于“異”,所以我們可以在繪制中國思潮的“三國演義”時將他們歸屬于文化保守主義一脈。但是,如果進一步研究,還是可以追問:現代新儒家是否僅僅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它是否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是保守主義,或者說始終是單一的保守主義?換言之,現代新儒家的光譜是否有更長的時段、更復雜的面相?
討論這一問題需要對什么是“儒”、“儒學”、“儒家”、“儒教”等一系列相關概念做一番澄清。從荀子開始,就對儒有各種分梳:有大儒、通儒、陋儒、小儒等等;近代儒者章太炎和熊十力都作有《原儒》,可看做對這一貌似簡單的問題有史學與哲學的兩類解答。*章太炎早期所作《訄書》中就有《尊荀》、《儒道》、《儒法》、《儒墨》、《儒俠》、《儒兵》諸多對傳統儒家學說的評論,尊崇孔子、荀子,但對舊說圣人如堯舜湯文武周公等則不然,因為力主改革的章太炎主張“法后王”。他1909年作《原儒》,后收入《國故論衡》(1910年),辨析古代和后人對“儒”的不同解說,認為“儒之名,于古通為術士,于今專為師氏之守”(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170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基本上是一個歷史學家視域中的“儒”。熊十力先生則于20世紀50年代作《原儒》一書,重在發展其立足于“心本論”而來的“內圣外王”的哲學思想,一開始就是《原學統》:“一、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來圣明之緒而集大成,開內圣外王一貫之鴻宗。二、論定晚周諸子百家以逮宋、明諸師與佛氏之旨歸,而執中于至圣。三、審定六經真偽。悉舉西漢以來二千余年間,家法之墨守,今古文之聚訟,漢、宋之囂爭,一概屏除弗顧。獨從漢人所傳來之六經,窮治其篡亂,嚴核其流變,求復孔子之真面目。而儒學之統始定。”(參見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六卷,311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熊先生之儒的“學統”實為“道統”,多為出于己意之創說。我以為,今天對它們的澄清,不必限于某家的定義,應該回到社會史,考察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如何使用這些概念。所謂“儒”,其意義在前現代中國有多重性。在學術的層面,它是指“儒學”,即研究歷史上的儒家經典與同時代儒家著述的學問或學科,傳統的經史子集四科之學都可以包括在內。從信奉一套價值、生活方式以及共享某些思維方式的角度說,它是一個政治—文化社會派別,可以稱作“儒家”。認孔子為宗主,共享某種信仰,包含了梯里希所謂的“終極關懷”或者現代新儒家自己強調的“內在超越”,并以此來規范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也可以說是“儒教”。儒家、儒教兩個名稱都和社會建制有關系,所以海外漢學家常常會使用所謂“儒家社會”或“儒教社會”的概念。由此可見,儒家或者以認同優先的方式研究儒家學說的“儒學”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儒教*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與此相應的是系統分析的方法:將儒家看成一個整全而復雜的大系統,它內部包含三個互相聯結又互有分殊的子系統。第一個是儒學經典義理系統,特別是經學系統。由于“經學必專守舊,世世遞嬗,毋得改易”的特性,經學內部盡管也有不同的派別,但總體上有較大的連貫性。無論今古、漢宋,都承認與尊重他們有一套共同的經典。第二個是儒家文化系統,是文學、史學、政治話語之體現。它可能包含了在長期發展中儒家自身不同進路的演進,以及和其他來源有異的思想(譬如佛教、道教甚至基督教的早期傳播)的融合。第三個是儒家社會系統或“儒教社會”,主要是社會、倫理、政治制度、風尚習俗及其中包含的觀念等。籠統地所稱的“儒家社會”,指社會倫理的基礎是儒家的,但是實際上在社會生活、制度、習俗等等中間,法家、佛教、道教(家)也都有自己的角色。“儒表法里”和“三教融合”都是人們對儒家社會復雜性的認知。,都不但表示一套思想觀念和價值,而且表示對其生活方式的忠誠。
就最基本的文化認同而言,古代社會的“儒家”是指以孔子為宗主、以六經為基本經典、以“仁義”為核心價值、以“禮”為可以有所損益(事實上也不斷有所演變)的建制這樣一個政治—文化派別;就其社會階層來說,儒家又特指鄉紳—士大夫—官僚三位一體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集團(這些精英集團內部中人也許有另外的信仰如佛教、道教)。古代儒家本來不是單一的宗教組織或學術團體。孔子以后,儒分為八,先秦即至少有思孟和荀子兩大流派。按照《淮南子》的說法,墨子也曾“學儒者之業”,后來才自立門戶。荀子之后學則有著名的法家李斯與韓非,兩千年的中國社會雖可以籠統地稱為儒家社會,其實是儒表法里。經過兩千年的傳承,盡管每一個朝代的儒學都有主流與潛流、中心與邊緣,甚至有正統與異端的種種分流,但是,由于儒學與政治的緊密關系,“一代有一代之學”,即意味著歷史上每隔數百年通常都劃分了儒學的“范式”,而同一時代的儒者通常共享著一套觀念共識。由于有這樣一套觀念共識,盡管儒家內部有種種爭論,儒家集團卻保持著基本的社會團結,即其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是基本穩定的。
19世紀中葉以后,上述情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來的變化。此變化經過數十年的醞釀發酵,到19世紀末甲午戰敗點燃了導火索,價值迷失與政治敗壞相遇,知識精英與政治主導在國家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促使儒家集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由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共同組成的儒家共同體迅速瓦解。
在此之前,主導儒家精英的思想路徑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經蘊含著融攝西學為儒學所用的意義,其本意是在獲得變革的動力之同時捍衛傳統之秩序。我曾經把它稱之為現代保守主義的第一個綱領。[12]它與單純的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表達了對新的國際環境之下中西文化沖突的初步概念化。如果放在更長的時段考察,它其實已經孕育著現代新儒家的方向。以往的西方漢學家把宋明理學稱作“新儒學”,它的“新”,在于汲取了佛老又排斥佛老,發展出一套更具哲學意味的理論。宋元明以降,儒釋道三教合流成為大勢。而現代新儒學之“新”,很大程度上是在回應和融攝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在經典世界有所根據而又適應現時代需求、希望能夠對治現代生活的理論。這樣一個過程,在時間向度上應該往前追溯;而在“現代新儒學”所覆蓋的范圍和解釋厚度上,則應該注意到從傳統的四科之學到現代學院制度之建立之間所帶來的學科的多樣性、風俗的流變和建制的過程。
前面我們討論到19世紀末儒學內部呈現的新變化,即將儒家精英集團和儒學內部的分化看成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起始階段。具體而言,提倡“中體西用”論的張之洞等屬于儒家是沒有爭議的,但在“中體西用”論實際支配了19世紀后期幾乎三十年的儒家精英集團以后,由于甲午戰爭的失敗,堅持此論者迅速被視為保守的一翼。從“中體西用”的儒家精英集團中分化出了政治上被稱作“改良派”的群體,戊戌時代的它近乎一個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聯盟:以康有為為首腦,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之先驅;從思想史與后來的歷史影響而言,其實還應該包括嚴復、章太炎。當然,這一群體迅速再次分化,十年左右的時間即一分為三:康有為最為復雜,也最有原創性。在他那里激進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兼而有之,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處理不同的問題時有不同的表現。20世紀初他成為保守的符號。梁啟超、嚴復等是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譚嗣同被視為20世紀激進主義的源頭,就曾經具有“革命”主張和對傳統儒學的批判而言,20世紀初的章太炎之激進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章太炎本來是古文經學的最后一個大師,其講“國粹”,晚年“粹然成為儒宗”,并有“回真向俗”的轉向,說其屬于儒家完全成立。但是,他不僅是革命家,而且曾經主張無政府主義,更對西方代議制民主持否定態度,認為中國可以實行“聯省自治”下的直接民主,其實都顯示了相當激進的姿態。
上述判斷需要稍作展開。無論康有為的“舊瓶裝新酒”如何震撼了傳統儒家,無論其《大同書》如何驚世駭俗,康有為之屬于儒家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不過,借公羊學的形式來闡發其得自域外和時代創獲之綜合,則遠遠超出了宋明理學的“新”。盡管說康有為是“舊瓶裝新酒”,其主旨在政教,在玄學的構造上也沒有那么成功,但其學說依然用一種新的形態闡發了這樣一種終極關懷的雙重走向,即將原始儒家從天的信仰下貫為“仁”及由“不忍人之心”擴充而為“大同”。康有為的追隨者譚嗣同、梁啟超,也都是把“仁學”和“大同”聯結在一起。救亡圖存固然是他們運用儒家資源來構筑理論的直接動力,但是未來人類的理想境界,可能是推動這批傳統士大夫投身社會運動的更深層的動因。人們說康有為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最具創造性的人物之一,就以《大同書》而言,其氣魄之闊大,在20世紀儒家中可謂后無來者,其影響所及也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儒家,因為他同時吸收了諸多學說。與其相比,自覺“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的陳寅恪就主張“以新瓶裝舊酒”[13](P462),已經退守至如何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不忘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梁漱溟以后的新儒家則依違在兩者之間,或者是這兩種方式的哲學綜合。
同理,無論譚嗣同如何激進,如何否定傳統政治,但“他仍然承襲了儒家對人生的道德取向,在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和完美的人格”*張灝先生對譚嗣同思想的儒家源頭以及儒家思想與大乘佛學、先秦子學等的緊張關系有細致的分析,尤其指出了古代儒家就具有的抗議精神如何在譚嗣同那里得到突出的表達。參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96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而且他的學術方向終究是《仁學》而不是其他。“《仁學》何為而作也?將以光大南海之宗旨,會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為宗旨,以大同為條理,以救中國為下手,以殺身破家為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14](P373)張灝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比較詳細分析了,“由張載和王夫之的哲學發展而來的新儒學世界觀”是譚嗣同演化其“仁”的概念的原初本源。[15](P95-122)譚嗣同心目中的宗主還是孔子,融貫儒釋道墨與西學可以采納者,是救世與救心的途徑。這一翼中某些人物政治態度一時的激進,并不完全改其儒家本色。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在對待帝制的問題上,實際上比康有為更為激進:梁漱溟和熊十力都參加過辛亥革命,20世紀50年代以后,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儒家社會主義傾向。因其在價值排序中主張平等優先,而我們通常把社會主義視為現代社會中激進的一翼。
至于自由主義的先驅嚴復、梁啟超*梁啟超與儒學(家)的關系之深,無需贅言。嚴復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其思想的復雜性而需要略加闡發。盡管嚴復曾經對正統儒家有過激烈的批判,我們依然不能把他看做與儒家絕緣的人物。這并不僅僅因為他參加科舉、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才獲得“進士”身份,也不僅僅因為他晚年參與“孔教會”、卷入“籌安會”的活動,同時也因為從分析其知識世界得出這一結論。大致說來,他對于傳統儒學有分析地汲取:對待漢宋之爭,他崇宋而抑漢;同是理學,他批評王學“師心自用”、取“道問學”的立場,但又贊揚王學悲天憫人的道德感。在“群己之辨”上,他游弋在“群重己輕”與“群己兼顧”之間,并不是原子主義的個人主義。在“天人之辨”上,他上承荀子、劉禹錫、柳宗元即儒學中強調“天(自然)人相分”的一脈。至于其進步主義的歷史觀,更是從易學的變異理論獲得傳統思想的基礎。他晚年則更回到原始儒家:“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尚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武器發掘淘煉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古今社會移動之點。”參見嚴復:《與熊純如書(五十二)》,載王栻 、嚴復:《嚴復集》,第三冊,66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無論是其最初的教養背景,還是晚年思想的歸宿,都顯示出對儒家的文化認同。中國的自由主義固然有更為西化的一翼,但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新儒家內涵著自由主義的另一脈:張君勱后來曾經參與設計中國的憲政。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是,如何在儒家心性論的基礎上“開出”科學與民主。徐復觀在和自由主義論辯的過程中,對自由主義不乏同情的理解,以至于“儒家自由主義如何可能”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總之,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應對現代性的過程中,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演化為一部“三國演義”,但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一百多年前儒家精英集團分化的結果。“道術而為天下裂”,由于“思想”已經進入現代社會的“三個市場”之中,在開放條件下上述分化的三者有時似乎顯得勢同水火。但是,由于它們終究是“中國的”或“中國人的”,所以內里總有傳統的因素,總有屬于“儒”的一部分。不過,內里到底是何種“儒”,它與其他文化要素如何結合,以及傳統由此發生了什么變化,可能就言人人殊了。
三
當年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曾經引起持久的爭論,尤其是在《孔子在共產主義中國的地位》一章中,列文森斷言孔子已經被珍藏在博物館里:“與儒家推崇的孔子不同,共產主義者時代的孔子只能被埋葬,被收藏。現在孔子對傳統主義已不再起刺激作用,因為傳統的東西已經被粉碎,孔子只屬于歷史。”[16](P342)如果把儒學視為只能以整全的觀念存在的話,列文森所言不虛。*余英時先生對此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有過論述:“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史,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范圍之內。”(參見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載《余英時文集》,第二卷,318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這可以看做一個整全的儒學(或儒家)的概念。現在的評論者通常只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使列文森懷疑自己的結論。其實,列文森的那本書沒有注意到現代新儒家中的梁漱溟、熊十力和馮友蘭,也沒有注意到海峽彼岸的新儒家的工作,當然更沒有注意到儒家傳統有其根深蒂固的部分,隱身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社會風俗和法律制度之中。從觀念史研究的角度,我們可以對當時的(同時也是歷史上的)“儒”采用三分的方式:(1)在后經學時代以一種“返本開新”方式通過詮釋儒家經典來闡發的觀念,它以經學為核心;(2)沉積在一般文學、歷史中的儒家觀念,包括正統的和異端的——其定位通常因政治形勢而改變,它可謂是文化—心理的;(3)體現在風俗與政治法律、政策制度中,它是建制化的觀念。我之所以說它們不在“顯學”狀態,是因為第一類在中國大陸未能被主流意識形態接受,后面兩類已經發生了現代性的轉變,有時甚至以“反儒”的面目出現。*此類問題相當復雜,實際上又關系到另一個重大問題的解答:儒家傳統在中國現代化(以經濟起飛為特征)中起了何等作用?因為在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話語中,一方面,他們指責由于五四運動打斷了傳統,所以現代化長期止步不前;另一方面,他們一直堅信儒家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本土資源。而僅僅這樣的論述是無法解釋當今中國崛起的原因和現實的。從學術的角度說,在討論中國經驗或中國道路的時候,我們非常期待能夠出現論述儒學傳統如何正面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著作。
與熊十力有直接師承關系的港臺新儒家,繼承了“返本開新”的路徑,在融攝西方哲學的某些派別的過程中發展了儒家哲學,“是對西方文明強力的沖擊的回應”。[17](P138)不過,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港臺那樣的言路條件下,他們中的部分學者依然采取比較審慎、內斂的態度,對外主張以“文明對話”化解“文明沖突”;同時認為即使視儒學為“生命的學問”,以“內在超越”的方式呈現其“精神性”(這是他們對儒家的宗教性的一種修辭),儒學也只是多元社會的個人選擇。其“道統”論所包含的獨斷論與權威主義色彩尚不強烈。所以,我認為它們作為保守主義本質上是防御性的。或者按照亨廷頓的說法,其依然是一種方位性的意識形態(a positional ideology),而不是捍衛特定制度的理論。
歷史的發展總有其吊詭的面相。從研究現代新儒家哲學(尤其是港臺新儒家)開始,三十年間,儒學在中國大陸迅速復活。它與港臺新儒學有所不同,正如李維武教授所指出的:“如果說此前的現代新儒學具有深刻的學術性,并對20世紀的中國學術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那么中國大陸新儒學則具有強烈的現實參與性,所思考和關注的重心是當代中國重大現實問題,特別是‘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它包括以政治儒學興起為標志的儒學的政治化、以提倡建立儒教為標志的儒學的宗教化以及以儒學走向民眾生活為標志的儒學的大眾化。[18]與梁漱溟、熊十力以后的新儒家偏向于宋明理學(尤其是陸王心學)與西方哲學的融合不同,在近二十年大陸新儒學研究中,荀子——以及多半因為荀子“隆禮”而禮學——受到的關注明顯增加,同時康有為重新觸發了儒學研究的靈感。因為20世紀初期,正是康有為曾經極力提倡建立儒教,其從公羊學出發來建立現代社會秩序的方式,被一些學人視為從文化的闡釋者變身為立法者的最合適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大陸出現的這一情勢已經表示現代新儒學不再是防御性的或者單純保守主義的,它們對中國的現狀明顯有著相當激進的態度。
上述變化自然有其內在的根據:一方面,一個有著悠長連續性的傳統在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后并未徹底斷裂,如前文所述,即使在列文森那樣的外部觀察者以為孔夫子進了博物館的時代里,儒家倫理乃至政治文化依然隱身于激烈變革的現實之中;另一方面,經濟建設時代意識形態的挑戰,需要可以提供秩序重建的多重資源——尤其是在本民族中根深蒂固的傳統——共同發揮作用。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曾經意味深長地說過:“新儒學是時代和社會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時代和社會。”[19](P1360)當代世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依然是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崛起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置身于此,確實需要建立更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精神權威,而現代新儒學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選項。當然,這里的“權威”即理想或者說合理的價值體系,它應該是令人心悅誠服的社會共識,而非獨斷的教義。用返魅的方式還是用充分發展論辯合理性的方式來建立社會共識,雖然有種種歷史的偶然性在其中起作用,但作為學人總應該有基本的自覺。展示現代中國的思想光譜希望于此有所裨益。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載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2][3][4] 賀麟:《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5]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總序》,載方克立主編:《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6] 賀麟:《近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9][10]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2] 高瑞泉:《秩序的重建:現代新儒學的歷史方位》,載《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
[13]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14] 梁啟超:《仁學序》,載蔡尚思、方行主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5] 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6]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7] 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18] 李維武:《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的總體走向與基本歷程》,載《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19] 陳旭麓:《陳旭麓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責任編輯 李 理)
The Changing Spectrum——Modern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Study
GAO Rui-q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With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the reference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is also being expanded.Within “Modern Neo-Confucianism”,there exist different concepts of “orthodoxy”.If we break through the concept of “orthodoxy”,which is similar to genealogy,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could come down to a theory that forms during the process responding to and assimilating western culture.Based on the classical world and capable of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age,it can be expected to cop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 life.The starting point of its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fucian elite group that is represented by Kang Youwe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However,it turns out that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includ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ism,Confucianism,which used to be a defensive and orientational ideology,begins to show its radical attitude to changing the reality,thus giving rise to a vastly different ideological spectrum of “Modern Neo-Confuci ̄anism”.
Modern Neo-Confucianism;orthodoxy;Kang Youwei;ideological spectrum
高瑞泉: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200241)
* 本文之寫作緣起于作者2015年初于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主持的“經典、經學與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由于談及康有為是現代新儒家的先驅,蔣國保兄認為大有爭論余地,其實這并非我一時的感想,近十年前已經在其他地方有所論及。而干春松教授則力促我撰寫成專文,又承《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李淑英編審的盛情邀約,遂將相關問題一并論述。雖倉促成文,未能盡言,對上述諸位朋友的關注仍心存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