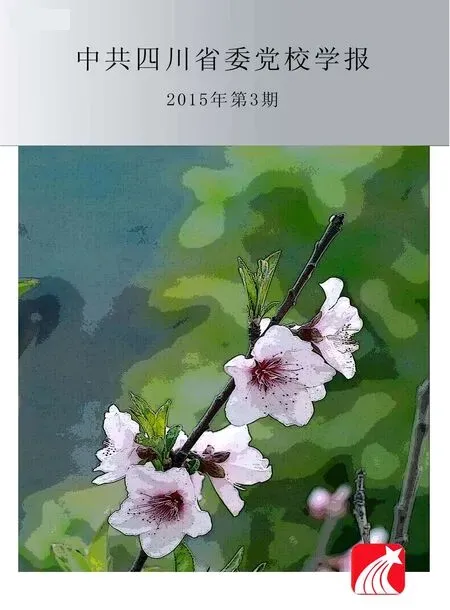加快推進成都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明 亮 王 蘋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四川成都 610016)
加快推進成都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明亮1王蘋2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四川成都610016)
[關鍵詞]治理;流動人口;少數民族
[摘要]民族事物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成都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聚集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迫切需要通過推進民族事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針對當前所存在的民族事物工作機制不健全,少數民族人口社會融入程度較低等問題,應建立和完善多元主體參與的現代民族事物治理機制,堅持以法治思維處理涉及少數民族人口的矛盾糾紛,著力提高公共服務質量水平,大力促進少數民族人口社會融合。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鑒于成都市作為西部少數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人口眾多,民族間交往頻繁,需要加快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的建設,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成都市少數民族人口狀況
作為緊鄰民族地區的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我市獨特的包容文化氛圍、便利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宜人氣候,使其長期以來成為西南乃至整個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的主要遷居地。其少數民族人口具有以下特征:
1、少數民族人口規模大。包括回族、藏族、土家族、滿族、羌族和彝族等55個少數民族在內的常住人口達12.69萬,戶籍人口10.67人。這些少數民族同胞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態分布于全市范圍內。因民族習慣和來源地等方面的差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聚集區域有所不同,如來自甘孜的藏族習慣聚居在武侯、高新和雙流;而來自阿壩的藏族習慣居住在金牛、郫縣和都江堰。
2、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眾多。根據成都市流動人口綜合信息平臺2013年4月采集的數據顯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6.88萬人,占全市流動人口總數的1.48%。實際上,在成都務工、經商、就學、就醫和旅游的少數民族人口群體具有頻繁的流動性,隨季節變化而在民族地區和成都之間進行鐘擺式流動,年均少數民族流動人次達400萬。成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以來自省內甘孜、阿壩、涼山三州為主。近年來,伴隨著成都區域中心城市作用越來越明顯,來自西藏、青海、甘肅、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人數也在逐年增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聚集區域包括一圈層的武侯、金牛、和高新;二圈層的雙流、郫縣和溫江;三圈層的都江堰、崇州和大邑。
3、少數民族人口構成復雜,從業分散。成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身份比較復雜,包括離退休干部、商人、僧侶、演藝人員、學生和一般務工者等各類人群。不同民族、不同來源地決定了其就業模式各不相同,如藏族以展演民族歌舞、經營建材和民族商品為主,彝族集中在建筑行業務工,維吾爾族則以銷售干果和販賣瓜果居多。同一民族的相同從業者往往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團,集中在某類行業,并排斥其他經營者。
二、成都民族事務治理存在的問題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近年來在成都居住、工作和從事經濟活動的少數民族人口逐漸增加。成都市民族事務治理面臨的各種因素更加復雜,城市民族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工作方式也面臨更大的挑戰,暴露出很多問題。
1、民族事務工作機制不健全
從總體上來講,一是有的部門對于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對城市民族工作的規律性、特殊性、復雜性等認識不到位,存在將民族事務工作簡單地等同于民宗部門工作的現象。二是民族工作組織領導機制還不夠健全,工作網絡體系、聯席協調機制、信息共享機制尚不完善。三是民宗部門工作力量較薄弱,少數民族居住較多的社區干部,特別是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干部較少,既無法精準把握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基本情況,又難以深入細致的開展管理和服務工作,管理和服務工作缺位現象較為突出。四是民族事務工作還沒有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民族工作事務處理隨意性大,“花錢買平安”的現象還比較突出。
2、涉及少數民族群眾的矛盾糾紛調解機制和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還不健全
伴隨著我市少數民族人口的日益增加,與部分少數民族群眾有關的經濟糾紛、醫患糾紛、購車糾紛、合同糾紛和勞資糾紛等事件多發。由于相關的矛盾糾紛調解機制還不健全,導致部分糾紛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致使矛盾累積成為影響城市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極易引發突發事件,需要立即予以高度重視,不斷完善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
3、部分少數民族群眾的社會融入程度還比較低
一是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對城市管理和城市生活的規則認同度不高。由于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公民意識和法制觀念較為淡薄,部分少數民族人口還無法適應現代城市生活。表現為拒交物管費和停車費,占道經營等問題。與現代城市生活秩序和城市管理原則矛盾較大。二是個別少數民族人口的越軌行為比較突出。部分少數民族人員違法犯罪問題成為我市治安管理的難點。三是成都市民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排斥現象較為明顯。極少數少數民族人口對現代城市生活秩序的破壞引起了部分成都市民的排斥,特別是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排斥較為明顯。如“拒住”、“拒載”和就業歧視等,對少數民族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利影響。
4、少數民族群眾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
伴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聚集和族群規模的擴張,少數民族人口群體的公共服務問題日益顯著。不同民族、不同身份背景和從事不同行業少數民族群眾的公共服務需求具有較大差異性,而當前我市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還難以滿足少數民族人口(特別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多元化公共服務需求。
三、加強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對策建議
民族事務治理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維護國家整體利益,促進和諧民族關系構建。各部門應站在國家利益、全局利益的角度看待民族政策。民族事務治理理念要求治理主體多元化,民宗部門是民族事務的主管部門,但不是民族事務治理的唯一主體。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講,只有民族事務治理主體多元化、職責明晰化,才能提高民族事務治理的系統性、協同性和科學性,這將是今后我市建立和完善民族事務治理體制機制的重要路徑和方向。
1、完善民族事務治理體制機制
當前我市民族事務工作的難點在于民族事務治理主體單一,一些涉及專門領域的問題民族工作部門無法管理,而業務主管部門又存在不愿或不敢管理的現象。鑒于此,應進一步明確相關職能和管理部門在民族事務治理中的職責,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和多元主體參與的城市民族事務治理體制機制。一是要加強統籌協調機制建設,建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負責,統戰、民宗、公安、城管、教育、民政和稅務等多部門參與的民族工作綜合協調機制。二是要加強職能部門之間的協作,在成都市民宗工作領導協調小組的領導下,形成以民族工作部門為主體,以公安、城管、工商、民政等職能部門為輔的橫向協調機制。三是要充分發揮“一市三州” (成都市、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聯席會議機制,“一局三辦”(成都市民宗局和甘孜、阿壩、涼山州駐蓉辦事處)聯席會議制度等平臺的積極作用,加強流出地與流入地的協同管理,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四是要加強民族工作隊伍建設,特別是要充實少數民族人口聚集地區民宗部門的工作力量。
2、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協調和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處理涉及少數民族矛盾糾紛時應遵循的第一準則,任何人違反了法律法規都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而不能因其民族差異而有所改變。同時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滿足其合理合法訴求。堅持依法辦事和人性化執法相結合,絕不能以“花錢買平安”的方式來處理涉及少數民族的矛盾糾紛;要加強民族事務工作方式和方法創新,吸引那些具有語言優勢、熟悉民族事務工作和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的少數民族干部(包括離退休干部)、社會公益人士和專家學者在內的利益相關群體,搭建包括多元主體參與的矛盾糾紛調解機制。
3、促進少數民族群眾的社會融合
一是要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族事務治理的制度化。應廣泛征求各族群眾意見和建議,制定和出臺具有高度社會認同度的“民族事務工作辦法”,明確處理民族事務的程序和原則。加強法律援助制度建設,保護其合法權益。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為少數民族提供心理咨詢、社會救濟、社區矯正等專業救助。二是要加強民族理論政策、法律法規、基本常識和民族團結的宣傳教育,提高成都市民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認知度,增強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社會知曉度,營造民族團結的良好社會氛圍,降低乃至消除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排斥現象。三是要深入推進民族事務治理社會化,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民族事務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少數民族的服務工作,實現民族事務治理從政府一元單向治理向政府、社會、民眾多元交互共治的轉變,為少數民族早日融入現代城市社會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
4、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機制
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離不開公平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從營造公平的制度環境和提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水平兩個方面著手解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的社會融合問題。
一是要加大針對少數民族的服務工作力度。建立包括勞動就業、職業培訓、子女教育、權益保護、法律援助、文化交流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引導和服務機制,滿足少數民族群眾的多元化公共服務需求。充分發揮社區服務功能,在少數民族相對集中居住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鼓勵和引導民間力量在社區層面建立社會工作服務站,與社區合作或者獨立開展少數民族服務工作。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信息登記和采集系統,及時搜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破除戶籍制度障礙,逐步放開政策限制,賦予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重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群體在隨遷子女教育、勞動技能培訓、就業服務、醫療和社保等方面的權益保障問題,確保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能夠均等地享受關系到人的生存發展的基本公共服務。
三是要保障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基本政治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要建立以社區為載體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公共參與機制,賦予常住少數民族人口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現參加國家管理和參政議政的權利,允許外來常住少數民族人口參與競選社區工作人員,實際參與城市社會管理服務。
(責任編輯:周建瑜)
[中圖分類號]D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5955(2015)03-0073-03
[作者簡介]明亮,男,成都市社會科學院社會與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王蘋,女,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收稿日期]201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