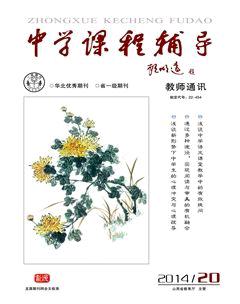少點無聊的爭辯 多點真情的熏染
陳彩珍
《羚羊木雕》是人教版語文七年級上冊第五單元的一篇選文。編者在本單元的“導讀提示”中就有這樣的話語:“濃濃親情,動人心弦。親情是人間真摯而美好的感情,描寫親情的詩文往往最能打動人。在本單元這幾篇課文中,作者以自身的切身體驗,寫出了親情的豐富和多彩,引起我們的共鳴。”可見,編者的良苦用心是立足于親情,以文章的真摯親情打動學生的心靈。可惜,在課后的“研討與練習”第三題里是這樣設計的:“分甲、乙、丙三個小組,甲方代表“父母”,乙方代表“我”,丙方代表“萬芳”,就這一場家庭矛盾的是非展開辯論。要注意擺事實講道理,并根據自己所代表的人物身份,掌握好說話的分寸。”于是,就出現了如下的課堂鏡頭:
學生分成甲、乙、丙三組,先組內討論,然后代表辯論,課堂熱鬧非凡。辯論的結果是:我責怪父母勢利,不體諒孩子間友情;萬芳也認為我的父母不應該逼迫我要回羚羊木雕,而傷害了友情;父母認為孩子不能夠送那么貴重的禮物,這是為孩子著想。這樣的辯論最終成了爭辯,甚至是指責,仿佛父母是一切過錯的源頭。
這樣的課堂場景很普遍,甚至在許多縣市級的公開課上也屢見不鮮。這顯然不是我們所想要的課堂,然而又反復出現,為什么?這不得不引起我的再思考。
思考之一:編寫目標與問題設計的自相矛盾。本單元的編寫目標顯然是立足親情,讓學生在豐富而多彩的故事中體驗親情的溫暖。但是,課后的研討與練習卻將這份親情演變成了一場爭辯,而爭辯的結果恰恰是父母成了指責的對象。這叫“親情”情何以堪!我想不妨這樣設計:“父母要我向萬芳要回羚羊木雕,難道僅僅是因為羚羊木雕貴重嗎?請用心揣摩父母的心。”
這樣的問題就避免了淺層次的爭辯,把學生的閱讀思路引向深入,引領學生透過父母嚴厲逼迫我要回羚羊木雕的表象去探究父母的真心,去體悟那份嚴厲中的親情。
思考之二:編者問題的設計顯然違背了語文的基本規律,是一種“思想品德課”式的說教。語文不能靠簡單的事例去教育學生,而是通過文本的情感體驗來感染學生,是熏染。
這樣的爭辯是蒼白的,只有真摯情感的熏染才是動人的。如果沿著筆者的設計思路,學生結合文章的相關語段,就可以明白:父母這樣嚴厲地要我向萬芳要回羚羊木雕,是有更深的心思。
“羚羊木雕是爸爸從非洲帶回來給我的”;“小朋友之間不是不可以送東西,但是,要看什么樣的東西……”;“不是媽媽不懂道理……就是爸爸媽媽也舍不得送人啊!”
羚羊木雕,是父母對女兒一份祝福、疼愛與期望的寄托,就像生活中有些家長捐了很多錢為孩子祈福換來一串手珠一樣,那是寄托著父母對孩子所有的美好祝福和愛。你把它送人了,不僅是因為貴重,更是把父母心中的那份對女兒的美好寄托破滅了,你讓父母在情感上如何能接受?
因此,透過羚羊木雕,我們不能只在表面上讀到父母的勢利、不守誠信等負面的信息,我們更要明白:這是另一種愛,一份濃烈的親情。
思考之三:教師對文本缺乏深入的品讀,無法主宰教材。我們一直提倡“用教材教”,要想“用教材教”,你就必須對教材有足夠的把握,有自己的見地,必須主宰教材。然而,許多教師的課堂教學一直依賴于《教參》和課后練習,成了教材的附庸。其實,在文章的末段這樣寫到:“可是,這能全怪我嗎?”請注意“全”字。這表明雖然我心里有怨氣,但我已經知道自己的錯誤,我知道我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再一味地責怪父母。
如果我們的課堂教學如筆者這樣進行,那還需要爭辯嗎?孩子已經感受到父母嚴厲背后的那份深情,孩子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不就是親情嗎?這正是編者所想要的目標,更是語文課堂所追求的景象。
(作者單位:福建省古田縣玉田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