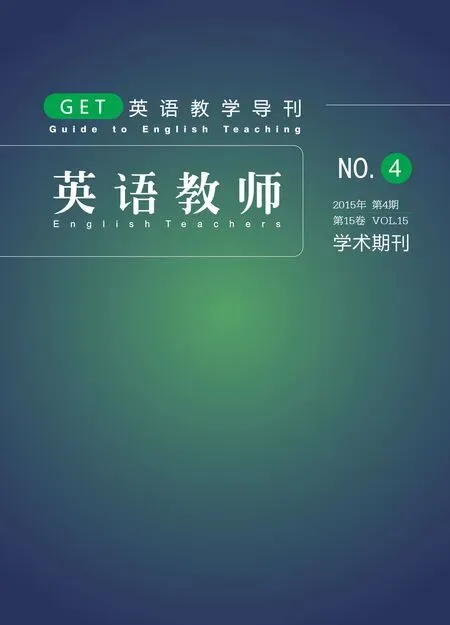中學(xué)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的環(huán)境分析
王彩琴
中學(xué)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的環(huán)境分析
王彩琴
【摘要】教師作為一種專業(yè),在我國已經(jīng)無需論證。基礎(chǔ)學(xué)段的教師自主專業(yè)發(fā)展能力已經(jīng)成為全社會期盼的焦點。教師在專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的角色從“研究者”到“行動研究者”再到“解放的行動研究者”,經(jīng)歷的不僅是身份和角色的變化,更是其深層次的教育教學(xué)理念及個體專業(yè)素養(yǎng)的提升。本文重點論述了中學(xué)英語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過程中影響“三者”角色發(fā)展的主要因素。
【關(guān)鍵詞】解放的行動研究者;“三者”角色;內(nèi)驅(qū)力
引言
“解放”(emancipation)”是英國課程專家斯騰豪斯的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理論的關(guān)鍵詞:“解放的本質(zhì)即……專業(yè)自主……通向解放的一條有效途徑,就是教師成為研究者(Teachers as researchers)”(Stenhouse.L. 1983)。
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得以完善的生態(tài)過程,其中的“他助性”成分越弱,教師的主體性作用就越突出,“自助性”意識和能力就越強大。澳大利亞學(xué)者凱米斯(Kemmis,W. C. S. 1982)認(rèn)為,“專門職業(yè)”有三個顯著的特征:其成員以顧客的利益為壓倒一切的任務(wù);其成員不受專業(yè)外的勢力控制和限定,有權(quán)作出“自主的”職業(yè)判斷;這種“專業(yè)自主”既是個人的,也包括集體的,即在特定的情境中可以自主選擇特定的行動,有權(quán)從整體上決定各種政策、組織和實施程序。凱米斯認(rèn)為,若按照以上標(biāo)準(zhǔn)來度量教師的教學(xué)活動,稱其為“專門職業(yè)”則有些勉為其難。因為教師少有研究意識,而且嚴(yán)重缺乏“專業(yè)自主(theprofessionalautonomy)”。
我國教育部自2001年啟動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到2010年與財政部聯(lián)合實施的大規(guī)模、有計劃的國家級中小學(xué)教師培訓(xùn)項目(簡稱“國培計劃”),都旨在“針對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需求,通過主題式培訓(xùn)、研究問題、分析案例,總結(jié)提升經(jīng)驗,提高師德修養(yǎng),更新知識,提升能力”(教育部2012)。“國培計劃”的實施已達(dá)五年,中學(xué)教師的行動研究能力及研究者的角色發(fā)展現(xiàn)狀如何?這五年來,哪些主要因素影響著中學(xué)教師的行動研究能力及角色發(fā)展?筆者力圖在本文中以中學(xué)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來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一、國外關(guān)于教師作為“三者”角色的主要研究
為了幫助“教師成為研究者”,斯騰豪斯成立了“教育應(yīng)用研究中心”,引領(lǐng)教師的自我解放,鼓舞了眾多的中小學(xué)教師及曾經(jīng)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埃利奧特和凱米斯就是其中的兩位重要人物。
擁有中學(xué)工作經(jīng)驗的埃利奧特更愿意使用“教師成為行動的研究者”(Teachers as action researchers)來表達(dá)他對教師自主專業(yè)發(fā)展的期望。埃利奧特的研究價值在于區(qū)分了兩種教師變革實踐的方式:思先于行(Reflection initiates action)和以行促思(Action initiates reflection)。前者強調(diào)“先轉(zhuǎn)變觀念,逐步完善教學(xué)策略”,教師將其他研究者提出的方案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從而改變自己的教學(xué)。后者強調(diào)“先改變教學(xué)策略,逐漸轉(zhuǎn)變理念”,教師針對某些實際問題改變自己的教學(xué)方式,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我監(jiān)控、評價,最初對問題的理解有望在評價的過程中得到修正和改進(jìn)。埃利奧特認(rèn)為斯騰豪斯提出的“教師成為研究者”屬于“思先于行”,可能導(dǎo)致有學(xué)術(shù)偏見的研究方案造成研究和實踐(采取行動)的剝離。所以,埃利奧特倡議“教師成為行動研究者”,將研究和實踐(采取行動)融為一體。埃利奧特的“以行促思”對斯騰豪斯的“思先于行”是一種教師專業(yè)的生態(tài)發(fā)展。
凱米斯將行動研究分為三種:技術(shù)性行動研究(technical action research)、實踐性行動研究(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和解放性行動研究(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鑒于教師的研究意識較弱,嚴(yán)重缺乏“專業(yè)自主”,凱米斯認(rèn)為,教師只有通過親自進(jìn)入研究來解放自己和自己的專業(yè),才有可能進(jìn)入自主專業(yè)發(fā)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為此,凱米斯把斯騰豪斯的“教師解放”和北愛爾蘭學(xué)者麥克爾蘭的“批判性行動研究(Critical action research)”加以融通,倡導(dǎo)“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Teachers as 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ers)”。是現(xiàn)實的實踐環(huán)節(jié)。“教—學(xué)—研”不僅是一個融合互補的整體,而且存在一種生態(tài)制約的關(guān)系。
二、國內(nèi)關(guān)于教師作為“三者”角色的主要研究
黃遠(yuǎn)振和陳偉振兩位教授是國內(nèi)較為系統(tǒng)地研究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生態(tài)的學(xué)者,他們認(rèn)為,中學(xué)教師有其從事教學(xué)研究的獨特優(yōu)勢。首先,中學(xué)教師的“在教學(xué)中研究”能有效促進(jìn)研究與教學(xué)之間的“共生互補”關(guān)系。第二,中學(xué)教師“在做中學(xué)”的研究是高效的學(xué)習(xí)模式,因為閱讀、合作、研究是促進(jìn)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三種方式,其中以“研究”最為有效。
黃遠(yuǎn)振和陳偉振兩位教授的研究(2010)證明,“教—學(xué)—研”組成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框架。首先,“教”是“行”,是教學(xué)實踐和體驗的場所,“學(xué)”就是“知”,是獲取理論知識的途徑。“教”決定“研”的方向,“研”決定“學(xué)”的內(nèi)容,“研”能提升“教”和“學(xué)”的品質(zhì)。其次,“學(xué)”為“教”和“研”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資本,使知識處于不斷生成和發(fā)展的狀態(tài)。第三,“教”既是教師活動的場所,又是生活的內(nèi)容,還是教師參與知識的一種方式。“學(xué)”是教師參與知識的另一種方式,發(fā)生在教育研究活動過程中。“研”即教育研究,是教師自主發(fā)展的運行過程,
三、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的環(huán)境需求
中學(xué)教師要想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需要兩種環(huán)境的支撐,且兩種環(huán)境之間要保持良性的互動生態(tài),這就是外在的發(fā)展環(huán)境和內(nèi)在的發(fā)展驅(qū)動力。
(一)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的外在環(huán)境
從教師發(fā)展生態(tài)的源頭看,高等師范院校是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首要階段。中學(xué)教師的前身都是高校的師范生,而我國的師范教育課程設(shè)置明顯偏重學(xué)科專業(yè)課程,教育學(xué)類課程只設(shè)公共教育學(xué)、公共心理學(xué)和學(xué)科教學(xué)法,高校的師范生很少接受教學(xué)與教育研究方面的系統(tǒng)訓(xùn)練。如:某所高等師范院校的英語師范類培養(yǎng)方案中的“教師教育平臺課程有11個學(xué)分,占總學(xué)分的6.8%;師資型人才培養(yǎng)方向的限選課有30個學(xué)分,占總學(xué)分的18.75%;實踐學(xué)分文科類專業(yè)要逸24學(xué)分”。該師范院校總計25.7%與教師職業(yè)相關(guān)的課程在具體操作層面多以大班額的理論講授為主,小班制的學(xué)生動手實踐機會很少。這就導(dǎo)致在職的中學(xué)教師從一開始就嚴(yán)重缺少從事教學(xué)行動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當(dāng)外來專家(facilitator)建議教師在其教學(xué)實踐中檢驗專家校外獲得的理論時,教師的行動研究就是“技術(shù)性行動研究”。當(dāng)外來專家以教師的伙伴身份出現(xiàn),幫助教師表達(dá)自己的想法,設(shè)計改革的行動策略,控制問題情境和各種變量時,教師的行動研究就是“實踐性行動研究”。當(dāng)教師在促進(jìn)者的幫助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共同體,能自我反思時,那么,教師的行動研究就成為“解放性行動研究”。技術(shù)性和實踐性行動研究只有暫時的意義,當(dāng)它們向共同體靠近、向“解放性行動研究”過渡時,才有存在的價值。
2012年,河南省教育廳啟動實施了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旨在“實現(xiàn)高等師范教育與基礎(chǔ)教育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共同發(fā)展,各課題組要立足實際,突出實踐研究、行動研究的價值取向,突出解決教師教育課程改革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研究成果要用于教師教育課程改革和教師教育工作之中”【河南省教育廳(教師〔2012〕829號)】。三年來,河南省內(nèi)各級各類高校承擔(dān)完成875項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課題,參與項目的高校教師大概有五千多人。然而,承擔(dān)教師教育課程改革項目研究的高校教師大都以“專家(facilitators)”身份出現(xiàn)在中學(xué)教師面前,所以,建議中學(xué)教師在其教學(xué)實踐中檢驗專家校外獲得的理論時,中學(xué)教師的行動研究就只是“技術(shù)性行動研究”。有些高校教師是以“教師的伙伴(partners)”身份出現(xiàn),幫助教師表達(dá)自己的想法,設(shè)計改革的行動策略,控制問題情境和各種變量,這樣的中學(xué)教師行動研究就是“實踐性行動研究”。技術(shù)性和實踐性行動研究只有暫時的意義,當(dāng)它們向共同體靠近、向“解放性行動研究”過渡時,才有存在的價值。
(二)教師成為“解放的行動研究者”內(nèi)在驅(qū)動力
在職教師教育是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生態(tài)的主體階段。筆者所在的課題組對近三年參與過“國培計劃”的127名農(nóng)村初中骨干英語教師進(jìn)行了一次“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行動研究能力調(diào)研(王彩琴2014)。結(jié)果顯示:
1. 38.58%的教師認(rèn)為科研能力能促進(jìn)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37%的教師認(rèn)為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培養(yǎng)科研能力的動力,25.19%的教師認(rèn)為兩者相互影響,1.57%的教師認(rèn)為沒有多大關(guān)系。
2.只有0.78%的教師認(rèn)為自己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強,14.17%的教師認(rèn)為自己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強。
3.大部分研究對象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專家所講內(nèi)容,很少主動問問題,只有7.87%的研究對象會經(jīng)常對授課教師所講的內(nèi)容提出質(zhì)疑。另外,只有4.72%的研究對象懷疑專家的觀點和權(quán)威,其他人基本上全盤接受;也只有11.8%的研究對象能對于專家所講內(nèi)容提出問題。
4.只有25.19%和4.72%的研究對象能夠“經(jīng)常”或“總是”將自己所學(xué)運用到教學(xué)實踐中,大部分研究對象不能運用自己所學(xué)的教育理論去解決自己教學(xué)中的真實問題,造成理論與實踐相脫節(jié)。只有39.37%和3.93%的研究對象善于根據(jù)問題和現(xiàn)實條件尋求合適的解決方案。只有33.85%和3.93%的研究對象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但是大部分的教師這方面的能力還比較薄弱。另外,雖然只有少數(shù)的研究對象能夠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但只有26.77%和1.57%的研究對象善于執(zhí)行解決問題的方案。
5. 13.38%的教師“非常愿意”參與教研活動,45.66%的教師“比較愿意”參與教研活動,0.78%的教師“不愿意”參與教研活動;61.41%的教師認(rèn)為科研活動對教學(xué)工作有幫助,38.58%的教師認(rèn)為科研活動是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15.74%的教師認(rèn)為與評價業(yè)績有關(guān),還有3.14%的教師是出于領(lǐng)導(dǎo)的重視才進(jìn)行教研活動。
由此看來,中學(xué)教師的行動研究能力和動力遠(yuǎn)沒有達(dá)到相關(guān)要求,他們?nèi)狈Φ牟恢饕茄芯拷?jīng)費、校領(lǐng)導(dǎo)支持或是擔(dān)心學(xué)生成績的下滑,而主要是對行動研究及自身角色轉(zhuǎn)變的決心、自信、堅持等專業(yè)精神層面的內(nèi)涵。
結(jié)束語
中學(xué)教師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性行動研究者”,首先,在他們接收高校師范教育階段,就要能夠享受到科學(xué)、系統(tǒng)的教師教育課程,使實踐教學(xué)的技能基礎(chǔ)得以夯實。同時,在其教師職業(yè)生涯的專業(yè)發(fā)展過程中,要有系統(tǒng)的獲得促進(jìn)者幫助的機會,形成自己的研究共同體,能自我反思。更為重要的是,中學(xué)教師要從“知、行、思”三方面做到教師角色的自我統(tǒng)合,積極體驗從“研究者”到“行動研究者”的角色轉(zhuǎn)變過程,對各自的教師課堂行動研究過程中的經(jīng)驗與困惑加以批判性反思總結(jié),提煉出能彰顯各自風(fēng)格、充分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的專業(yè)自主意識和能力,從而成為真正“解放的行動研究者”。
引用文獻(xiàn)
教育部.2012.“國培計劃”課程標(biāo)準(zhǔn)(試行)[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教育部.2012.中學(xué)教師專業(yè)標(biāo)準(zhǔn)(試行)[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教育部.2012.教師教育課程標(biāo)準(zhǔn)(試行)[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申繼亮.2007.教學(xué)反思與行動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王彩琴.2013.生態(tài)哲學(xué)視域下的河南省中小學(xué)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研究.2013JSJYLX005.
王薔.2002.英語教師行動研究.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
Elliott,J. 1991. Ac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hanges[M]. Bucking ham:Open University Press.
Kemmis,W. C. S. 1982. Becoming Critical:Education,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M]. London:The Falmer Press.
Stenhouse. L. 1975.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I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Stenhouse.L.1983. Authority,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本文是河南省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2014-JSJYYB-021】和河南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項目【2014BJY010】的成果之一。
作者信息:476001,河南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wangcaiqin99@163.com
wangcaiqin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