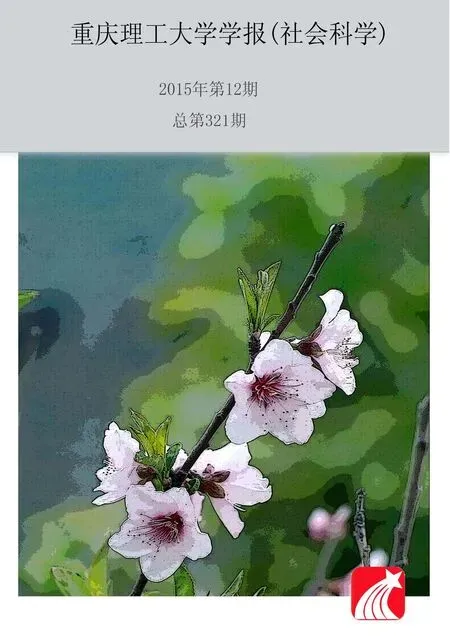論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理論基礎、現實困境與法律進路
張 力,劉小硯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論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
——理論基礎、現實困境與法律進路
張力,劉小硯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401120)
摘要:臨床試驗是新藥物、新療法在研發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而受試者作為臨床試驗法律關系中的弱勢群體,其權益極易受到侵害。受試者權益保護以生命倫理學和普遍人權理論為理論基礎,具有理論層面的必要性。同時,面對我國當前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不科學等現實困境,推進完善受試者權益保護也具有實踐層面的必要性。結合域外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有益經驗,我國可以從事前立法和實施制度進行規范,以及事后司法進行救濟等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臨床試驗;權益保護;生命倫理學;普遍人權理論;無過錯責任
中圖分類號:DF5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425(2015)12-0097-08
Abstract:Clinical trials are indispensable lin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and new therapies. While as vulnerable groups in clinical trials in legal relationship, the subjects’ interests are vulnerable to abuse. The protection of the subjects’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ioethics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has the necessity of theoretic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that is not perfect, the system is not scientific and other realistic difficulties,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subjects’ rights and interests also has the necessity of practical level. Combining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utside of the subject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in the clinical trial of the patients, our country can be engaged in the promotion of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post judicial relief or other aspects.
收稿日期:2015-06-01
基金項目:2013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西部農村階層分化與民主政治建設研究”(2013YBZZ013)
作者簡介:劉純明(1966—),男,四川隆昌人,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哲學;柴鵬(1991—),男,山東濟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政治哲學;劉遠冬(1992—),男,重慶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政治社會學。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5.12.018
On Protection of Subject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linical Trial:
the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Legal Route
ZHANG Li, LIU Xiao-yan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Key words: clinical trial;protection of right and interest;bioethic;universal human right;no-fault liability
自1948年英國著名生物學家Bradford Hill在實驗設計中利用臨床試驗方法使用鏈霉素成功治療肺結核之后,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就在醫學研究中被廣泛應用,并成為檢驗新藥物、新療法有效性的黃金標準。如果臨床試驗成功,將會更好地預防、診斷和治療人類疾病,發展醫藥事業和醫學實踐,改善和增加人類健康福祉。正如《赫爾辛基宣言》所說:“醫學的進步以研究為基礎,而這些研究最終依賴于人體受試者進行人體試驗。”然而,由于臨床試驗是在對所涉物質的療效和毒性尚無確切知曉和把握的情況下,首次將其應用于人體的試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人體,特別是在病人體內沒有得到證實之前,即便是一種有希望的藥,也決不能說就是一種藥[1]。對于臨床試驗受試者來說,它意味著高風險。一旦這種風險現實化,將會損害受試者的健康權甚至生命權。因此,這些作為弱勢人群的受試者不僅應受到人文關懷和尊敬,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在法律層面為受試者提供切實可行的維權和救濟的方法和手段。
一、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理論基礎
臨床試驗是一把雙刃劍,在新藥物、新療法問世帶給人們驚喜和歡呼的同時,由于背后巨大經濟利益的推動,臨床試驗致使受試者生命健康權受到侵犯的現象屢屢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于相關機構和人員未認識到受試者權益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理論層面的必要性論證是對受試者權益保護現狀進行剖析,并對其進行制度設計的前提和基礎,在證明序列上具有優先性。
(一)倫理基礎——生命倫理學
單靠科技的進步并不能使人類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我們還必須研究適于我們時代的倫理道德和道德價值本身[2]。二戰中的《紐倫堡法典》給人們敲響警鐘,醫學只有在倫理學的指導下,才能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只有遵循倫理道德規范,才能真正造福人類。臨床試驗作為試驗對象為人的科學研究,也必須符合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科學理論——生命倫理學[3]。
自1979年美國倫理學家Tom L Beauchamp和James F Childers提出生命倫理學的四大原則——尊重、不傷害、行善、正義,其作為普遍的原則被人們廣泛接受。相應的,在臨床試驗的過程中,這四大原則也應貫徹試驗的全過程。
詳言之,第一,尊重受試者的自主確定權,并保護不具有自主決定能力的人。康德認為,尊重一個人的自主性是基于所有人都具有絕對的價值和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4]。在臨床試驗之前,研究者應當將試驗預期的目的和可能的后果如實告知受試者,征求受試者的意見,并尊重受試者的決定。第二,不對受試者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在臨床試驗中,為了達到試驗目的,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傷害受試者的可能。不傷害原則的意義不在于消除所有傷害,而在于強調試驗者應當謹慎行醫,對受試者高度負責,以達到適當的照顧標準,避免受試者遭遇不應有的損害。第三,試驗所要達到的目標和效果對于受試者來說確實有益。這要求受試者確有疾病,并且該臨床試驗所欲達到的目標與解除受試者的疾病痛苦直接相關,同時,受試者受益不會給別人帶來大的損害[5]。第四,受試者應當受到公正的對待。臨床試驗中的“公正”即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同種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也就是說,在受試者的病情、身體狀況等方面一致時,應采取同樣的治療方法。反之,則采取的治療方法也應有所差別。
臨床試驗的科學性與倫理性具有一致性[6]。醫學倫理的評價和價值判斷,使科學家和醫療工作者在研究活動和醫療行為中始終保證醫學判斷的正確性。生命倫理學意味著對受試者生命的尊重,是受試者權益保護最根本的理論基礎。
(二)法理基礎——普遍人權理論
從法理學的視域來看,受試者作為法學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對其權益進行保護是普遍人權理論的應有之義。*法學意義上的弱勢群體,通常是指由于社會條件和個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礙而無法實現其基本權利,需要國家幫助和社會支持以實現其基本權利的群體。可以說,弱勢群體最為重要的特征是其基本權利得不到實現。
1.受試者的弱勢群體屬性
首先,臨床試驗具有風險性。美國國家生物咨詢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于大多數醫學研究的風險與結果的不確定性,所有受試者都屬于弱勢群體[7]。其次,受試者的法律權利虛化。臨床試驗所涉及的受試者知情權、生命健康權、自主決定權、隱私權、損害補償權等大部分權利都屬憲法中的基本權利。從權利實現角度看,只有當這些“應然權利”轉化為“實然權利”才能得到有效保護。然而,我國國內的相關法律文件中,僅《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定》概括的規定,“在藥物臨床試驗的過程中,必須對受試者的個人權益給予充分保障。”*《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定》第8條。但相關具體權利在受試者保護規范中并未具體化、法定化。再次,受試者權利保障、救濟機制弱化。權利的實現依賴于各項制度保障。在權利保障上,我國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等行政監管部門對臨床試驗的監管尚未規范化、制度化,倫理委員會審查制度作為受試者保護的重要制度,在我國也并不完善;在權利救濟上,我國受試者權利救濟制度尚處空白,受試者遭受損害后只能借助《侵權責任法》中的相似制度尋求法律救濟。
由上可知,不論受試者是否基于自然人的某些特殊屬性而被社會大眾視為弱者,也不論其社會、經濟、政治地位如何,只要其屬于受試者,就成為臨床試驗法律關系中的“弱勢群體”。
2.基于普遍人權理論的受試者權益保護
普遍人權,即人權的普遍性,指人權是一種應當被普遍尊重和遵行的價值。這種價值的存在和實現對于任何國家、種族和民族的任何人都是沒有區別的,因而它具有普遍的屬性[8]。 “人的權利的最終基礎是人本身。”[9]人權普遍性的源頭在于人的尊嚴和人自身的價值。特別是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今天,人權不再是單純的人的基本權利的問題,而是貫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問題。
(1)對受試者權益進行保護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內在要求
現代法治理念中的普遍人權,不僅意味著對人的尊嚴的普遍認同,還意味著獲得普遍認同的人權必須惠及所有人[10]。受試者作為弱勢群體,理應受到普遍人權理論的關懷。不僅如此,對受試者進行特殊的傾斜性保護,使弱者能夠切實享受到作為人所應享受到的一切權利,緩和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內在要求[11]。
(2)對受試者權益進行保護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本質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社會對形式正義的典型表述。這意味著,在個人起點不同的情況下,強者越強而弱者越弱,最終將導致兩極分化。然而,一個富有正義的社會應當保證社會各個階層的生存權利,并讓每個階層都獲得幸福。它在給強勢階層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和較多收入的同時,也應保證弱勢階層的基本生存,并分享到社會發展的成果[12]。羅爾斯的實質正義理論認為,“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差別原則[13]。差別原則導出了補償原則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對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受試者給予更多的關懷和保護,使每個人各得其所,各獲其利,才能調整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實現實質正義。
(3)對受試者權益進行保護是權利本位的題中之義
“法律權利”能夠將人權的應然性理想轉化為實然性存在,當“權益”轉化為“權利”之后,受試者作為權利主體,就能夠在受到損害之后,采取訴訟等公力救濟方式維護自身利益。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社會由階級斗爭轉化為權利本位。在權利本位價值模式下,權利處于主導地位,義務服從于權利,義務的設定是為了權利的實現[14]。其本質是承認并崇尚人自身的價值以及人的主體性。在權利本位的引導下,通過法律賦予臨床試驗受試者各種權利,并將權利置于主導地位,有利于提高受試者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現實困境
(一)相關法律體系不健全
國際上對臨床試驗的規范已經相對完善,*臨床試驗的國際規范,目前發揮作用的主要包括,二戰時期制定的《紐倫堡法典》、由醫學研究國際組織理事會與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各項國際倫理指南》(2002年修訂版)、由世界醫學會制定并頒布實施的《赫爾辛基宣言》(2008年修訂版)等。但我國的臨床試驗剛剛起步,在管理規范上并不健全,特別是涉及受試者權益保護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CDE數據顯示,每年新批準的藥物臨床試驗約400個,正在進行的藥物臨床試驗有1 000多個,涉及的受試者約50萬人[15]。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尚未有法律專門就受試者權益保護做出系統規定。*目前我國大陸地區對臨床試驗做出明確規定的專門性立法僅有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3年頒布的《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但是,該法在效力層級上僅為“部門規章”,而非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我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均未就臨床試驗問題做出專門規定,僅一些規定可套用進臨床試驗中。*如《刑法》中的非法行醫罪、醫療事故罪;《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對醫療事故的界定、事故等級、處理程序等;《執業醫師法》第26條和第37條從試驗實施者的角度進行了規定,醫務人員進行臨床試驗應當經醫院批準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屬同意。《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從臨床試驗的倫理審查方面進行了規制,但2008年《赫爾辛基宣言》修改后,對于其中所提及的最新規定卻未進行更新,反映出我國在倫理審查方面的立法滯后。《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簡稱GCP)是目前我國最為系統的臨床試驗全過程的標準規定。*參見《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總則第2條。它是以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協調會議制定的ICH-GCP指導原則為藍本,結合我國國情制定的[16]。GCP的相關規定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傳統倫理,為規范我國藥物臨床試驗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但同時也應看到其存在的問題。譬如,GCP僅適用于藥品的醫學臨床試驗,而不能規范諸如新的治療方法、基因技術等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的相關制度不健全,未明確具體的審查程序和審查結果救濟機制。
總體來說,我國在受試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立法并不健全,無法真正為受試者的權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途徑。
(二)相關制度建設不科學
倫理委員會是我國目前保護受試者權益的唯一專門機構,對授試者的權益保護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我國卻沒有明確的倫理審查程序規范,對其職權的規定過于籠統,在具體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倫理委員會的運作機制上,對于委員會成員也缺乏有效培訓機制,這導致作為“裁判員”的委員會成員無法知道確切規則從而無法監督研究者是否違規[17]。從倫理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說,倫理委員會委員一般是醫院中層干部,同時身兼數職,難以保證審查過程的獨立性。
(三)受試者救濟措施不完善
我國目前對于受試者沒有設立專門基金和進行強制保險。除了受試者免費試藥和一般經濟補償以外,基本不提供損害補償,甚至因此被稱為“廉價小白鼠”[18]。當受試者出現不良反應,一般由研究機構進行救濟,由申辦者負責相關費用。而一旦出現嚴重醫療事故后,研究機構和申辦者往往由于缺乏足夠的治療能力和補償能力而使受試者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和補償。
三、域外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有益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視野下從立法實踐、制度模式和救濟措施3個方面進行考察,并選取對該部分監管相對規范、對受試者保護最為有效的國家為代表,提煉其理論和實踐的有益經驗,是迅速完善我國受試者權益保護體系、提升受試者權益保護程度的捷徑。
(一)域外關于受試者保護的立法實踐
美國在開展臨床試驗方面領先于其他國家,在域外立法實踐方面也屬美國最為全面。因此,該部分主要介紹美國經驗,窺一斑而見全豹。
美國最早的關于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法律是1962年制定的《1938年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的科弗爾-哈里斯修正案》,該修正案第一次明確規定了在新藥上市前,藥品制造商必須向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證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并首次提出進行藥品臨床試驗必須獲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19]。1966年,美國衛生部國立研究所發表聲明,凡受衛生部資助的醫學研究項目,若存在造成受試者傷害的風險,則須事先經專家委員會審查,權衡醫學研究項目的利弊并獲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后方可進行,以充分保證受試者的權利能夠得以保護[20]。1974年,美國聯邦教育與福利部制定了《保護受試者法規》,其中確立了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負責權衡醫學研究項目的利弊,保護受試者權益。這是美國規定受試者權益保護的第一個專門性文件。1991年,聯邦衛生與福利部發布《保護醫學研究受試者聯邦法規》(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45CFR46),并于2005年修訂,成為美國用于保護受試者權益最重要的專門性文件。由此可見,美國保護受試者的法律詳細、具體、全面,并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值得我國學習。
(二)域外關于受試者保護的制度模式
1.行政監管模式
美國的臨床試驗受FDA和美國衛生部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OHRP)這兩個機構監督。FDA的職能主要是制定相關指南和法規,監督和審評臨床試驗的過程和結果,監管各地的倫理審查委員會。*FDA對機構審查委員會的監管權力很大,可以中止或終止其之前批準的臨床試驗研究繼續進行,甚至取消機構審查委員會的資格。OHRP負責領導機構審查委員會,并為其工作制定標準和計劃[21]。
在法國,行政監管機構根據臨床試驗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區別:關于藥品、化妝品和醫療器械的臨床試驗由法國衛生與衛生產品安全局(French Agency for Security of Health and Health Products,FASHHP)進行監管,除此以外的臨床試驗由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監管。分不同機構監管的優勢是,監管部門專業化水平更高,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更強,監管更加有效。
2.倫理委員會審查制度
倫理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最早發源于美國。1974年和1981年美國分別頒布了美國聯邦法律45CFR46和21CFR56,歷經多次修改后成為IRB監管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也奠定了監管機制的法治基礎[22]。其主要職責是評估臨床試驗的風險與臨床試驗帶給受試者或社會的利益比值是否合理,審查具體臨床試驗的設計是否尊重受試者個人隱私,試驗中知情同意程序的正當性等。美國IRB不是一個統一的倫理審查機構,而是存在于各研究機構內部。因此,每一個IRB的設置條件和運行規則有所不同。
在荷蘭,進行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并保護受試者權利的機構是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Medical Ethics Review Committee,MERC)和人體試驗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CCMO)。同美國等由機構內部設立審查委員會不同的是,荷蘭采取行政審查模式。即倫理審查機構不附屬于研究機構,而是獨立的行政性機構。即使METC附屬于某一機構,其中至少有一名委員會成員獨立于該機構[23]。荷蘭《人體試驗法》賦予CCMO和METC公法地位,使其成為行政主體,能夠有效保持倫理審查的獨立性、中立性和客觀性。
(三)域外關于受試者保護的救濟措施
臨床試驗中的受試者救濟措施主要分為損害責任認定和損害補償制度。
在損害責任認定方面,美國采取過錯責任原則,即考察研究人員在臨床試驗中的行為是否違背正常的治療標準。在美國,對于各種疾病的治療都有相應的治療標準,在給患者進行治療時,醫生必須達到該種疾病的治療標準。臨床試驗也應如此,只要臨床試驗的研究者沒有達到該種疾病的治療標準,就應承擔相應責任;法國的歸責原則根據研究類別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對受試者有一定治療利益的臨床試驗中,采取過錯推定責任;在對受試者沒有任何治療利益的臨床試驗中,采取無過錯責任原則[24]。
在損害補償方面,美國采用政府強制補償和研究機構自愿補償相結合的制度[25]。政府強制補償主要針對疾病患者,只要其在臨床試驗中受到損害,就可享受政府為其提供的醫療保險賠付。同時,受試者還可接受研究機構的自愿補償方式,其通常是在試驗前由試驗申辦者與研究機構協商確定補償方案[26]。法國則由申辦者和其他參與者根據強制保險的責任范圍承擔經濟上的責任。
四、我國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法律進路
理論基礎從理論層面證成了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現實困境從實際出發指出了我國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缺憾和不足,域外實踐從經驗層面指引了我國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方向和目標。由此,順理成章地找到我國臨床試驗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法律進路。詳言之,法律進路應包括受試者權利保護的立法模式和相關制度構建這一綜合性、多層次的體系。
(一)臨床試驗受試者權利保護的立法進路
1.制定《受試者權益保護法》,打造受試者權益保護的“有力法寶”
對受試者權益保護進行專門立法,無疑是對受試者進行保護的最佳選擇。
在具體立法中,首先,應當明確受試者享有的各項權利,并對如何進行保護做出詳細規定。其次,規定申辦者應當為受試者及其他研究參與者購買臨床試驗強制責任保險,以保證其在研究過程中若造成損害,能夠獲得有效的經濟補償。再次,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例如,借鑒美國對婦女受試者、兒童受試者等弱勢群體進行傾斜保護,借鑒法國將臨床試驗分為對受試者有直接利益的臨床試驗和無直接利益的臨床試驗,從而對不同類型進行分別保護。
總之,受試者權益保護法不僅是受試者保護的“有力法寶”,更彰顯我國法治建設中對人權的重視和保障,是對我國“人權入憲”的有力回應。
2.改進臨床試驗管理規范,撐起受試者權益保護的“防護傘”
臨床試驗管理規范是從臨床試驗本身進行規制,能夠有效排除不符合條件的臨床試驗,間接達到對受試者的保障。可以說,臨床試驗管理規范是受試者權益保護的一道“防護傘”。
第一,應當制定臨床試驗管理規范的一般法。我國目前的管理規范均是從單一角度對臨床試驗進行規制,由此導致對于我國一部分臨床試驗,尚無明確完整的法律進行規制,受試者權益無法在事前得到有效保護;第二,應當制定具體臨床試驗管理規范的特別法。由于每一類臨床試驗的特點不同,有必要對不同類別的臨床試驗進行分別規定,包括藥物臨床試驗、治療方法臨床試驗等。
3.完善相關配套立法,構建受試者權益保護的“保護網”
對于以上兩個層面的法律法規,我國還需要進行相關配套立法的完善。例如,對于受試者隱私,需要建立完善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于臨床試驗強制責任保險,應當由《保險法》加以規制。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有在相關配套立法上加以完善,才能使受試者權益處于“保護網”中,得到立法層面的全方位有力保護。
(二)臨床試驗受試者權利保護的制度進路
立法上的規定須落實到具體制度中,以制度為依托、用制度作保障,才能對法律規定的內容進行有效實施。
1.行政監管制度構建
(1)完善現行行政監管制度
目前,我國臨床試驗行政監管部門為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就其已有的監管成果和監管經驗來看,這一行政監管部門不宜再做大的變動,當務之急是完善其監管職能,強化其對臨床試驗的申辦者、研究機構等相關機構和人員的規范化管理。在完善的手段上,可將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對象分為機構和人員,對其進行不同方式的監管。
對相關機構的監管主要是準入監督和工作監督。具體包括對臨床試驗研究機構進行資格認定以及對臨床試驗過程的監督,對倫理委員會進行審查工作的監督。在監督方法上,特別強調對臨床試驗的事前監督,即建立臨床試驗事前審批制度。對具體臨床試驗進行事前審批能夠有效排除方案不合理、不安全、風險高的臨床試驗。
對相關人員的監管主要是工作監督。具體包括明確界定參與臨床試驗人員的義務和責任,并為不同的義務設定對應的監管部門,加強對相關人員的監管。同時,應當加大對臨床試驗的參與者及倫理委員會成員的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其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素質。
(2)增設臨床試驗受試者保護辦公室
由于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較多,為了保障其對受試者保護的工作落到實處,建議在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內部增設“臨床試驗受試者保護辦公室”專職負責相關工作。臨床試驗受試者保護辦公室的職能不僅包括上述行政監管工作,還包括進行相關立法,例如對現有臨床試驗規范進行完善、補充制定新的臨床試驗規范等。
2.倫理委員會審查制度構建
(1)設立獨立的倫理審查行政機構
對于倫理委員會審查模式,我國目前采納的是美國式的機構內審查模式。但由于我國社會狀況不同于美國,社會人情化程度較高,審查人員很難不受干擾,這導致我國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獨立性、中立性和客觀性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在機構設置方面,應當仿照荷蘭,建立獨立于具體研究機構的倫理審查行政機構。如此方能有效地對具體研究機構內的臨床試驗項目進行審查和監管,更好地保障倫理審查落到實處。
(2)提高倫理審查指導規范的法律位階
我國現行的倫理審查指導規范——《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是倫理審查委員會設立和進行審查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據。但在法律位階上,《辦法》只是部門規章。從目前我國倫理委員會的監管現狀來看,這一狀況亟需改善。建議提高倫理審查指導規范的法律位階,增強其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進一步對其進行完善,為倫理委員會的監管提供有力法律依據。
(3)完善倫理審查的委員回避機制
相關委員回避機制的目的是通過限制倫理委員會委員在具體試驗中的審查權限,消除其利用職權謀私徇情的可能性。我國《辦法》第19條建立了相關委員回避機制,但并不完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第19條:“倫理委員會不得受理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科研項目提出的倫理審查申請。倫理委員會委員與申請項目有利益沖突的,應當主動回避。無法回避的,應當向申請人公開這種利益。”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確立“利益沖突”的認定標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生物醫學研究審查倫理委員會操作指南》規定,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利益沖突判斷標準應同臨床試驗研究者的利益沖突標準相同,具體應當包括可能影響其對臨床試驗所享有的財產利益、重大報酬、經費的事項[26];第二,規定委員在應回避而未回避時,應當采取的措施,如有權機關可強制要求其回避等;第三,規定“無法回避”的原因,對于無法回避的,該委員向申請人公開這種利益后,可不予回避,但什么情形下構成“無法回避”,法條未予規定,由此可能出現應回避而不回避的狀況。
(4)加強倫理委員會的后續監管
我國《辦法》第9條、第22條原則性地規定了倫理委員會的后續監管職責,但對于后續監管的具體內容和程序缺乏規范。
在具體內容的確定上,筆者認為,應當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生物醫學研究審查倫理委員會操作指南》,當出現下列情況時應當進行后續監管:(1)對試驗方案的任何修改,可能影響受試者權利、安全、福利,或影響研究的實施;(2)與研究實施和研究產品有關的、嚴重的和意外的不良事件,以及研究者、申辦者和管理機構所采取的措施;(3)可能影響研究受益/風險比的任何事件或新信息。*參見《生物醫學研究審查倫理委員會操作指南》第九章。
在實施程序上,重點是明確倫理委員會進行后續監管的時間和頻率要求、研究者對于試驗進展的報告程序,以保證臨床試驗機構嚴格按照最初被批準的試驗方案執行并及時發現試驗過程中損害受試者權益的行為。
(三)臨床試驗受試者權利保護的救濟進路
1.歸責原則方面
臨床試驗損害賠償責任歸責原則在目前學術界引起較大爭論。大致來講,認為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學者的主要依據是受試者弱勢理論、醫療體制的保護不足、臨床試驗屬于擴大化的“高度危險作業”等[27]。
在臨床試驗中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優點顯著,受試者在進行舉證時,無須考慮試驗方的過錯,從而極大減輕了受試者的舉證責任。但是,在進行歸責原則的設計時,不僅僅要考慮這些,更要從實際出發。若在臨床試驗中引入無過錯責任,又要求保險公司對臨床試驗承擔強制保險,保險公司很可能由于臨床試驗的風險性過大而不愿承保。同時,無過錯責任也對我國現行醫療責任的過錯責任原則帶來沖擊。換句話說,無過錯責任原則會加劇風險分擔的不平衡性,從而導致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侵權責任無法運行。
筆者認為,臨床試驗損害賠償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在具體操作中,由于臨床試驗涉及到較多的生物醫學知識,受試者往往一竅不通,導致受試者與研究者在掌握證據的能力上差距懸殊。因此,應當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中的過錯推定原則,使舉證責任倒置,由研究者證明其無過錯,否則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2.損害補償方面
在賠償范圍方面,臨床試驗與我國一般的醫療人身損害的賠償范圍并無二致,因此,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16條。關鍵問題是,受試者遭受的損害應當由誰賠償。我國目前尚無政府強制補償制度,實踐中主要由研究機構進行補償。此外,為了使受試者獲得有效的賠償,筆者認為還應當建立臨床試驗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在保險制度設計時,應兼顧受試者、投保人(申辦者、研究機構)、保險人之間的利益需求,尋求利益平衡。只有將強制保險制度與損害賠償制度相結合,才能充分保護受試者權利,使臨床試驗達到增加人類福祉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砂原茂一.臨床藥理學:尋找新藥和藥物治療的基礎[M].王仁忠,孫友樂,等,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2:7.
[2]李淑蘭.試論科技發展的倫理意義[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3(10):102-105.
[3]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Declaration of Helsinki[R].59th WMA General Assembly of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Seoul.2008.
[4]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127.
[5]徐宗良,劉學禮.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實踐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3.
[6]丘祥興,沈銘賢,胡慶澧.干細胞研究倫理[J].生命科學,2012(11):1308-1317.
[7]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Participants[R].U.S.,NBAC.2008.
[8]杰克·唐納利.普遍人權的理論與實踐[M].王浦劬,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9]夏勇.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公民權利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18.
[10]張文顯.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中國法學,2014(4):5-27.
[11]付子堂.法治體系與人權保障[J].法學研究,2013(2):23-26.
[12]占志剛.試論弱勢群體及其法律保護[J].行政與法,2003(3):54-55.
[1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4.
[14]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366.
[15]劉稚亞,李晗.“走鋼絲”的人體試藥員——醫療進步的犧牲品[EB/OL].[2015-03-15].http://www.jingji.com.cn/html/news/djxw/20434.html .
[16]李海燕,吉萍.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在臨床研究中的價值及我國研究者的依從情況[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0(6):637-639.
[17]夏鍇,盧建華.隨機臨床試驗中倫理問題的探討[J].醫學與哲學,2012(1):64-71.
[18]侯艷芳.非法人體試驗與我國刑法的應對[J].法學評論,2011(2):122-129.
[19]約翰·亞伯拉罕.漸進式變遷——美英兩國藥品政府規制的百年演進[J].北大法律評論,2001(2):588-622.
[20]曹國英,鄒和建,伍蓉.生命倫理學委員會[J].生命科學,2012(11):1237-1242.
[21]趙幗英,江濱,史錄文.我國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運作模式及監管機制探討[J].中國藥事,2007(1):25-28.
[22]胡林英.對倫理審查委員會監管機構的分析與思考[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6(2):17-19.
[23]滿洪杰.從“黃金大米”事件看未成年人人體試驗的法律規制[J].法學,2012(11):54-63.
[24]滿洪杰.論醫學人體試驗中的侵權責任——以比較法為視角[J].法學論壇,2012(5):113-120.
[25]吳軍,湯權.新藥人體試驗致人損害民事賠償訴訟中的法律問題[J].人民司法,2007(23):70-72.
[26]彭真明,劉學民.論人體生物醫學研究活動中的侵權責任[J].法商研究,2009(2):18-26.
[27]倪正茂,陸慶勝.生命法學引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307.
(責任編輯何培育)

引用格式:劉純明,柴鵬,劉遠冬.西部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路徑選擇[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12):105-111.
Citation format:LIU Chun-ming,CHAI Peng,LIU Yuan-dong.Choice About Development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Basic Democracy in West Villag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12):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