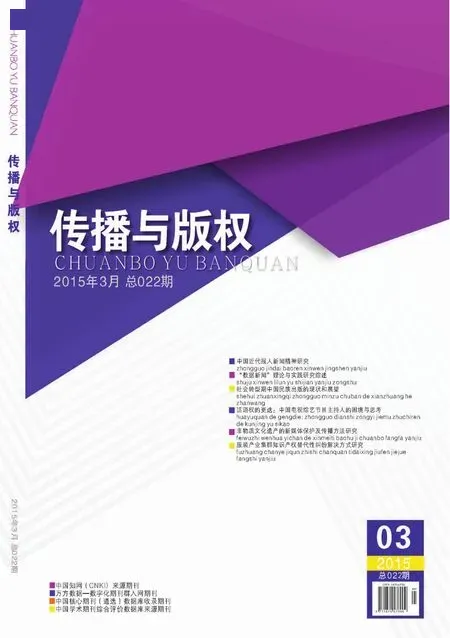技術、社會與媒介:論公民記者產生的現實動力
劉辛未
技術、社會與媒介:論公民記者產生的現實動力
劉辛未
[摘要]公民記者的誕生與發展建立在公民社會逐步形成的基礎之上,更與傳統新聞傳播系統的現存弊病、急需新生力量密不可分——公民記者的產生與發展是多重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試從技術因素、社會因素與媒介因素三個方面論證公民記者產生的現實動力。
[關鍵詞]自媒體;公民記者;公民新聞;現實動力
[作者]劉辛未,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
一、技術因素:自媒體時代的到來
(一)自媒體的開放性——拓寬公民記者的生存空間
自媒體本身是新媒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特征,具有新媒體的即時性、交互性特質。自媒體本質上是普通民眾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即時交互平臺,一種具有開放性、平等性的信息提供與分享平臺。自媒體的開放性首先是由于新媒體技術平臺的交融性,新媒體使得文字、聲音、圖片、視頻等多媒體內容共存于一體,并且新媒體平臺的操作日益圖形化和簡易化,降低了準入門檻和用戶的使用難度,同時對內容的要求不甚嚴格,不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的傳播內容。開放與包容,部分填充了不同文化水平公民之間使用新媒介的“能力溝”,使得網絡這一公共領域和民主論壇不斷擴大。伴隨著公共知識分子參與社會事務、跟進新聞事件、表達自我愿望的日益強烈,自媒體的開放性為這些聲音提供了傳達媒介,也可以說是自媒體的開放性成就了公民新聞以及公民記者的出現與生存。
(二)自媒體的“平權互播”——技術賦權于普通公民
自媒體的出現使得草根大眾這一“新意見階層”逐漸崛起,新聞傳播進入了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全民書寫”時代。“平權”“互播”具體指的是自媒體的平等性、交互性特質。自媒體的出現有效地改變了傳受雙方地位的不平等,顛覆了“輿論一律”的傳播格局,是一種平權傳播。同時,自媒體使得傳者與受者可以同時存在于一個傳播節點,公民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是內容的生產者與傳遞者,不僅可以接受信息,還可以對其進行反饋,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群體在傳播中的地位。傳統媒介不再壟斷信息源、獨享話語權,媒介權力的重心逐漸向自媒體偏移,新聞不再是幾家媒體的發言,而成為全社會的和鳴。尼葛洛龐帝把權力的分散視為數字化生存四大特質之首,認為傳統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觀念將隨著網絡的發展成為明日黃花。①李永剛:《我們的防火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7頁。自媒體時代帶動了新聞業的新一輪革命浪潮。自媒體“平權互播”的特質與公民新聞“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可以發聲”的主旨不謀而合,自媒體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公民新聞的主要傳播場所,亦即成為公民記者得以生存和繁榮的土壤。
(三)自媒體的“同向傳播”——“同向價值”吸附公民記者
自媒體的開放性、平等性、交互性等特質都在無形之中增加著自媒體的使用頻次,而越來越多的普通公民選擇自媒體而非傳統媒體來獲取與分享信息的原因除了上述特點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自媒體的媒介價值觀與受眾的價值觀是同向的。自媒體代表的是普通公民的聲音,它區別于從屬團體、組織、利益集團抑或是黨政機關的“他媒體”,即便是目前十分火熱的政府微博、企業微博,其本身也帶有一定的獨立屬性和個人色彩。而大部分的自媒體是獨立的和自由的,其信息的生產者、使用者具有相近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的同向性決定了以自媒體為平臺的公民新聞具有更加強烈的貼近性、趣味性、動態性,更符合目標受眾的偏好。②周曉虹:《自媒體時代:從傳播到互播的轉變》,《新聞界》,2011年第4期。
自媒體的草根性與其價值傳播的同向性,吸引了大量的公民記者和普通受眾,使其在傳受兩方面都積聚了大量的主體資源,為公民新聞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主客體的雙重保障。
二、社會因素:公民意識的覺醒與行動力的增強
(一)公民記者是在“公民意識”覺醒的前提下誕生的公民積極主動地參與公民新聞的生產與傳播,其中
很大一個原因來自公民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公民的民主平等意識。公民民主意識主要體現為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平等意識、法治意識這五個方面。
公民的主體意識強調每個公民都是社會民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是社會運行的主體。在我國,公民自身的主體意識仍然處于萌芽狀態,公民自身對自我的“主體地位”感知度差,導致參與公共事務時缺乏主觀能動性。隨著近兩年技術門檻的降低和民主進程的推進,公民主體意識在這種氛圍下被強化,參與社會事務的主動性提高,公民記者大批涌現。
公民記者在參與新聞傳播活動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最主要權利是言論自由權,公民新聞打破了傳統媒體壟斷話語權的局面,使得普通公民有了更加廣闊的話語空間,而越來越多的公民積極參與其中,就是分割話語權的一種表現,在此過程中,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得以實現。公民記者具有較強的平等意識,“人人都是記者”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平等意識,促使公民記者不斷爭取話語權、不斷參與民主進程和公共事務的探討。公民的法治意識則是指公民應具有的知法、守法、抵抗違法行為的意識。日益成熟和活躍的法治意識為“公民記者”尋求關注目標以及規范自己行為起了關鍵的指導和約束作用。①李曉娟:《新媒體時代“公民記者”現象探析》,中國政法大學,2010年,第21頁。
公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帶動了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有獲取民主權利的動機,同時又受到自身法治意識的約束,公民記者群體不斷壯大,在道德與法律雙雙達標的理想環境下,公民記者的質量也會得以提升。
(二)公民社會的萌芽與公民的行動力增強
公民意識的覺醒促進了公民社會的形成,“公民社會使公民重新獲得一部分輔助性和自覺性,提供了民眾表達言論、參與公共事務的制度安排以及實現自主性的舞臺”。②蔣達勇:《我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及其對大學德育的意義》,《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公民逐漸成長為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一方面爭取到了更開放的話語平臺,另一方面也逐漸成為社會行動的主體,災難救援、民主抗辯、公益實踐,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自2003年孫志剛事件起,到后來的“黑磚窯”事件、“華南虎照”事件、“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再到鄧玉嬌事件,再到近來的2013南方周末事件、長春304盜車殺童案等,歷次重大社會事件中,公民記者的參與都為案件朝客觀、公正方向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輿論支撐。民眾公民意識的覺醒,樸素正義感的表達對其中大部分案件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一樁樁公共事件證明,公民通過有序的參與,形成合力,可以引導輿論、制約濫權、伸張正義。而在社會事件中不斷深入人心的一系列法制觀念、人權觀念、民主意識、責任意識,也預示著公民社會正在逐漸孕育和成長。
三、媒介因素:傳統媒體的失語及專業記者的缺位
傳統媒體失語現象對傳媒來說是一件很困惑又很無奈的事,對受眾來說則是一件很失望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總的來說媒體失語的原因有二:一是政策體制的管控;二是經濟利益的壓力。
政策體制方面的壓力來自于我國長期以來的媒介審查制度。凡是涉及重大、敏感話題的新聞事件,都需要得到上級的審批才能夠進行報道。這樣的后果一來是耽誤了新聞的及時播發,降低了新聞的時效性;二來是許多重大事件不允許報道,媒體被動失語。這是由目前我國的媒介生存法則決定的,如要改變現狀則需要從本質上廣開言路,解放思想,改革新聞審查制度。經濟利益方面的壓力來自于媒體的經營管理模式。作為經營性事業單位,媒體只愿意為那些能給自己帶來廣告收益的受眾提供信息,滿足他們的信息需求。③王正明:《媒體失語與失信》,http://www.jmtv.com.cn/html/btwy/lw/20090511/3230.html。在此金錢至上的理念之下,媒體逐漸降低了對內容的要求,一味地迎合廣告主或利益體,因此,那些和媒體本身存在經濟利益關系的團體,則成為揭露與批判的“禁區”。而正是傳統媒體的缺席和失語,給公民新聞的生存創造了一個缺口。
此外,專業記者難免有其認識盲點或誤區,這就容易造成記者在報道新聞時出現語言上的紕漏、觀點上的偏頗,而當突發事件特別是災難性事件發生時,專業媒體記者很難及時趕到現場進行報道。由此,特定場合下公民記者的存在可以填補專業記者所造成的缺位,彌補可能造成的公眾對于新聞事實認知的漏洞和偏差。
總之,公民記者的產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現代傳播科技迅速普及的必然結果,是公民社會萌芽和公眾影響力、行動力提升的結果,也是政策法律、理論研究共同支持的結果。公民記者的出現順應了公民對于知情權、參與權、言論自由權等權利的訴求。公民不再是沉默的羔羊,而是能夠質疑權威、挑戰權威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