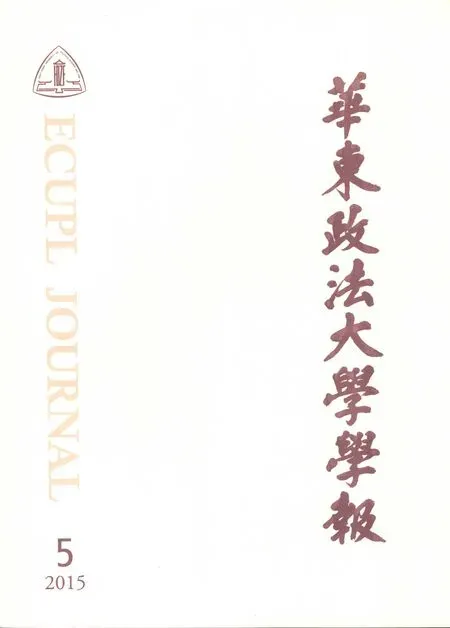法制化途中的人工胚胎法律地位——日本法狀況及其學說簡評
周江洪
“無錫冷凍胚胎案”所引發的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問題,引起了學界和實務界的關注。人工胚胎問題涉及生命倫理,關涉各國的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各國因此所采取的法律政策會面臨諸多不同。美國JMP(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雜志在其2004年8月刊中就曾對歐美各國ES細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法律規制展開了討論,〔1〕該期雜志刊載了 Christine Hauskeller,Howard J.Curzer,Alexandre Mauron and Bernard Baerstschi,Giobanni Maio, Jan P. Beckmann,Tanja Krones and Gerd Richter 等人的六篇文章,就人類胚胎的各國法律政策進行了評析。其核心問題為“人工胚胎”的道德定位,并對各國的法律政策狀況作出了評析。
關于胚胎的法律地位,“無錫冷凍胚胎案”兩審法院都作出了判斷。其中,一審判決認為,“胚胎作為其生命延續的標志”,“施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過程中產生的受精胚胎為具有發展為生命的潛能,含有未來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樣任意轉讓或繼承,故其不能成為繼承的標的”;而二審判決認為,“胚胎是介于人與物之間的過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潛質,比非生命體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應受到特殊尊重與保護”。其實,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工胚胎的法律定位問題在日本也引起了醫學界、法學界和政策制定機關的極大關注。本文僅就日本的相關情況作簡單介紹,以供今后我國立法時批判或參考。
一、人工胚胎法律地位的“軟法”化傾向
(一)關于人工胚胎的立法探索
總體上來說,日本在關于生殖輔助醫療方面的法制化上,雖然也作出了諸多努力,但仍然沒有形成關于生殖輔助醫療方面的法律,這遠遠落后于諸多發達國家。〔2〕南貴子:《生殖補助醫療の法制度化における課題》,《愛媛県立醫療技術大學紀要》第8巻第1號(2011年12月)第16頁。1998年10月21日,原厚生省的厚生科學審議會先端醫療技術評價分會設立了“生殖輔助醫療技術專門委員會”,并于2000年12月28日提出了《通過精子、卵子、胚胎的提供等進行生殖輔助醫療的理想狀態的報告書》。日本厚生省和法務省根據該報告書設立了各自的審議會,力爭在3年之內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2003年4月28日,厚生省提出了《生殖輔助醫療分會報告書》;〔3〕該報告書雖然并未能最終成為法律,但其涉及了與“無錫冷凍胚胎案”中相似的問題,即人工胚胎的冷凍保存。依該報告書,精子、卵子的保存期間,以2年為限;胚胎的保存期間以10年為限;但是,精子、卵子及胚胎提供者的死亡得到確認時,對該精子、卵子及胚胎實施廢棄。報告書全文參見http://www.mhlw.go.jp/shingi/2003/04/s0428-5a.html#1-1,2015年3月5日訪問。法務省則于2003年7月15日提出了《關于通過精子、卵子、胚胎的提供等生殖輔助醫療出生的子女的親子關系的民法特例法綱要試擬稿》。但是,兩者都未能最終向日本國會提出法案。此后,日本學術會議于2006年12月21日設置了生殖輔助醫療理想狀態研討委員會,并發表了對外報告“《以代孕為中心的生殖輔助醫療的課題》”,該報告指出應當對代孕進行法律上的規制,原則禁止代孕,〔4〕該報告指出了代孕的五點問題:(1)代孕的醫學影響尚不明確,危及胎兒和母體的可能性不小;(2)接受代孕的女性的“自我決定”,并不限于充分了解了身心負擔及其風險的基礎上、且在未受外在壓力等的影響下作出的自主意思;(3)難以否定對出生子女造成的身心影響,違反“子女福祉”原則;(4)以營利為目的或支付了對價之情形,存在著“女性的商品化”的負面影響;(5)醫療實踐中,因懷胎者與委托人之間所希望的醫療并不相同等原因,要進行合適的醫學判斷非常困難。基于上述理由,該報告書指出原則上要禁止代孕,但同時也允許在特定對象領域進行臨床試驗。但亦未能形成法律。與此相關,關于克隆技術、干細胞研究等生物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生命倫理問題也日益突出,也迫使日本厚生省、文部省、內閣府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生命倫理專門調查會等諸多機構對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的生命倫理、法律政策等持續做出探討。但至今為止,都尚未能形成法律。
關于胚胎的法律地位,日本現行法上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日本關于人類胚胎的唯一法律是2000年制定的《關于人類相關克隆技術等的規制的法律》(2014年5月1日最新修改)。雖然該法的目的在于“考慮到克隆技術的發展可能對維持人之尊嚴、確保人之生命及身體安全及社會秩序穩定產生重大影響”,“通過采取措施禁止克隆胚胎移植于人或動物體內,對克隆胚胎的作成、受讓及進口作出規制,以及其他合適手段,防止克隆人及雜交個體及類似個體的生成,以促進與國民生活、社會相協調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但在該法中也對“胚胎”、“生殖細胞”、“未受精卵”、“胚性細胞”、“人類受精胚胎”、“胎兒”、“人類克隆胚胎”等諸多概念下了定義,也就是說,至少在目前的日本法律中,“人類受精胚胎”是作為“人之生命的萌芽”加以對待的,在這點上,與我國“無錫冷凍胚胎案”部分表述類似。
當然,上述法律也對胚胎、人類受精胚胎、胎兒等作出了定義。依該法律,胚胎指“細胞或細胞群,且存在著經人體或動物胎內的發生過程得以成長為一個個體的可能性、胎盤開始形成前的細胞或細胞群”;人類受精胚胎指“人之精子和未受精卵受精后所生之胚胎”;胎兒指“人或動物胎內的細胞群,且存在著經胎內的發生過程得以成長為一個個體的可能性、在胎盤形成開始后的細胞群,且包括胎盤及其他附屬物”;人體克隆胚胎指“存有核之人類體細胞與人類除核卵相融合(通過受精以外的方法將復數的細胞合成為一個細胞等)形成的胚胎”。從定義可以看出,在日本現行法律上,雖然并沒有對人類胚胎的法律屬性作出特別界定,但人類胚胎至少與普通的人體細胞以及胎兒相區別,且存在著人類受精胚胎和人類克隆胚胎之分。
此外,與人體胚胎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最新法律,則是2013年通過的《關于確保再生醫療等的安全性的法律》。雖然該法律并沒有直接提及人體胚胎,但因該法律涉及再生醫療技術相關的“細胞”,與人體胚胎也有一定的關系。日本厚生省2014年根據該法律制定的《再生醫療安全法實施細則》第7條規定了從事再生醫療應當對再生醫療中使用的細胞的妥切性作出確認。其中第10項和第11項對人類受精胚胎的提供作出了規定。即“接受人類受精胚胎的提供之情形,在得到該細胞提供的同意后至少30天以內,不得用于人的胚性干細胞的培育,而應在醫療機構保管該細胞,以確保該細胞提供者得以撤回其同意的機會”;“接受人類受精胚胎的提供之情形,應滿足以下要件:(1)為生殖輔助醫療之目的受精胚,且目前不存在用于該目的之預定;就該受精胚的銷毀,確認了提供者的意思;(2)冷凍保存中的人類受精胚胎;(3)不包括冷凍保存期間在內,受精后14日之內的受精胚胎”。因此,該實施細則雖然沒有直接規定胚胎的法律地位,但亦對胚胎的提供作出了特別的規定,反映出人體胚胎區別于普通人體細胞之特殊性。
(二)以人類胚胎的研究利用為中心的行政指導
除此之外,日本并沒有法律對胚胎的法律地位作出規定,其主要通過文部省、厚生省等發布的行政指導或協會自律的方式加以規范。前者主要集中在胚胎研究的相關領域,主要的有《關于從事人類受精胚胎作成的生殖輔助醫療研究的倫理指導》(2013年修改)、《關于人類ES細胞的培育的指導》(2014年修改)、《人類ES細胞的分配及使用的指導》(2015年修改)、《從事從人類IPS細胞以及人類組織干細胞作成生殖細胞研究的指導》(2013年修改)、《以人為對象的醫學研究倫理指導》(2014年公布)、《關于利用人類干細胞的臨床研究的指導》(2013年修改,因《再生醫療安全法》的實施于2014年廢止)等。但上述行政指導基本是與胚胎細胞的研究利用相關的行政指導,日本尚不存在生殖輔助醫療相關的法令或行政指導。〔5〕米村滋人:《特殊醫療行為法(5):生殖補助醫療》,《法學セミナー》第717號(2014年10月)第99頁。從理論上來說,對于生命科學等迅速發展的領域,為確保其研究的合理性,采用得以隨時修訂的行政指導的方式而不是僵化的法律規制的方式,即“軟法”規制的方式可能更為合適。但事實上,有學者指出,之所以未能制定法律,原因之一在于應當予以遵守的規范本身并不明確。〔6〕當然,也有學者指出,在日本,除了器官移植,其他生命倫理問題并沒有成為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而生命倫理相關立法的協調和合意形成,又存在諸多困難,只好暫時采用行政指導等方式來處理。不僅如此,法學專家與醫學相關者之間的意識和考量因相互了解不夠而存在諸多不同,加之生命科學和醫學的進步日新月異,相關問題更是變得多樣而復雜,更進一步加劇了完備法制的困難性。參見川崎政司:《ヒト組織等の醫學的利用に関する法の整備の方向性》,《慶応法學》第29號(2014年)第100-103頁。不僅如此,所謂的“軟法”,對實施研究的程式和遵守事項等作出了較之通常的法律更為具體細致的規定,且對于研究者來說“指導”多被認為是與法律具有同等的權威而加以遵守,其事實上對研究者的舉手投足都產生了很大的束縛,其拘束力并不比法律要低。〔7〕辰井聡子:《生命倫理と刑法》,《ジュリスト》第1396號(2010年3月15日)第95頁。
但是,諸多行政指導也僅僅針對人類胚胎用于研究時的處理方式。〔8〕此外,上述諸多行政指導中都規定了書面的“知情同意”要求,并確保在一定條件下提供者得以撤回其“知情同意”。以《關于從事人類受精胚胎作成的生殖輔助醫療研究的倫理指導》為例,該指導對應如何對待人類受精胚胎做出了規定。依該指導第3章的規定,人類受精胚胎的作成,限于研究實施之必要且最小限之范圍內;且其得以操作的期間限于原始線條(原條)出現前的期間,且在受精胚胎作成后14天內未能形成原條的受精胚,亦不得進行操作;禁止將研究作成的受精胚胎移植于人體或動物胎內,且不得在擁有得以移植人類受精胚胎設備的室內從事研究;不得將作成的人類受精胚胎移送其他機構;研究終止時或上述得以操作期間屆滿時應立即廢棄此等人類受精胚胎。該規定亦僅限于對人類受精胚胎的特殊處理方式,且限于研究領域,并未對胚胎的法律地位作出指導。
(三)人體胚胎法律地位的判例法理闕如
在日本的司法實踐中,亦未能就人類胚胎的法律地位確立相關的判例法理。與人類胚胎相關的日本最高院判例,多是涉及人工受精后出生的孩子地位問題,其中著名的有涉及配偶利用亡夫冷凍精子人工受精死后懷胎出生的孩子與亡夫之間的父子關系認定的判例(以下簡稱“日本冷凍精子案”)〔9〕最判平成18年9月4日判タ1227號120頁(2007年2月15日)。和涉及配偶利用在美國的第三人代孕出生后的母子關系認定的判例(以下簡稱“日本代孕案”)。〔10〕最判平成19年3月23日判タ1239號120頁(2007年7月15日)。前者從現行日本民法的解釋入手,否定了其父子關系;但同時也認為,是否肯定此種情形的父子關系,應通過立法予以解決;今井功法官在該案補充意見中也提到,“是否肯定精子提供者死亡后利用冷凍保存精子的受精,若加以肯定,需具備什么條件”,都需要對醫療法制、親子法制等作出探討,以完善相關法制。后一判決則堅持現行法上的母子關系以懷胎出生為準的解釋,否定了卵子提供者與代孕出生孩子之間的母子關系;但該判決也同時指出,應從出生后孩子的福祉、希望存在遺傳基因聯系的期望及社會一般倫理對于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的倫理感情等角度探討如何完善醫療法制、親子法制。兩者雖然都涉及冷凍精子、人工受精胚胎等,但都沒有成為案件的爭點,亦未對人工受精胚胎的地位作出判斷。
(四)輔助生殖技術實踐領域的自主規制
事實上,關于人工胚胎以及輔助生殖技術的運用等,日本主要通過醫學界或醫療集團的自主規制加以規范,或者通過設置于醫院內部的倫理委員會予以規制。例如,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的“會告”和日本醫師會的職業倫理都明確禁止代孕。〔11〕http://www.jsog.or.jp/statement/html/announce_13FEB2008.html ,2015年3月5日訪問;日本醫師執業倫理則參見http://dl.med.or.jp/dl-med/teireikaiken/20080910_1.pdf,2015年3月5日訪問。關于人工胚胎的操作等,亦存在一些此等自主規制,如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日本生殖醫學會、日本生殖輔助醫療標準化機構等團體亦都提供了輔助生殖醫療方面的指引和相關的倫理指導。由于此等自主規制亦是日本生殖輔助醫療領域的“重要規范”之一,以下就此作一簡單介紹。
例如,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的“關于人類胚胎及卵子的冷凍保存與移植的見解”中就對會員明確了人類胚胎及卵子冷凍保存的要求。其要求,“實施冷凍保存及其移植時,實施機構應當對被實施者預先說明……并取得其同意,并將其書面文書加以保管”(書面知情同意);“冷凍卵子歸屬于該卵子來源的女性;冷凍胚胎歸屬于兩配子來源的夫婦;該女性或夫婦委托實施機構保管該冷凍卵子或冷凍胚胎”;“冷凍胚胎的保存期間,不超過實施對象作為夫婦持續的期間,且不超過采卵女性的生殖年齡;冷凍胚胎或冷凍卵子融解后植入采卵女性體內,且每次手術實施都需取得實施對象夫婦或女性的書面同意”;“實施本手術時,應當依所定的格式向本醫學會作出報告并備案”等。〔12〕“ヒト胚および卵子の凍結保存と移植に関する見解”(2014年6月修改),http://www.jsog.or.jp/ethic/hitohai_201406.html,2015年3月5日訪問;日本醫師會發布的《醫師執業倫理指針》也規定,體外受精及胚胎移植實行向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的備案和報告制度,參見http://dl.med.or.jp/dl-med/teireikaiken/20080910_1.pdf,2015年3月5日訪問。而對于受精卵的研究操作等,則要求有獨立于診療或醫療行為的知情同意書。〔13〕“ヒト精子·卵子·受精卵を取り扱う研究に関する見解”(2013年修改),來源:http://www.jsog.or.jp/ethic/H25_6_hitoseishiranshijyuseiran.html, 2015年3月5日訪問。此外,該學會也禁止從事胚胎提供的生殖輔助醫療,不管是配子雙方所取得的胚胎還是不孕治療后剩余胚胎,既不得移植于別的女性,也不得參與移植或為胚胎提供進行斡旋。〔14〕“胚提供による生殖補助醫療に関する見解”,http://www.jsog.or.jp/about_us/view/html/kaikoku/H16_4.html, 2015年3月5日訪問。此外,該學會還發布了關于未受精卵及卵巢組織的采集、冷凍、保存的倫理見解,關于非配偶者之間人工受精的倫理見解,關于輔助生殖醫療中多胎防止的倫理見解,人類體外受精、胚胎移植臨床應用范圍之倫理見解等諸多生命倫理見解,要求各會員予以遵守。〔15〕其詳細內容參見http://www.jsog.or.jp/ethic/index.html,2015年3月5日訪問。與生殖輔助醫療相關的另外一個學會則是日本生殖醫學會,其也發布了諸多“指引”或“聲明”,要求其會員予以遵守。〔16〕其內容多與產科婦人科學會的內容保持一致,且其未涉及人工胚胎的保存問題,此處不再贅述,詳細內容可參見http://www.jsrm.or.jp/guideline-statem/index.html,2015年3月5日訪問。
在具體實踐中,實施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會根據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的要求,對實施對象實施告知并取得其同意。其告知書或承諾書都會告知冷凍保存的期間及其費用,其內容包括“夫婦離婚之情形,或者是夫婦一方死亡之情形、妻子的年齡超過了女性生殖年齡、失蹤之情形,遵循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的會告,依倫理之妥當方法(對冷凍胚胎、冷凍受精卵、冷凍卵子)予以廢棄”。〔17〕參見ミューズレディスクリニック“受精卵(胚)、卵子凍結説明書”, http://www.muse-lc.jp/taigai/pdf/jusei2014.pdf,2015年3月5日訪問。夫婦一方死亡情形的胚胎廢棄,亦可參見醫療法人社団暁慶會ハラメディカルクリニック的知情同意書,http://www.haramedical.or.jp/news/documents/pdf/tempoEMBRYOFREEZEagreement.pdf,絹谷産婦人科“胚凍結保存の同意書”, http://www.kinutani.org/haitouketudouisho.pdf,2015年3月5日訪問。也就是說,在日本輔助生殖實踐中,除非難以確認夫妻雙方或一方的死亡,依此等知情同意,冷凍胚胎在夫妻一方或雙方死亡后都會被廢棄,而不會產生“無錫冷凍胚胎案”中的情形。當然,將來也不排除有醫生違反學會要求而出現類似情形的可能。例如,雖然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一直禁止代孕等,但仍有醫生實施代孕手術而被學會除名。〔18〕米村滋人:《特殊醫療行為法(5):生殖補助醫療》,《法學セミナー》第717號(2014年10月)第101頁。該醫生被除名后,雖然不屬于任何學會,但仍然從事著同類醫療活動,且該醫生曾進行了數例代孕手術。該事件的發生,也顯示了日本有必要進行國家層面的立法。
二、“人體組成部分”相關學說背景下的人工胚胎
日本法上雖然不存在賦予胚胎“人”之地位的規定,但在民法、刑法等解釋論上通常認為,作為來源于人類的細胞,應與通常的“物”加以區別對待。〔19〕出自日本內閣府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生命倫理專門調查會2004年7月23日報告“ヒト胚の取り扱いに関する基本的考え方”,www8.cao.go.jp/cstp/tyousakai/life/haihu39/siryo5-1-1.pdf, 2015年3月5日訪問。總體上而言,關于胚胎的法律地位,日本學界的討論多將其置于羅馬法以來的“人”“物”二分的框架中予以討論,近年來則出現了從行為視角予以討論的學說,則多將其與胎兒、身體的組成部分相比較而展開分析。
一方面是與胎兒的對比。關于胎兒,日本法律上多有特殊保護,如民法中賦予胎兒在特定情形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及繼承權,刑法上則有墮胎罪的保護,以及母體保護法上關于人工流產的規定等。從這些規定來看,雖然并未將胎兒視為完整意義上的“人”,但亦非物。如前所述,日本法律上雖然對胎兒與胚胎作出了定義上的區分,但對于體內受精胚胎,多認為將其作為胎兒加以保護也不會有什么障礙。問題在于體外受精胚胎。一般認為,并不能將體外受精胚胎作為胎兒加以對待。〔20〕本山敦:《精子·卵子·胚の所有と管理》,《NBL》第742號(2002年8月1日)第26頁。
另一方面是與身體的組成部分或人體組織的對比。較之胚胎,日本民法學界在人體組織方面的討論更為廣泛,但亦并不充分。從理論上來說,胚胎作為生殖細胞的結合,亦屬于一種特殊的細胞或細胞群,關于人體組織的相關學說,對于胚胎的討論亦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關于人體組織的討論,主要有“人”“物”二分的研究進路和“行為”進路的區分。前者關注人體組織的私法性質;后者則更多地關注人體組織的可處分性及可讓與性問題。
關于人體以及人體由來的分離物,其性質如何及應當成立何種權利,大體上有三種學說。一是所有權說,二是人格權說,三是所有權人格權統合說。〔21〕關于三種學說的整理,未特別注明的,均出自米村滋人:《醫師法講義第21回·ヒト組織·胚の法的地位1》,《法學セミナー》第720號(2015年1月)第95頁。另參見西希代子:《ヒト組織の醫學的利用に関する法的·倫理的諸問題:民事法學の立場から――ヒト組織提供行為の私法的性質を中心として》,《慶応法學》第29號(2014年)第44-45頁。所有權說認為,作為所有權客體的“物”,通常應當具備有體性、支配可能性和非人格性。據此,人體本身因難以滿足非人格性要件而不能作為所有權客體意義上的“物”,但就其分離物而言,足以構成所有權的客體,只不過該所有權受到公序良俗等的限制。依該學說,人體組織自其分離時開始成為由來者的所有物,此后的法律關系原則上依所有權法理予以解決。我妻榮、幾代通等學者主張該學說,近年來,支持該學說的學者也不少。人格權說則認為,所有權說無法應對因研究目的而使用人體分離物的情形,應當以人格權來統合,以賦予提供者“目的外使用的停止侵害請求權”。也就是說,人格權說則更接近于侵權法上的“受害人同意”的構成,并不適用法律行為總則的規定,其同意的撤回亦更為便捷,原則上允許面向將來的撤回同意。所有權人格權統合說則認為,并不能否定人體組織本身屬于客觀意義上的“物”,但同時亦包含了特定的人格價值,得以同時成立所有權和人格權。該學說包括兩種觀點:或認為就財產部分和人格部分分別成立所有權和人格權,就其財產部分肯定其可讓與性,而就其人格部分,則肯定提供人的控制權;或認為成立一個兼具所有權和人格權性質的單一的融合權利。
當然,也有學者一方面主張身體或身體的組成部分為“物”,但在歸屬關系上將其定位為人格權領域,主張人的身體構成“人格權”的客體。該學者認為,作為“人格媒介”的身體,本身就是“物”,只不過是需要特殊對待的物。但將其界定為“物”,并不妨礙在其上構建人格權。人體由來物質本身雖然是有體物,有其財產的利益,但源于人的尊嚴的法律特別對待決定了其存在著人格利益。而身體本身,并不像人體由來物質一樣存在著財產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共存,其財產利益并不被認同,而僅剩下人格利益。也正因為如此,完全可以考慮存在著以有體物(尤其是身體這一特殊的有體物)為對象的人格權。〔22〕吉田克己:《身體の法的地位(二)》,《民商法雑誌》第149巻第2號(2013年)第136頁以下。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日本學界對待人體組成部分的態度,基本上是圍繞人物二分的傳統民法理論而展開。即使將其定位為物,也將其作為特殊的所有權來考慮,或者直接將其作為人格權,兩者都無法否認人體組成部分所內涵的人格因素,需對其加以特殊對待。但上述學說都沒有直接針對人體胚胎作出定位。實際上,就胚胎而言,其與通常的人體組成部分存在著很大不同。在人體組成部分中,既有如同頭發、母乳等一樣的容易再生且其分離通常不會損害人體本身健康的分離物,亦存在著人體器官等不宜再生且其分離通常會損害人體本身健康的分離物。前者作為所有權的客體加以對待,不會有什么大的問題,也符合日常的社會現實;而后者即使將其作為所有權客體對待,也會有受到公序良俗(包括身體的不可侵性等公序良俗)等的制約;而血液、細胞等用于生物醫學研究目的時,通常會涉及人體遺傳信息等特定的人格信息,進而可能借鑒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人格權領域的最新發展,對其許可及對第三人的提供等作出嚴格控制。也就是說,即使就人體的組成部分而言,因所涉及的公序良俗各異,使用目的各異,即使將其定位為“物”,也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不同的考慮。而對于胚胎而言,其存在著孕育成生命的可能,對人之尊嚴的尊重更是顯得必要,其法律定位也就更為困難。當然,也有學者認為,精子、卵子、胚胎等得以發展成獨立人格的人體組成部分,其并不同于遺體、遺骨等過去人格的遺留物,兩者并不能同等對待,進而明確否定胚胎得以成為所有權或繼承權的標的。〔23〕本山敦:《精子·卵子·胚の所有と管理》,《NBL》第742號(2002年8月1日)第25頁。事實上,在“無錫冷凍胚胎案”中,一審法院雖然肯定了冷凍胚胎的“物”的屬性,但將其定位為一種不具有可讓與性的特殊的物,進而否定了其得以成為繼承的標的,與該學說類似。
然而,筆者認為,無論是將其定位為所有權的客體還是人格權的客體,其權利行使都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實際上,將其定位為物還是介于人與物之間的特殊存在,若都需考慮其間的人之尊嚴,其法律地位并不會有本質的不同。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控制胚胎相關的處分。在這點上,從區別于財產處分角度闡述“處分人體相關權利”的“行為”進路亦值得注意。該進路不同于人物二分的傳統進路,而是從行為角度去探討人體及其組成部分的處分合法性及其限制問題。該進路認為,雖然人體的處分多需同意要件,但僅具備同意要件并不充分;尚因不同的人體處分而需具備特定的要件,如危險性與受益之間的均衡、醫學必要性或者是他人治療利益的存在、無償性及匿名性要求等等,都構成了作為“身體公序”的人之尊嚴的必要要求。而且,關于人體處分的同意,其與通常契約中的同意并不相同,得以隨時撤回其同意。〔24〕櫛橋明香:《人體の処分の法的枠組み(8)》,《法學協會雑誌》第131巻第12號(2014年)第2570頁。當然,該作者也認為,以行為為中心探討人體處分相關的法律構造,并不否定人體及其分離物的性質決定對于人或物的概念再構成的積極意義,并不否認應當繼續分析人體及其分離物的性質決定對于人體處分法律框架的影響。〔25〕櫛橋明香:《人體の処分の法的枠組み(8)》,《法學協會雑誌》第131巻第12號(2014年)第2606頁。
從上述討論也可以看出,日本學說中并未對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作出特別討論。套用米村滋人教授的話來說,其現狀是“關于人體胚胎的法律關系,處于問題梳理不夠、且并非輕易得以下結論的狀況。一方面,人體胚胎亦得以用所有權加以衡量的觀點值得考慮,但另一方面,仍然有必要對各個具體的情形加以縝密的研討。其詳細的法律關系,仍然有待今后學說的展開”。〔26〕米村滋人:《醫師法講義第21回·ヒト組織·胚の法的地位1》,《法學セミナー》第720號(2015年1月)第97頁。當然,依人體組成部分相關學說的進路,若非要認定其具體的法律性質,其很有可能被定位為一種特殊的物。但是將其作為所有權的客體還是作為人格權的客體,則會出現分歧。因涉及生命萌芽的問題,若定位為所有權的客體,其事實上的處分或法律上的處分亦會受到人之尊嚴這一公序良俗的限制,并不能成為完整意義上的所有權,而僅可能成為特殊目的的所有權(日本學說中曾就遺體發展出了供瞻仰、埋葬等特定目的的所有權的概念)。若將其定位為人格權,則其處分原則上被禁止,且對于后續使用等,提供者具有更多的控制權,但為了醫學研究目的等必須發展出若干例外規則,如前述學說中以同意為中心構建的許可規則。
事實上,在“無錫冷凍胚胎案”中,兩審法院的說理,與日本的學說狀況具有相似之處。一審法院以人物二分為進路,雖然肯定了冷凍胚胎得以成為特殊的物,但否定了其得以成為繼承的標的;而二審法院則回避了這一性質決定,而是從涉案胚胎的相關權利歸屬上來論證,在將其定位為“人與物之間的過渡存在”這一模糊的“中間地位”后,更多地從監管權和處置權行使等行為角度對案件作出了判斷,回避了冷凍胚胎是否得以構成繼承的標的這一性質判斷。而且,從判決來看,法院也只是肯定了雙方父母的監管和處置,并未說明醫院是否應移交冷凍胚胎,更是凸顯了法院對于這一性質決定的模糊處理。
三、結語
綜上,日本法律上將人類受精胚胎作為“人之生命的萌芽”予以對待,并沒有對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作出特別規定;判例法理上亦只涉及親子關系的判斷,并未涉及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問題。目前主要通過行政指導、學會團體的自主規制等方式對受精胚胎的生殖輔助醫療使用、研究利用等加以規制。而知情同意書的普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夫妻死亡后的冷凍胚胎歸屬和監管問題。另一方面,日本學說也未能就受精胚胎的法律地位作出充分的討論,其討論的焦點多集中于“人體的組成部分”這一方面。但此等學說的發展也為未來關于人工胚胎的性質決定或行為規制提供了方向,即無論將其作為所有權的客體還是人格權的客體,對受精胚胎所內在的人之尊嚴的尊重,構成了其權利行使的限制。在具體行使方式上,以同意為中心兼顧其他要件的行為規制模式的探討,對于今后的理論發展和實踐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就人之尊嚴這一模糊的身體公序而言,其在各國的情形中可能會不同。日本曾有學者指出,一方面是對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胚胎保護與生殖領域其他法律問題,特別是與中止妊娠之間的關系。〔27〕堀田義太郎:《ヒト胚の道徳的地位をめぐる論爭狀況》,《醫療·生命と倫理·社會》第4號(2005年3月)第76頁。在我國,如何結合社會意識和國家政策將中止妊娠的法律定位與胚胎的法律地位加以綜合衡量把握,是今后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過程中須加以處理的重要問題之一。〔28〕以日本的學說討論為例,與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國家不同,在日本,對于生殖輔助醫療本身的批評并不多,而更多的是從“子女的福祉”、女性的“自我決定”等法律視角探討生殖輔助醫療技術。參見米村滋人:《特殊醫療行為法(5):生殖補助醫療》,《法學セミナー》第717號(2014年10月)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