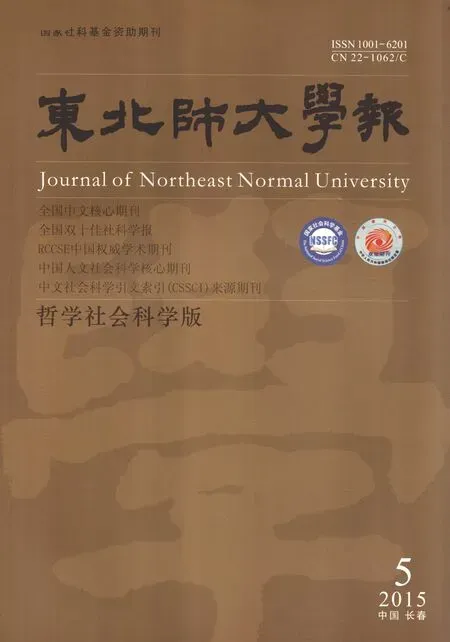慣用語塊概念化的認知解讀
都 平,吳曉春
(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100044)
慣用語塊研究成為近年來語言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語言學家嘗試從各種角度探討其性質及使用。作為一種重要的比喻手段和語言現象,慣用語塊承載著豐富的語言信息和文化內涵。20世紀早期,眾多語言學家在結構主義語言學和形式主義語言學框架下孤立地去研究語言現象,將詞匯和句法完全割裂開來。尤以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為主流派別,認為語言是高度系統化,按語法規則組成的獨立體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句法規則在句子生成中的作用,對語言中合乎語法規則的語句有一定解釋力。慣用語塊作為一種慣用化的多詞單位,是詞匯中的一種特殊范疇,是語言現象中不規則的部分。按傳統語言學觀點,大多數慣用語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死隱喻”現象,在語義和句法上是不可分解的也是不可分析的,無理據可談。隨著近年來認知語言學的發展,語言學家對慣用語塊進行了全新的、系統的解釋。Lakoff &Johnson指出,語言的隱喻處于交際和認知核心[1]。作為特殊語言表達的慣用語塊,并不單純是一個個單詞的簡單組合,其本意與其隱喻意義之間并非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源于人的概念范疇,其各個組成部分深層次地揭示了慣用語塊的概念化過程。大多數慣用語存在著許多系統的概念理據[2]。由此可見,慣用語的意義是可以推導出來的,而非任意的,慣用語的各構成項單詞的意義對整個慣用語的意義有貢獻。
一、慣用語塊語義建構的認知基礎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共性說明語言絕不完全是人的任意的創造。在語言的形成過程中,多方面的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認知環境、人的生理環境和個人認知能力等。語言形式反映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和內在認知機制。Lakoff &Johnson 提出,“我們賴以進行思考和行動的日常概念系統,從本質上是隱喻性的。”[1]經驗與認知在語言結構和功能中具有重要作用,大腦與環境的互動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認知基礎。
(一)慣用語塊的體驗性
認知語言學派認為,語言發展是人類最初對現實世界和自身的認知為基礎的。由于人類具有相同的身體生理構造,所生活的環境空間大致相同,雖然各自感知體驗存在著差異,但仍有許多共同之處,這就成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語義結構的基礎。Johnson &Lakoff認為,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心智、意義和思維三者都是體驗性的,這構成了體驗哲學的核心[3]。
Lakoff &Johnson 系統地闡述了體驗哲學的基本思想,并將其概括為三條基本原則,即:心智的體驗性、思維的無意識性及抽象概念的隱喻性[4]。其中心智的體驗性貫穿其整個哲學思想。心智體驗觀認為,人類在對外部世界種種現象的感知體驗過程中,通過自身感覺器官對外部世界的體驗以及與空間方位的互動逐步形成范疇、概念、推理,產生認知結構,并通過它們獲取意義,為人們所理解。總之,認知意義是基于身體經驗的。語言符號在大多情況下都是有理據性的,同樣遵循“現實—認知—語言”這樣一個發展規律。慣用語塊作為一種重要的比喻語言現象也是如此,其語言結構的體驗性特征主要通過身體經驗和空間經驗兩方面體現出來。慣用語的語義與我們的主觀認識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在英語中,許多隱喻的體驗性在慣用語的語義上拓展。如通過人體最基本的“聽覺、視覺和嗅覺”等體驗獲取知識,將形象性強的詞語作喻體,用來表示抽象概念的本體。因此才有:hear about,smell the cat,Seeing is believing等慣用語和諺語。漢語中這方面的表達也層出不窮,如“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嗅出點味道來”等等,由此可見,語言的表達形式是通過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來實現的,語言的體驗性構成了語言的本質,從而證明語言并非是一個自治系統。
(二)概念隱喻與慣用語塊
從結構語言學角度出發,慣用語塊始終被作為是一串符號或長單詞來孤立地研究,重在解釋其詞源、結構和意義。慣用語塊的意義是任意的,不可推導的。認知語言學認為多數慣用語是人們系統概念的產物。Lakoff & Turner曾指出:“概念隱喻不是一種語言表達式,而是從一個概念域向另一個概念域的映射。”[5]103即以源域的經驗來理解目標域的經驗,源域的部分特點被映射到目標域上,后者因前者而得到部分理解。
慣用語塊是高度概念化的隱喻形式,其充分體現了本族語者的思維方式。以英語中表達情感的慣用語為例,多是采用人類概念系統中最基本的概念來表達其抽象性的意義。以“FIRE”概念構成的慣用語為例,將許多抽象概念的理解通過其自身不同特征的映射而實現。
(1)ANGER IS FIRE
The bishop was breathing fire over the press release.
(2)CONFLICT IS FIRE
The murder of the boy by the police sparked off the riot in Greece.
(3)LOVE IS FIRE
The fire between the lovers went out.
(4)LIFE IS FIRE
The robber snuffed out the little baby's life.
據作者篇末自署,這篇序文撰于紹興二十六年(1156),其時朱熹(1130-1200)才27歲。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段文字中,朱熹兩次提到了“玩”:“奇古可玩”“披筐篋卷舒把玩”。他的玩法自有特點,就是將石刻拓本視同書卷,“卷書把玩”。最后一句提到的“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為橫卷若書帙”,也是從形制角度,將刻石拓本視同書帙。總之,朱熹受其父癖愛金石收藏的影響,很早就養成了對于金石學的興趣,但他對金石拓本的玩賞和理解著重于文獻與文本,顯然與歐陽修、趙明誠等前賢不同。
(5)IMAGINATION IS FIRE
The conver sationset fire to his dreams.
(6)ENTHUSIASM IS FIRE
His writings fanned the flames of the readers.
由此可見,與“火”相關的慣用語塊體現了“火”各種不同特征及隱喻概念。例如慣用語“fire up”的意思是“to be angry”,是根據隱喻概念ANGER IS FIRE 得來的,其意義通過源域(fire)和目標域(anger)之間的對應–the intensity of fire is the intensity of anger 得來的。以上分析表明,慣用語中的隱喻體現著人的概念結構和概念知識。
(三)概念轉喻,常規知識與慣用語塊
與隱喻一樣,轉喻也是一種重要的思維和認知方式。“與概念隱喻一樣,概念轉喻的實質是概念性的、無意識的和自發的認知過程”[6]。與概念隱喻相區別的是,概念轉喻所涉及的是“接近”和“突顯”的關系。轉喻映射發生在單一認知域中,不涉及跨域映射[5]。隱喻和轉喻之間是一種連續體關系。隱喻和轉喻都是概念性的,具有系統性、生成性和概括性的特點。Radden &K?vecse認為,“概念轉喻是指相同認知域中的概念映射,即一個概念實體(即源域)為另一個概念實體(目標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認知操作過程”[7]。轉喻是在同一認知域中用易感知、易理解的部分替代整體或整體其他部分。轉喻的主要功能在于同一認知模型中,用一個范疇去激活另一個范疇,這樣后者就得到突顯。作為慣用語的生成機制,轉喻需要常規知識的共同參與,將認知對象范疇化,并形成各種圖式或框架知識,這些知識構成認知或推理的基礎。
K?vecses &Szabo認為,常規知識指的是特定文化群體所擁有的概念領域的共有認識,比如形狀、大小、用途、功能等[2]。不論在哪種文化中都有一些對事物的基本的知識,人們可以用這些基本知識去認識或推理。例如:與“手”相關的習語在各種文化中幾乎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有文化常識,理解上不會造成太多困難。如He is a green hand這句話,我們用agreen hand 代表毫無經驗的新手,運用的概念隱喻就是THE HANDS STANDS FOR THE PERSON。下例句中慣用語塊的語義是建立在概念轉喻基礎上的。
此句中的慣用語塊make head or tail of,從傳統意義上說,head和tail都是單數可數名詞,前面使用零冠詞是不合乎語法規范的。而在概念轉喻HEAD STANDS FOR INTELLECT 和HEAD OR TAIL STANDS FOR SENSE的作用下,其意義可以被映現為“明白,弄清楚”。在認知解讀的過程中,源域“head”和“tail”的特征被放大,并與目標域的整體過程相對應,使目標域在概念上豐富起來,即“對事物的了解程度如同對自身的頭尾一樣清晰明了,于是這個慣用語塊理解起來就比較簡單了。
二、慣用語塊的認知語義特征
傳統的語言學觀點認為,慣用語的語義是獨立于人的概念認知系統之外的。而從認知角度分析,作為慣用化了的多詞單位的慣用語,其整體并非是各組成項之和。慣用語和其意義之間的聯系系統性地受制于概念結構。慣用語塊有其自身的認知語義特征。
(一)慣用語塊的組構性
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慣用語的主要特征有結構的凝固性和非組構性,語義的晦澀性等特點,慣用語是封閉的、不可預測和不可分析的。許多慣用語諸如spill the beans,kick the bucket都是“死隱喻”,沒有比喻義。慣用語的組成項對慣用語的整體意義沒有貢獻。對此,眾多認知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發表了不同見解,并提出了很多理解和加工模式。從語言認知的角度,慣用語塊的構成項的意義對整個慣用語的意義有貢獻,在語義和句法上具有組構性和分析性。Lakoff,Kovecses &Szabo等研究表明,大多數慣用語塊產生于概念系統,而非單純的語言詞匯,其構成詞項系統地發揮作用。慣用語塊是可以分析的,慣用語塊的比喻意義是可以推導的,而非完全是任意的,慣用語塊的意義是有系統概念理據的。例如,在使用慣用語塊have an eye for時,語言使用者根據經驗有可能形成“能看出……,具有識別……價值的能力”這樣的字面場景,從而獲取語言構造的整體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慣用語塊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分析性。
Nunberg,Gibbs,Cacciari &Gluckberg分別就習語不可分析性的傳統觀念提出了他們各自的觀點。根據語義分解程度的不同,Nunberg將慣用語劃分為三種不同類屬[8]。第一類是分解性慣用語,其各組成成份的詞義與慣用語意義是相匹配的,例如pop the question(求婚)。第二類是不規則可分解的慣用語,這類慣用語各組成部分的詞義與慣用語意義有一定關聯,但并不完全匹配。如spill the beans(泄密)。第三類是非分解的慣用語,其組成部分詞義與慣用語意義不相關聯,如kick the bucket(死亡)。Gibbs通過實驗來證明只有少數習語是不可分析的或不可分解的“死喻”[9]。它們在語義上是空白的。如:by and large,shoot the breeze等。而絕大多數的慣用語都是組構性的或可分析的。Gibbs等認為可分析的慣用語要比不可分析的慣用語容易理解。Cacciari &Gluckberg按照慣用語成分與意義的關系,將慣用語分為可分析隱性(analyzable and opaque)、可分析顯性 (analyzable and transparent) 及“準隱喻型” (quasimetaphorical)[10]。同時,他們還提出了結構性假說。其觀點認為,慣用語的組成成分以節點形式存儲于心理詞典中,各節點之間緊密相連,有機結合,作為整體的慣用語單元被激活。
(二)慣用語塊的意象性
意象圖式是慣用語塊隱喻的基礎之一。意象圖式是在互動體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從而形成了范疇、概念和意義。Johnson羅列出了27種簡單意象圖式,并指出人類基于此可建構出其他概念和概念體系。Lakoff指出“意象圖式是人們與外界相互感知、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再現的動態性模式,這種模式賦予我們經驗以連貫和結構。”[11]267作為一種抽象的認知框架結構,意象圖式對具有相似關系的多個事物反復感知體驗。在人的思維、感知和行為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種抽象關系和具體意象。在人類的認知體系中,意象圖式處于相對具體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s)和相對抽象的命題式結構之間[12]。意象圖式不是具體的形象,而是抽象的認知結構,是“基于身體體驗的思維,是從具體域到抽象域的隱喻投射”[11]275。從本質上來講,我們的空間域和存在于我們抽象域中的諸多概念都是在意象圖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在人體對自然的體驗中,對“上—下”、“前—后”、“多—少”對應關系的感知產生相應的意象圖式。這些空間或非空間的對應關系就為隱喻概念提供了經驗基礎。例如:通過隱喻投射我們得到具體概念:MORE IS UP/LESS IS DOWN。擴展到抽象領域,我們有了HIGH STATUS IS UP/LOW STATUS IS DOWN 等隱喻概念。這種以意象圖式為基礎,從一個領域映射到另一個領域的心理意象過程被稱為意象圖式隱喻。語言中的慣用語塊大都是以意象圖式隱喻為基礎催生出豐富的隱喻表達[5]106。根據意象圖式隱喻
TOWARDS COMPLETENESS IS UP/TOWARDS FANALITY IS DOWN,可以有如下例子:ups and downs,butter up,lay down。這些慣用語的喻義都是與小品詞up,down構成的“上—下”意象圖式隱喻緊密相關的。
慣用語的隱喻性使我們有理由認為意象圖式隱喻是許多慣用語的認知理據。例如在spill the beans中,spill相當于“揭露”或“暴露”,意義映射到“let out”或“divulge”上。“豆子”和“秘密”從概念上來講并無明顯的相似性,通過意象圖式結構,我們得知“豆子”和“秘密”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通過抽象思維,將beans的意義映射到secret之上。
(三)慣用語塊的生成性
Cowie認為慣用語具有結構的凝固性和語義的整體性特征[13]。其特點是結構相對固定,構成詞是線性排列,構成詞的順序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容改變的。不能對慣用語的結構、構成詞做更改、增刪、移動,任何改變將直接導致慣用語意義的損失。作為隱喻的語言表現形式,慣用語根據交際或修辭的需要,對其自身的結構進行調整或變更自身原有的功能,生成新的形式,創造出新的意義,產生臨時變體[14]35。由于認知主體的參與,慣用語體現了人類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具有創新性的、有一定生成能力的慣用語表達更生動、形象,對人們理解抽象概念,發展推理能力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慣用語的臨時變體通過對自身結構中小品詞的移動、替換實義詞、構成詞分散重組等手段實現。
語言結構中的小品詞,如in,out,on,up,在慣用語結構中有時可靈活使用,例如:
(8)If you don'tmakeyourmindupsoon,I'll make it up for you.(如果你不趕快作出決定,我就要替你決定下來。)[15]160
慣用語的原形是make up one's mind。通過小品詞的移動,變換了句子結構,句子意義并未發生改變。
在特定情況下,語言使用者根據需要,臨時替換慣用語中的實義詞,創造出新的變異形式,突出表達內容,達到特定的交際效果。例如:
(9)There is the plain speaker who tells his immediate superior that the affair he is having with his secretary isthetalkoftheofficeand that he had better be careful.[14]40
此例中的thetalkoftheoffice(辦公室議論的話題)是在慣用語thetalkofthetown(眾人談論的話題;全城談論的話題)的語義基礎上,通過空間類比,替換實義詞創造出新的臨時變體,體現了慣用語隱喻意義的生成性特征。
有些慣用語在不同理據的作用下,在原有慣用語的基礎上通過移動小品詞、調換構成詞順序、結構詞分散重組等仿造生成出新的慣用語。例如:
(10)It is horribly expensive to play golf in America.And when you consider the relatively improved reward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thenthegrassontheothersideoftheAtlanticdoes notlookall that muchgreener.(在美國打高爾夫球是貴的嚇人,但考慮到世界其他地方所提高的費用,那么,大西洋彼岸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15]163
此例中臨時生成變造出的慣用語的原形是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這山望著那山高)。在原有焦點詞義的基礎上通過添加否定詞、修飾語,變更實義詞等手段,使慣用語在形式上發生了較大的變異,形成新的隱喻意義。
三、結 語
不同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語言的靜態描寫,認知語言學對語言進行動態分析,從而使人們對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慣用語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16]。實例證明,慣用語塊作為人類概念體系的產物,在語義層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解的,具有可分析性。概念隱喻、概念轉喻和意象圖式隱喻共同參與了慣用語塊的認知和理解,充分體現了語言使用者的概念結構和思維方式。
[1] Lakoff G,M 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4.
[2] K?vecses,Z,P Szabo.Idioms:A View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J].AppliedLinguistics,1995(17.3):326-355.
[3] Johnson M,G Lakoff.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J].CognitiveLinguistics,2002(13.1):245-263.
[4] Lakoff G,M Johnson.PhilosophyintheFlesh-The 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5] Lakoff G,M Turner.MorethanCoolReason:AField GuidetoPoeticMetaphor[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6] 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116.
[7] Raden A,Z K?vecses.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In Panther,K-U.& Radden,(eds.).Metonymy inLanguageandThought[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21.
[8] Nunberg G.et.al,Idioms[J].Language,1994(70):491-537.
[9] Gibbs R W & Nayak N P.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f Idioms [J].Cognitive Psychology,1989(21):100-138.
[10] Cacciari C & Glucksberg S.Understanding Idiomatic Expressions:The Contribution of Word Meanings[A].In:Simpson,G.B.(ed.).Understanding WordandSentence:AdvancesinPsychology77[C].Amesterdam:North Holland,1991:221-225.
[11] Lakoff G.Woman,FireandDangerousThings:What CategoriesRevealabouttheWorld[M].Chicage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2] 藍純.認知語言學與隱喻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58.
[13] Cowie,A P.The Treatment of Collocations and Idioms in Learner Dictionaries[J].AppliedLinguistics,1981,2(3):223-235.
[14] 華先發.英語習語的臨時變體[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3).
[15] 駱世平.英語習語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16] 都平,吳曉春,王清正.外語學習者邏輯連接詞使用意識的調查研究[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