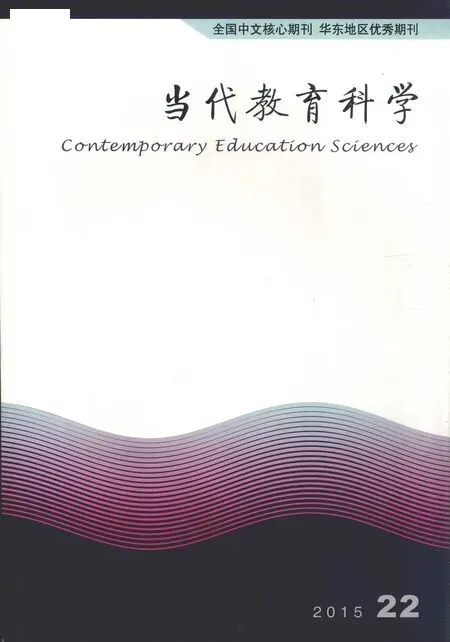美國教師語言研究的進展與啟示
●呂長生 劉登琿
美國教師語言研究的進展與啟示
●呂長生 劉登琿
美國教師語言研究可以分為行為分析、話語分析和專業發展三個階段。其中行為分析階段具有基于教師提問和好教師探究教師語言的特征,話語分析階段具有建立量化分析模式和確立基本研究領域的特征,專業發展階段具有探析教師語言內部結構和拓展研究領域的特征。借鑒美國的研究成果,我國在教師語言研究中需做到拓展研究的理論基礎、深化研究的領域分支和采用實證的研究方法。
美國;教師語言;研究
自20世紀初至今天,依據研究的社會背景、所采用的理論基礎和研究的系統性,可以把美國教師語言研究分為“行為分析”、“話語分析”和“專業發展”三個階段。由于社會變革的需求以及教育領域本身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差異,在每個階段教師語言研究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借鑒美國教師語言研究的歷史經驗,對加快我國教師語言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行為分析”視域下的教師語言研究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下,美國進入了“高效率、科學化、標準化”的時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在美國產生了重要影響,教師語言研究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中興起和發展的。
(一)行為主義心理學催生行為分析的誕生
20世紀初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形成和發展,為教師語言研究奠定了科學依據和研究方法。第一,行為主義心理學顯著特點是采用運動反應的模式識別所有的心理現象,因此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注重“測量可觀察的外顯行為”。而教師語言行為所具有的雙重特殊性(第一,教師語言行為是占據課堂教學時間最多的行為;第二,教師語言在課堂教學中扮演的影響學生的行動、形成和學生更親密的關系、作為思想和知識的有意識的運載工具的重要作用[1]),使其成為了課堂教學中最容易觀察和記錄的“外顯行為”,因此對教師語言進行行為分析成為了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進教師語言行為、提升課堂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的重要手段。第二,把行為主義心理學引入到教師語言研究之中,轉變了研究的方法,即教師語言研究從反省的主觀分析法中解脫出來,能像其它學科一樣采用客觀研究的路徑,這樣對教師語言行為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在實踐應用中便有了方法論基礎。
(二)行為分析視域下的教師提問和好教師語言的特點
在行為分析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沒有形成一定的研究體系,其研究主要借助于教師提問和好教師顯現出來的。
1.基于教師提問探究教師語言的影響
教師語言研究是從教師提問中延伸出來的,并借助于教師提問的研究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從得出的分析數據來看,首先,教師在一個教學日內平均會問大約300-400個問題,提問頻率在每分鐘2到4個問題;其次,師生問答的時間占據了全部課堂教學時間的大約80%-85%,其中教師語言表達的時間大約占據課堂教學時間的三分之二(R.Stevens,1912[2];Miller,1922[3];Haynes,1935[4];Curtis,1943[5])。基于研究數據,教師語言的影響呈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要改善教學,教師通過語言表達必須能提出激發學生反省性思維的問題;其二,教師語言行為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的提升以及態度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雖然這些研究均是在教師提問中進行的,沒有形成一定的研究體系,但是為美國五六十年代形成完整的系統化、科學化和規范化的教師語言研究體系作出了鋪墊。
2.基于“好教師”探究教師語言的特點
教師語言行為特點作為甄別“好教師”和“差教師”的標準之一,是從整體上對教師語言的總體形象進行描述。根據霍特林(Hotelling,1940)、柔(Roe,1943)等人的研究,“好教師”的語言特征一般表現為“言行穩定一致”[6]、語言表達是“清晰的、悅耳的、簡潔的、有效的和幽默的,而不是漫無目的的”以及要善于使用學生能理解的語言表達方式來進行教學[7];而“差教師”的語言特征則表現為諷刺、挖苦學生、啰嗦不停、言行霸道、無幽默感。[8]
二、話語分析視域下的教師語言研究
隨著話語分析理論的成熟,教師語言研究從行為分析轉向了話語分析。在話語分析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建立了各種量化分析模式和確立了研究的基本領域。
(一)話語分析的客觀需求和演變過程
隨著五六十年代教育變革的推進,核定教師效能成為了教育變革的重心,目的是檢驗教師的教學是否有效。效能核定促使“好教師這個詞變成了有效教師”。[9]在核定教師效能中,人們發現教師語言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如卡塞爾和約翰斯(Cassel&Johns,1960)發現,“與同事和學生談話時要字斟句酌”和“教師語言的幽默性”在衡量有效教師的標準中占據第一位和第三位。[10]教師語言在核定教師效能中的重要性,使人們意識到要深入研究教師語言,必須為其找到堅實的理論基礎、來對教師語言進行科學、系統的研究。話語分析理論的成熟并被引進教育學領域,為教師語言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也帶來了新的生機。
1952年,哈瑞斯(Harris,1952)[11]在《語言》期刊上發表了《話語分析:示范性文本》一文。在文中,哈瑞斯從理論分析和實踐舉例相結合的視角為“話語分析”建立了一套系統化、科學化的分析框架,此后話語分析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并影響到了社會各個領域。在話語分析浪潮的影響下,貝拉克(Bellack,1966)等人在呈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報告《課堂中的語言》中,參照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把教學過程視為教師“發話”和學生“接話”的特定“語言游戲”過程。[12]基于此他們從內容分析和統計分析兩個視角對課堂教學中的口頭語言和非口頭語言進行了話語分析,這標志著“話語分析”在教師語言研究中的真正建立。
(二)話語分析視域下的教師語言量化模式和基本領域
在話語分析的英美學派、福柯學派和批評話語學派中,對美國教師語言研究影響最大的是英美學派。英美學派研究的側重點在于語言和語言的使用以及語言使用的語境。[13]在此影響下,教師語言研究建立了量化分析模式,確立了研究的基本領域。
1.教師語言研究的量化模式
在教師語言的量化分析模式中,影響最大的是弗蘭德斯的師生交互作用模式。弗蘭德斯通過對不同年級和不同學科進行課堂觀察,把師生言語分為了10類,其中7類是教師語言行為。依據對學生產生影響的途徑,又分為直接影響學生的語言(包括講解、指示、批評或維護權威)和間接影響學生的語言(接納感受、贊賞或鼓勵、歸納或采用、提問)。[14]在分類的基礎上,弗蘭德斯通過矩陣分析用曲線來描述教師的語言行為組合模式,進而推論教師語言對學生所發生的影響。[15]雖然此法對分析教師語言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作為一種課堂分析技術,具有強烈的結構化、定量化研究的特點,這為它在課堂分析中的運用帶來了極大的局限。[16]這種局限性的客觀存在促使研究者在80年代之后開始轉向從人種學視野下探究教師語言的內部結構。
2.教師語言研究的基本領域
在話語分析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的基本領域大致形成,這主要包括教師語言的類型、模式和功能。第一,在教師語言類型的研究中,貝爾斯(Bales,1979)在阿米登和哈克(Amidon&Hough,1967)的 VICS(即The Verbal Interaction Category System)分析系統上,從語言功能和使用內容兩方面將教師語言分為情感性教學語言和認知性教學語言,其中每一類型包括三對范疇六個子類型。情感性語言包括:表示滿意和表示不滿、表示支持和表示異議、表示同意和表示反對;認知性教學語言包括請求指令和發出指令、提供信息和索取信息、提出意見和征求意見。[17]第二,在教師語言模式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史密斯(Smith,1970)等人的循環模式。史密斯在貝拉克等人研究的基礎上,把教師的語言行為分為兩類,即情節語言行為(即師生對話中的語言轉換)和獨白語言行為。[18]這兩種語言行為在課堂教學中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融為一體的,進而形成一個語言系列中的八個成分:定義、描述、名稱、陳述、報告、替代、評價和觀點,這些成分在教師講授過程中自動形成依次循環的系列,指導著課堂教學的有序進行。第三,教師語言作為知識傳遞的手段之一,其最為關鍵的功能就是對學生的學習起著促進的作用,如所羅門(Solomon,1964)[19]和希勒(Hilier,1971)[20]通過實證研究分別發現教師語言的清晰性能促進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而“教師教學語言的模糊性和學生的論文成績以及教師講解有效性之間呈現負相關”;科根(Cogan,1958)[21]和斯波爾丁(Spandling,1963)[22]通過課堂觀察發現,教師語言的邏輯性也能促進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
三、“專業發展”視域下的教師語言研究
在八十年代,隨著教育改革的新一輪開啟和教師專業發展成為教師研究的主流,教師語言研究也從話語分析轉向了專業發展。在轉向中,教師語言研究出現了研究范式的轉變并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
(一)教師語言研究轉向專業發展視域
1980年,《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題為《Help! Teacher Can Not Teach》的文章,分析了教師專業素質低下及其對課堂教學的負面影響。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了美國上下的反思,加速了教師研究的轉向,其標志是出臺了《明日之教師》。《明日之教師》的核心精神是把“教師視為一種專業”,呼吁“要使教師成為更有效能的專業人員”、“建立入選教師專業的標準”。[23]在這種背景下,各種教育組織和教育研究者開始研制各種專業化標準和教師準入的資格制度,目的是“使師資培養應達到專業標準”[24]。而教師語言和教師語言表達能力作為教師專業標準的維度之一成為了關注的重要對象,如吉比尼和威爾瑪(1986)用來測評實習教師專業素養的個人能力測驗分析圖中,有三條是教師語言表達能力的要求,即“使用能被學習者接受的口語和書面語”、“使用一系列功能性語言的,或非言語的交流”、“說出毫不含糊的指示語和做出明確的說明”。[25]此后,教師語言研究便在教師專業發展視域展開了新一輪的研究。
(二)專業發展視域下教師語言范式轉變和視域拓展
和話語分析視域下的研究相比,在專業發展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出現了研究范式的轉變和研究視域的拓展
1.專業發展的指向加速研究范式的轉變
在話語分析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遵循的是“IRE(Initiate-Respond-Evaluate,即提問—回答—評價)”模式。IRE模式的“系統預設”遮蔽了教師語言的動態生成性,“數據統計”割裂了教師語言的整體性[26],這使教師語言研究越來越數字化和科學化,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教師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于是突破話語分析對教師語言的研究約束,尋找更好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成為了研究者探究的重點。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以整體性研究為前提,開始引入質性研究中的田野考察,力圖把教學語言研究放置到人種學研究的視野之下。在轉變過程中,研究者開始著力探究教師語言的內部結構,分析教師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現象、文化意義以及教師語言所代表的社會現象和社會意義,試圖超越量化分析對教師語言研究的束縛,其中卡茲登(Cazden,1986,2001)對教師語言內部結構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卡茲登依據社會文化理論和建構主義理論,把教師主導的課堂語言分為“課程話語”、“控制話語”和“個性話語”,并設定了話語功能的三重核心:命題性動能(指命題性信息的溝通)、社會性功能(指社會關系的構筑與維系)和表達性功能(指說話者的個性、態度的表現)。[27]卡茲登雖然提出了話語的三重功能,但是其更為重視“互動-交流”模式中的社會性功能和表達性功能,而不是“習得-傳遞”模式中的命題性功能上。通過卡茲登的研究,人們認識到教師語言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工具,更是反映了教師話語權利和話語角色以及權利和角色背后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28]
2.專業發展指向催生了研究視域的拓展
在專業發展視域下,教師語言研究拓展的新領域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在教師語言專業化特征的探究中,約翰遜(Johnson,1999)基于解釋學理論認為教師語言的專業化特征表現為:解釋性、情境性和推理性,他給出了大量的案例來佐證其觀點,說明教學語言在教學過程中的應用,并為一線教師開出了“處方”,即在實踐中要最大限度地發揮語言的功效,提升教學的有效性。[29]約翰遜從解釋學做出的此項研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理論分析和案例舉證相結合進行分析,為教師語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巴克曼(Bachman,1990)借鑒認知心理學理論,把教師語言意識(Teacher Language Awareness,即TLA)視為是教師依據課堂情境的變化進行語言交流的能力,包括語言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機制三部分。語言能力包括組織能力(即語法能力和語篇能力)和語用能力(即言外能力和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是指促使語言使用者決定交流目標、評估交流資源、規劃并實施溝通的嚴格的過程;心理機制作為人類交流的一部分,涉及聽覺過程、發音過程和神經過程。[30]此分類很好地解釋了教師語言意識的本質及其運行的復雜性,后續的研究者大多以此框架為參考來對教師的語言意識做出劃分,在本質上和巴克曼的分類并沒有差異。
第三、根據社會互動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者發現,雖然教師語言及其行為約占課堂教學行為和時間的三分之二(Corey,1940[31];Bialystok,1978[32]),但影響課堂教學有效性最大的因素,是教師的非語言因素(Mehrabian,1968[33];Birdwhistell,1972[34])。因此,研究者開始對非語言行為進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伍爾福克和布魯克斯(Woolfolk& Brooks,1983)的研究最具影響力。伍爾福克和布魯克斯通過課堂觀察、師生訪談等方式,建立了教師非語言行為研究的問題框架:問題1——教師如何運用自己的非語言行為表達思想、期望、和態度;問題2——教師如何揭示自己非語言行為中的這些期望和態度;問題3——學生如何解釋教師非語言行為中的變量;問題4——在教學和課堂管理中非語言交流所起的作用。[35]在提出這四個問題之后,兩位通過實驗進行了驗證,得出結論如下:1.空間關系、輔助語言、合作性語言行為是影響四個問題的共同因素;2.除上述三個因素之外,文化差異和特定的種族或性別是影響問題1的因素,多重行為是影響問題2和問題4的因素,非語言交流中的年齡差異是影響問題3的因素。兩位提出的此研究框架成為了研究教師非語言及其行為的經典框架,后續研究者在對教師語言和非語言及二者關系研究中大多從這一框架出發進行研究。
四、美國教師語言研究對我國相關研究的啟示
我國研究者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在教師語言研究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和美國較為成熟的研究相比,我國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學習和借鑒美國教師語言研究應拓展研究的理論基礎、深化研究的領域分支和采用實證的研究方法。
(一)拓展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國內,雖然吳康寧(1994)等人從社會學中的“角色理論”[36]、沈貴鵬(1994,1997)從社會學的“互動理論”[37]、葛棣華(1990)從信息論[38]等對教師語言進行研究,但是由于我國研究者認為“在教學的諸要素中,教學語言是教學論研究的起點,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是對教學本質最真實的反映”[39],因此許多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就把教師語言研究囊括進了教學論的研究體系之中,教學論也成為了我國教師語言的主要理論基礎,這也是我國教師語言研究和美國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在美國,研究者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會尋找不同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建基于多元化理論,這是美國教師語言研究持續發展的生命力之一。因此,我國在教師語言研究中如何拓展研究的理論基礎,把教師語言研究放在更廣的理論視域中加以分析,突破教學論的束縛是亟需加強的研究。
(二)深化研究的領域分支
對教師語言進行研究,其視角有兩個:其一是對教師語言自身進行的靜態研究,其探究的主題包括教師語言的性質、功能、類型、使用原則、模式等,其目的在于科學地認識教師語言;其二是對教師語言的動態研究,探究教師語言在教育情景中和教育內容、教育對象、專業發展和教育改革等之間的關系,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師運用語言的能力。在美國,研究者在對教師語言進行了靜態的、宏觀的研究之后,就開始從動態的、微觀的視角對教師語言進行分析,目的也從科學地認識教師語言轉變為了如何在實踐中提高教師運用語言的能力。而我國研究者雖然在研究中也提出了提高教師運用語言的能力,但其實質仍舊是在教學論視野中的宏觀論述和經驗式總結。因此,在我國的教師語言研究中如何轉變研究思維,把研究從靜態的、宏觀的層面轉移到動態的、微觀的層面,是今后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采用實證的研究方法
在我國的教師語言研究中,理論研究者一般采用理論分析的方法,而工作在一線的教師大多使用經驗總結的方法,這就使得“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之間的鴻溝難以抹平”[40],歸根結底是我國缺少一種把二者聯系起來的中介機制——實證研究。其一,實證研究需要理論分析的指導,來奠定科學的分析方法;其二,經驗總結為實證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為實證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奠定了基礎。這樣實證研究就成為了理論分析和經驗總結的“粘合劑”,是二者溝通起來的“橋梁”,這在美國的教師語言研究中表現最為明顯。因此,借鑒美國研究者的多元研究方法,我國研究者如何在實證研究視角下通過多元的分析方法對教師語言進行研究,并從大樣本的分析中得出教師語言的一般規律,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1][美]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M].姜文閔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96.
[2]Stevens,R.(1912).The question as a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instruction:A critical study of class-room practice(Vol.48).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3]Miller,H.C.(1927).The new psychology and the teacher.New York:Albert&Charles Boni.
[4]Haynes H C.Relation of teacher intelligence,teacher experience,and type of school to types of questions[D].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1935.
[5]Curtis,F.D.(1943).Types of thought questions in textbooks of science.Science Education,27(2),60-67.
[6][8]Hotelling,H.(1940).The teaching of statistics.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11(4),457-470.
[7]Roe,W.S.(1943).How Good a Teacher Are You?.The Clearing House,17(6),362-365.
[9][美]加里.D.鮑里奇.有效教學方法[M].易東平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4.
[10]Cassel,R.N.,& Johns,W.L.(1960).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Effective Teacher.NASSP Bulletin,44(259),119-124.
[11]Harris,Z.S.(1952).Discourse analysis:A sample text.Language,28(4),474-494.
[12]Bellack, A.A., Hyman, R.T., Smith Jr, F.L., & Kliebard,H.M.(1966).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New York:Teache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13]黃國文、徐珺.語篇分析與話語分析[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0).
[14][15]Flanders,N.A.(1961).Analyzing Teacher Behavior as Partof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Merrill.;Flanders, N.A.(1970).Analyzing teacher behavior.Addison-Wesley P.C.
[16]寧虹,武金紅.建立數量結構與意義理解的聯系——弗蘭德斯互動分析技術的改進運用[J].教育研究,2003,(5).
[17]Bales,S.N.(1999).Effective Language for Communicating Children’s Issues.Washington,DC:Coalition for America’s Children with the Benton Foundation.
[18]Smith,B.O.,Meux,M.O.,&Coombs,J.(1970).A Study oftheLogic ofTeaching.Urbana, 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Solomon,D.,Rosenberg,L.,&Bezdek,W.E.(1964).Teacher behavior and student learning.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55(1),23.
[20]Hiller,J.H.(1971).Verbal response indicators of conceptual vagueness.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51-161.
[21]Cogan,M.L.(1958).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and the 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ir Pupils:II."Trait"Analysis.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27(2),107-124.
[22]Spaulding,R.(1963).Components of Observed Teacher-Pupil Transactions in a Sample of Elementary SchoolClassrooms.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3]范寧.霍姆斯協會報告:明天的教師(1986)(上)[J].全球教育展望,1988,(5).
[24]Gardner,D.P.,Larsen,Y.W.,&Baker,W.(1983).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5]沈劍平.美國本科畢業的實習教師能力評定條目[J].比較教育研究,1987,(5).
[26][28]Cazden,C.B.(2001).The languag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The languag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53-79.
[27][日]佐藤學.課程與教師[M].鐘啟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353.
[29]Johnson,K.E.,&Ma,P.(1999).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Reasoning in action.New York:Heinle&Heinle.
[30]Bachman,L.F.(1990).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Corey,S.M.(1940).The teachers out-talk the pupils.The School Review,48(10),745-752.
[32]Bialystok, E, M Frohlich & J.Howard(1978).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wo Distinct Learning Settings.Project Report.Toronto:Modern Language Centre.
[33]Mehrabian,A.(1972).Nonverbal communication.Chicago:Aldine.
[34]Birdwhistell,R.L.(1978).Nonverbal Communication:A Research Guide and Bibliography.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s,5(1),70-70.
[35]Woolfolk,A.E.,&Brooks,D.M.(1983).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eaching.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10,103-149.
[36]吳康寧.教師課堂角色類型研究[J].教育研究與實驗,1994,(4).
[37]沈貴鵬.初中課堂口頭言語互動研究 [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4,(1);沈貴鵬.師生課堂口頭語言互動研究[J].教育科學,1997,(2).
[38]葛棣華.課堂教學語言初探[J].課程·教材·教法,1990,(11).
[39]石鷗.論作為教學論研究起點的教學語言[J].上海教育科研,1997,(8).
[40]劉慶昌.教育知識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13.
(責任編輯:劉君玲)
呂長生 劉登琿/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