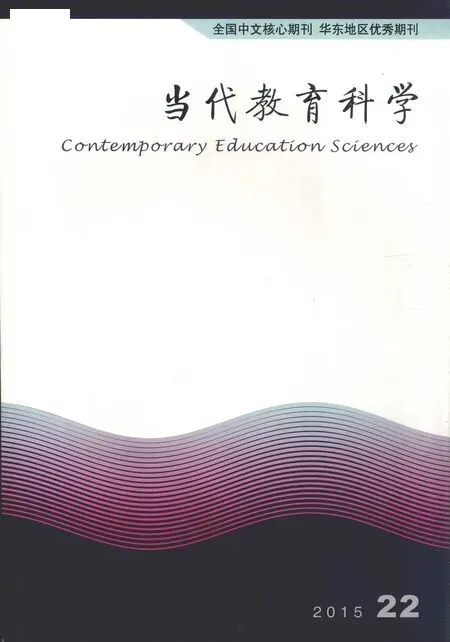從校本教研看教師實踐知識創生的可能性*
●張曉蕾
從校本教研看教師實踐知識創生的可能性*
●張曉蕾
新課程改革深化階段,學校教研組及校本教研活動被視為教師共同探究、建構實踐知識的平臺。本文借助教師知識理論討論對上海市兩所初中教師校本教研學習過程及成效分析發現,教研活動為教師獲取教學實踐中的知識提供支持,但不同類型教研活動及其間學習過程的差異使教師提煉并建構的實踐知識呈現差異。為持續推進實踐知識建構,借助多元分享性學習材料開展不同類型的教研活動,重視從探究的角度引導教師共商教學實踐尤為關鍵。
校本教研;教師學習;實踐中的知識;實踐知識
我國基礎教育學校有教師校本學習的傳統,教研組支持教師基于日常教學實際問題開展學習。新課程改革深化階段,基于學校教研組的校本教研應是教師們共同探究、建構實踐知識的途徑。①但當前,教師參與校本教研活動究竟學到什么,教師知識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建構,這些涉及教師學習過程和成效的問題尚缺乏實證研究來回應。本文基于2013年5月至12月間對上海市兩所初中調研的數據展開分析,旨在呈現教師校本教研學習經驗,探索其間實踐知識建構的可能性。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教師學習的研究從先前認知-行為理論路向轉為基于社會建構理論展開探討。建構主義強調人和情境的動態交互塑造,學習的過程并非事先安排好,而是學習能動者在行動中不斷建構、探索和重構的過程。從此立場出發,Borko &Putnam(1996)認為教師的學習是主動建構的過程,伴隨著知識不斷演化發展,受到個人已有的知識和信念的影響,并深深根植于特定情境中。區別于早先研究將主要關注點放在個體教師身上,新近展開教師學習的研究者們認為教師的同事合作社群(或稱實踐社群)為促進教師持續學習提供較好支持。在實踐社群情境中,學習是教師投入到集體活動中,圍繞共同愿景對分享性材料展開意義協商和探索的過程。
實踐社群首先支持教師通過相互分享、交換和解釋,將存在于實踐中的知識澄清出來。這種知識與好的教學實踐(good practice)相符,包括學科知識如何表征、教學策略如何選擇、教學情境如何理解等。這類知識有細節化、具體化、情境化等特點,并與特定的實際問題綁定在一起,是教師需具備的實踐中知識(knowledge-in-practice)。
但參與實踐社群的學習不局限于認識具體實踐或分享經驗,教師還可將課堂和學校視為研究場域和對象有目的地進行探索,“生產”出適用于自身及學校本土情境的知識系統。這類知識系統是教師基于學習社群,將自身實踐公開化于社群中接受討論、批評、證實,不斷改進、豐富和創生的實踐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其間,實踐社群是否以探究(inquiry)為導向,社群中教師是否能夠將教學實踐公開化轉化、編碼和擴散,社群的持續互動是否支持教師們不斷批判、反思并改進其實踐,皆是教師學習是否能創生實踐知識的關鍵。[1]換句話說,參與實踐社群學習一方面是教師建構實踐中知識的途徑;另一方面為他們審視自身實踐,展開合作探究,創生實踐知識提供可能。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研究者于2013年5月至12月間深入上海市兩所初中②(Y、H校)教研組(備課組)開展研究,數據包括校本教研活動觀察記錄,教師深入訪談,田野日記及相關文本資料。借助質性分析軟件Nvivo-8,依主軸編碼策略將訪談錄音、觀察筆記、田野日記等原始資料打散編入不同類目中,在此基礎上情境分析策略試圖發掘隱藏在資料間的關聯及意義。第八次課改后科學課首度出現在初中課程大綱中。作為一門綜合性較強的課程,科學課以學生自主探究建構知識為目標,涉及生物、物理和化學等知識點及大量實驗活動。本文選取兩校科學教研組(備課組)數據來呈現教師校本教研學習的過程及成效(表1)。③

表1 Y、H兩校科學教研組(備課組)教師基本情況
三、研究發現
2004年,Y、H校開展科學課教學。面對改革,兩校教師都基于各自教研組(備課組)對如何開展教學展開探討。
(一)Y校科學備課組及其校本教研:獲取實踐中的知識
Y校科學備課組有五位教師,隸屬理科教研組(包含化學、物理、生物和科學等教師)。在科學備課組,教師們集體學習的方式主要是集體備課和公開課,以教材為核心,就課堂教學的內容、設計、方法及問題進行討論。④
借助集體備課,Y校科學備課組教師們經常分享各自對教材內容的認識。如W老師所言:集體備課中組里老師通常互相幫助,如某個專業背景的教師負責課程相關章節備課與課件準備,分享給其他教師(W老師)。備課中教師也對教材存在的爭議性問題展開探討。S老師回憶某次集體備課的討論:落葉是不是生產者?(教材中)生態系統講到綠色植物屬于生產者,有老師認為不是,因為落下來就死掉了。但有老師提出來:若這個樹葉是風吹落呢?雖然最后組內沒有肯定結論,很多科學問題也有爭議,但通過討論,課堂上講到這個問題(教師們)就比較清楚(S老師)。可見,他們以教材為依據,通過集體分享和相互討論有效抵御來自變革對教師教學工作的沖擊。
校本教研活動還支持教師對課堂教學設計展開意義協商。集體備課中,教師們討論集中于課堂教學:備課通常很詳細,涉及上課上什么、怎么上、實驗如何安排、設置什么問題;此外也根據不同年級、班級學生程度適當擴充或精簡一些內容(S老師)。如S老師補充的,同年級教學,不能講太深,也不能講太淺,深淺快慢怎么把握,互相之間要商討(S老師)。相比較下,公開課對課堂教學的討論主要圍繞教學設計及實踐效果展開,如U老師所述:借助磨課,組內老師每次都就我的教學設計,如課堂導入怎么安排、提問怎么設置等提出意見,還請相關學科背景(如:物理)的老師從學科的角度指出哪里怎么說更專業等(U老師)。
通過參與教研活動,Y校教師逐漸達成科學課教學的共識,他們認為,初中段科學課目的是向學生啟蒙和普及科學常識,借此增進對科學問題的興趣(S老師,U老師)。基于此,教師圍繞教材和課堂教學設計,借助集體備課和公開課活動走到一起,不斷對教材所承載的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及課堂教學策略進行協商,好的實踐經驗借助語言和公開化的教學行動為組內教師共享,教學所需的實踐中的知識為教師掌握。隨著科學課教學走過三四輪,教師們對教材越來越熟,可爭論的問題逐漸減少。
可見Y校科學教師透過校本教研活動學習獲取了適用于教學實踐的認識和技能。正如Cochran-Smith&Lytle(1999)所述,這些教學實踐中的知識體現在教師的行動及他們持續做決策的過程中。學習是獲得既有教學經驗的過程。但學者們同時指出,對現有經驗的學習需保有深思熟慮的態度,如若缺乏反思,現有經驗將停滯不前,失去生命力。[2]這是當前Y校科學教師逐漸感到透過教研活動學習于自身教學收獲式微之原因所在。
(二)H校科學備課組及其校本教研:從實踐中的知識走向實踐知識創生
H校科學備課組有四位教師,教師們集體學習的活動形式包括集體備課、公開課、主題性教研活動及集體課題,以教材、課程標準、學科領域知識及學生作業等為分享性學習材料展開研討。
與Y校類似,H校教師借助集體備課對科學課程目標和教材內容展開討論:每周集體備課都要整理七年級三課時、六年級兩課時的內容,三維目標,重點難點等,具體到每節課怎么上、課堂環節怎么安排、實驗如何進行、課時進度如何安排等(Y老師)。
公開課(聽、評課)活動中,H校科學備課組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從不同角度對課堂教學設計提出各自看法。如T老師所述:沒有規定要先講酸雨形成原因,后講危害,再講防治。我也可以先講酸雨的危害,然后再引出酸雨的成因,學生一樣能懂,關鍵要能講通,這是我們經常討論的(T老師)。與Y校不同,H校教師對課堂教學設計的研討不單求同,更重存異。教師近年來持續將“同課異構”作為教學實踐討論的核心議題,逐漸形成自身教學實踐意義協商的視角。
此外,兩周一次的主題性教研活動讓教師對與科學相關的學科知識和學科教學知識進行協商。如組長Q老師所述:科學課本就具有學科綜合性,剛好組內老師的背景不同,利用優勢,結合大家共性問題,教研組內開展主題培訓,幫助蠻大(Q老師)。組內曾進行過“人體器官構造及位置”,“顯微鏡使用及教學”,“生態系統及其教學”等主題培訓。這樣的培訓不局限于教材內容,是對知識體系(如生態系統)來龍去脈的梳理。對此教師們解釋認為,相關學科知識及學科教學知識的學習不僅限于教材,而應分領域、成體系掌握、歸納和提煉(Q老師,L老師)。
集體備課、公開課和主題性教研活動支持教師針對課程知識及如何實施教學等議題展開討論,令他們掌握并內化適用于教學的實踐中的知識。但在H校,教研活動不僅限于形式上定期“碰頭”,組內開展的集體課題行動研究用另一種方式讓教師走到一起,就學生學習相關議題持續協商、開展探索。如L老師所述:科學課頭幾年,組內圍繞教學內容“年級適配(同一知識點在不同年級講到何種程度)”展開討論,如光合作用知識點在不同年級教學重點有異,預備年級講光合作用的場所、產物及原料;初一年級通過實驗檢驗光合作用;到初二年級,對光合作用的講解主要集中于葉片的功能……(L老師)
近年來,考慮到學生個性差異,組內又圍繞“分層學習”展開意義協商。教師認為,所謂“分層”應體現在學生作業及反饋機制上。圍繞給予適合學生個性的作業及評價,組內探索認為:有些作業是共性的,全體學生做;有些作業和科學小實驗有選擇性,個別學生感興趣可回家完成。但設想在實踐中發現問題:真正回家做實驗的學生較少。此后,我們又協商調整作業布置、反饋與評價的策略,并再在實踐中嘗試(T老師)。
組內教師集體課題行動研究超越教材本身,從H校學生學習特點和培養科學探究精神的角度深化教師對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及學生學習的認識。教師學習不單停留于內化操作性的教學實踐策略,而是圍繞相應議題,共同展開行動研究,形成自身對實踐理性化的體認與理解。如Q老師所言:認真做一個課題老師們就會思考,將原來零散的思路加以總結、歸納和提煉(Q老師)。這一過程令教師生產適用于自身教學的實踐知識成為可能。
目前在H校,“以學生為主、以科學探究活動為主”成為科學教師持續研討教學達成的集體共識。科學組教師透過校本教研活動進行意義協商和批判性思考的議題不僅涉及科學及其教學、科學之于學生的意義,還擴大到對課程改革及實施,與科學相關的社會性議題的探討,如T老師所言:我現在經常與學生們討論實驗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不成功。學生也該理解實驗并不是每次都成功,就像科學家們做多次重復實驗一樣(T老師)。Y老師認為:眼下科技和社會變化很快,科學課依舊是一門新課程,如何理解這門課程,如何開展科學課教學還需不斷探索(Y老師)。
在H校,教師的學習不單獲取適用于教學實踐的認識和技能,還透過探究性的校本教研活動,如集體課題行動研究,通過行動不斷反思、重構和理性化對自身工作的認識。如 Cochran-Smith&Lytle(1999)所提示的,在實踐社群中,探究性的學習活動很大程度上令教師的學習從獲取實踐中的知識到建構自身實踐知識進行拓展,并將他們對工作的認識同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等事務聯系起來。[3]
(三)教師實踐知識建構和創生的可能性
面對變革的新要求,Y、H兩校教師都將教材作為主要學習材料,透過集體備課和公開課活動,針對每節課上什么、如何上,及實際課堂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兩校校本教研活動為教師學習應對變革,建構實踐中的知識提供支持(表2)。

表2 Y、H兩校科學教研組(備課組)教師學習情況
但就過程分析,兩校教師參與校本教研的學習經驗和知識建構顯出差異。其中,H校教師透過校本教研活動所展現出的學習經驗體現出向實踐知識建構拓展的可能性。
具體來看,實踐知識建構是否可能首先有賴于教師相互投入的教研學習活動形式。除了集體備課和公開課活動,相較Y校,H校教師就教學的共性問題進行分享和討論;同時,集體課題行動研究讓教師以問題為出發點在行動中反思、歸納并提煉出適用于自身實踐情境的理性認識。正如Cochran-Smith&Lytle(1999)指出,探究導向的學習活動很大程度上為教師獲得新的學習經驗、建構自身實踐知識創造條件。[4]
其次,實踐知識建構的可能性還受到分享性學習材料的影響。區別于Y校教師主要將教材作為學習材料,在H校,支持教師透過校本教研意義協商的材料包括教材、課程標準、學科領域知識及學生作業等。多元分享性材料為教師提供不同的學習環境,更為豐富的話語系統和活動目標,使其學習內容不再局限于現有教材,而從不同角度激發和拓寬實踐社群中教師學習的程度。
除多元的學習活動和材料,教師學習在何種程度上走向實踐知識建構還關乎集體意義協商達成的對教學的基本共識。[5]將科學課視作“向學生普及科學知識”的共識透露出Y校教師偏向工具理性的教學認識,他們將學習視為獲取知識的過程,這種認識也反映在教師自身學習過程中。對Y校教師來說,掌握教材內容及課程知識是實施科學課的關鍵,校本教研的過程與成效亦在幫助教師掌握和內化教學所需的實踐中的知識。相比之下,H校教師透過意義協商,從批判建構視角認為科學是“以學生學習為主,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課程。教師學習并不限于現有教材知識,更從知識領域本身及學生學習的角度開展持續探索。校本教研活動成為教師探索的平臺,使其逐漸轉化、生成并建構關于如何理解科學課、如何開展教學及如何評價學生學習等議題的獨特認識。從這個意義上,H校教師對科學課教學達成批判建構的共識令其獲得更豐富的學習經驗,為實踐知識建構提供支持。[6]
四、討論與建議
通過對上海市兩所初中教師校本教研實踐分析可見,課程改革深化階段教師透過校本教研的學習和知識建構呈現出差異。與已有研究和理論呼應,校本教研為支持教師相互投入和意義協商提供平臺,一方面令教師掌握業已存在、適用于實踐的知識系統;另一方面為教師持續意義協商,轉化、生成自身實踐知識提供支持。其間,教師參與校本教研活動是否以探究為導向,教研活動是否形式多元,學習資源是否豐富,集體協商是否達成建構主義的教學共識等都影響實踐知識建構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參與教研活動,意義協商達成對科學課教學的共識反映出不同社群中教師對學科、教學、知識、學習及學生等的認識基礎,具備生成性。它通過教師不斷互動達成并延續,是對改革意念和要求的本土詮釋。教師們透過校本教研進行協商既可以探究為導向,將探究的意念滲透于教師們討論話語、互動規范和實踐探索中達成默契,也可能局限教師對于教與學的認識。這反映出校本教研作為實踐社群具有的兩面性:實踐社群為教師開啟某方面學習機會的同時也可能限制和關閉另一方面的學習機會。[7]簡言之,教師參與校本教研學習活動的成效不斷受到社群長期互動形成的群體文化觀念的牽制。
為持續推進并改進校本教研以促進教師學習轉變,首先應從探究的角度引領教師的校本學習,或與校外專家展開邊界跨越的合作與對話,對提升其學習成效尤為有益。其次,活化教師校本教研活動形式和目標,探尋多種活動形式及目標之間的連接點和相互關系,避免學習活動流于形式和疏于實質尤為重要。再次,要為教師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使校本學習不止于教材教案,還包含學生學情分析、作業反饋、教育理念情境化轉化等,這將對教師學習及其實踐知識的建構有所惠及。由于不同社群情境各自的傳統與規范影響教師對自主與合作、維穩和創新、異己之聲甚或探索性意見的接納度,因此開放的教研文化對于教師立足教學實踐開展學習和探索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注釋:
①胡惠閔(2005)指出,改革情境下校本教研無論目標、內容和方式上都提出同原有教研組不同的實踐思路,體現出向專業學習社群(PLC)靠攏的發展目標,包括注重實踐反思、關注教學研究、重在理念更新和文化再造等。
②有別于小學及高中,當前我國初中階段學校教育面臨外部考試壓力(中考)、學生學習差異及學生身心發展等復雜問題,教師更需要校本教研給予其專業上的支持。
③第八次課程改革過程中,科學作為全新的課程出現在初中課程和教學大綱要求中,這就要求開展這些課程教學的教師們加緊學習,以適應變革要求。
④在Y校,教研組活動主要以布置學校計劃和任務為主,深入細致地對科學課教學展開研習主要基于備課組進行。
[1]胡惠閔.教師專業發展背景下的學校教研組[J].全球教育展望,2005,(7).
[2][3][4][6]Cochran-Smith, Marilyn,& Lytle, Susan L.Relationship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Teacher learning in communities.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1999,(24):249-305.
[5]Westheimer,Joel.Communities and consequences:An inquiry into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teachers’professional work.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99,35(1),71-105.
[7]Little, J.W.Inside teacher community:Representations of classroom practice.Th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2003,105(6),913-945.
(責任編輯:劉君玲)
*本文系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組織學習視角下的校本教師學習研究(15YJC880135)”階段性成果之一。
張曉蕾/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教師學習與專業發展、教育政策與課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