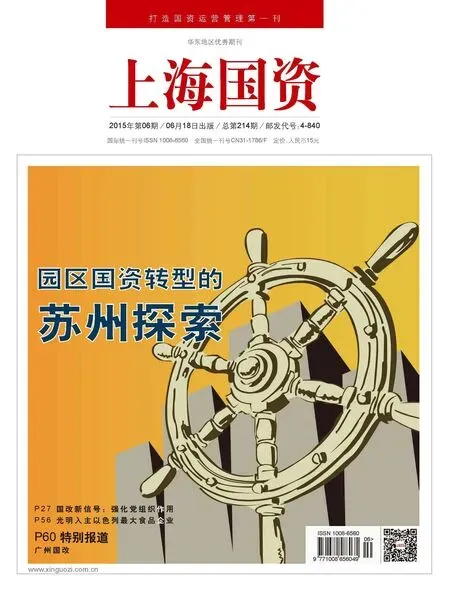園區國企的20年
文‖上海國資記者 王錚
園區國企的20年
國資辦的部署是,在解包還原基礎上,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園區開發類企業盡快“走出去”。
文‖上海國資記者 王錚
“園區的開發模式與國有企業的運作模式,看似兩個不同的范疇,但在蘇州工業開發區,兩者是深度融合在一起的,這既締造了蘇州園區的成功,也為今日國企的轉型提出了挑戰。”蘇州工業園區國資辦主任沈磊在接受《上海國資》采訪時做了這樣一個開場白。
蘇州工業園區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其為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的旗艦合作項目,也是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
從開發至今,蘇州工業園區已走過21年歷史,所獲成就固然顯赫。但時至今日,當開發建設任務基本完成,一路伴隨園區成長,并發揮著不容替代作用的國資國企正處于轉型的當口。
希望和彷徨,膠著與前行相互交織,破繭而出當需要極大的勇氣。
從“解包還原”推進政企分開到推動企業走出去倒逼企業市場化;從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資產流動性到推行市場化考核激發企業活力,蘇州工業園區的國資轉型升級的大幕正在徐徐展開。
據《上海國資》了解,因蘇州工業園區的先天條件與大多數開發區并不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園區開發類國企轉型的基礎和高度。
不一樣的起點
1994年2月,園區經國務院批準設立,同年5月實施啟動,目前行政區劃面積27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區80平方公里,下轄四個街道,常住人口約78.1萬。
“工業園區的開發,一開始即借鑒新加坡市場化的模式。地方財政沒有在開發公司投入資金。”沈磊介紹。
現在看來,這種開發方式顯得極為另類。
當時,為推進雙方合作,開發園區的頂層是由兩國副總理出任雙方主席的中新聯合協調理事會,負責確定借鑒新加坡經驗工作的目標和范疇,協調解決借鑒新加坡經驗過程中的重大問題。
具體的開發建設則是由中新雙方成立合資公司進行,這家公司即現在的中新集團。該集團在2001年之前,注冊資本1億美元,由新方控股65%,中方控股35%。中方財團由江蘇省屬國企、蘇州市屬國企以及一些央企出資。中新集團設立董事會決策機制。
其與政府的分工是,蘇州市政府負責中新開發區的土地征地拆遷,合資公司則負責土地“九通一平”和招商。
“按照當時的土地制度安排,政府鼓勵整體批租,成片開發。因此政府是將土地成片出讓給合資公司。合資公司以現金方式受讓土地,再將土地分割轉讓。”沈磊介紹。他當時即在中新集團任職,亦是園區招聘的第一批公務人員。
事實上,新加坡投資方極為謹慎。與通常所見的開發類企業不同,中新集團設立有地理信息部,從事土地規劃。
“中新集團信奉最大程度節省成本,他們會考慮凈地率,即除去道路、橋梁、醫院、政府部門用地外,可以出售或出租的商業用地。中新集團準備有未來5年的財務模型,將所有開發成本都能歸結到單位成本,即每平方米多少美金,相當細致。”沈磊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好處是中新集團與政府的關系非常清晰,但弊端是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
“因為以現金方式成片受讓土地,再進行分割轉讓,盈利期變得漫長。新方股東認為這樣的開發模式讓自身承擔的風險較大。”沈磊介紹。
經過談判,雙方達成一致,自2001年起中新公司中方控股65%,新方持股35%,園區開發主導權交由中方。
自此開始,蘇州工業園區開啟了新一輪開發模式,開發類國企紛紛成立并迅速成為主力軍,開發進度和效率大大提升,在這一點上,其與目前已遍地開發的同類園區企業并無多大不同。
但可貴的是,中新集團運作6年的開發模式與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理念已深入人心,市場化基因亦已深駐園區。此后,國企雖承擔開發重任,身負政府指令,亦存政企不分諸多弊病,但企業已認可,此種模式不可持續,各有轉型準備。同時,園區政府亦著意創造條件,敦促國企盡早轉型。
公用基礎設施PPP
2001年之后,雖然中方開始主導園區開發,開發類國企于此時紛紛成立。但這些企業大多負責地面建筑。
對于公用事業基礎設施,如水、電、氣、熱等源廠和地下管網建設,園區政府則仍采用市場化方式購買服務。
這有其背景。
“園區開發建設充分借鑒了新加坡城市規劃建設的經驗,綜合考慮蘇州古城水鄉特色與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其特點是:實現‘兩先兩后’即先規劃后建設,先地下后地上的科學建設程序。”蘇州工業園區在其20周年開發建設藍皮書中表示。
因為在中新合作區,其時由政府與中新集團合作完成了公用事業源廠和地下管網建設,而其他開發區域屬于5個鄉鎮(后改為4個街道辦事處),基礎設施落后。園區政府希望其他區域應與中新開發區一體化建設。
既然決定實施一體化,采用的建設模式亦相同,由政府購買專業公司服務。
2003年至2010年,園區政府完成了區內公用事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自來水、污水處理、燃氣、發電、集中供熱、供冷、污泥處置源廠及其管網等,均交由專業公司投資建設和運營,政府與這些公司簽訂特許經營協議,明確公共服務責權利。
比如,水務基礎設施由園區清源華衍水務有限公司負責投資運營,該公司成立于2005年,承擔蘇州工業園區行政區域內自來水、污水廠及其管網建設和運行管理。
“水務公司由香港上市公司中華煤氣持股50%,另外50%是中新集團下屬中新公用持有,中新公用是中新集團下屬公用事業板塊集團企業,中新集團持股50%,園區國資企業國控公司和兆潤控股共計持股50%。”蘇州工業園區國資辦副調研員華亮介紹。
園區政府與這家水務公司簽訂特許經營協議,賦予其一定期限內園區水務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權。中新公用受政府委托,建立面向社會公眾的24小時公用事業便民服務熱線,對公用事業專業企業的服務質量進行第三方監督。
雙方關鍵的協議指標是,對于公用事業,價格由政府管制,企業提價必須經過工業園區物價部門批準。此外,公用事業必須與政府開發建設同步。“道路修建到哪里,地下管網必須同步建設。”華亮介紹。
水務公司設立有董事會,股東雙方各派4人,另有4名由政府指定代表公眾利益的特別董事,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決策,但對于公司有可能影響公眾利益的重大事項擁有一票否決權。
設計頗為詳盡。
水務公司目前累計投資60億元—70億元,盈利還處于爬坡期。
“因為投資的基礎設施都是重資產,一旦折舊收回,水務公司就將進入盈利高增長期。”相關人士解釋。
工業園區對于燃氣管道建設亦采用如此方式。蘇州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由香港中華煤氣與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市政公用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投資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中華煤氣占合資公司55%股權,中方占45%股權,注冊資本為人民幣2億元,以特許經營模式負責園區范圍內的燃氣公用事業。
契約制亦讓政府嘗到甜頭。
“我們園區規劃建設局公用事業處只有3個人,卻負責了100多萬人口的園區所有自來水、污水、燃氣、發電、供熱、供冷、污泥處置等公用事業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務,非常高效。因為對于政府來說,這些特許經營的公司即能承擔日常運營管理和為公眾提供一流服務的職責。”華亮介紹。
與公用事業源廠及地下管網建設比較,從事地面開發的國有企業并沒這么輕松。
國企主力軍
“中方控股之后,園區行政權和開發權合二為一。”沈磊表示。2001年,最先成立的全資國有企業是蘇州工業園區地產經營管理公司,目前更名為兆潤控股,承擔新一輪土地開發任務。
“地產公司與各地的城投并沒什么兩樣,主要是依靠融資進行土地一級開發和儲備土地。當時國家開發銀行給我們極的支持,迄今累計貸款200余億元,因為園區規劃較好,前期引進項目優質。”沈磊介紹。
其后,園區相繼成立了八大公司,大多從事土地開發或房地產建設。比如從事土地開發的地產經營公司、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建屋集團、從事商業地產的圓融集團、從事社區商業的鄰里中心、從事舊城改造的重建公司、從事文化場館建設的文博中心等。不過,仍可見其講究分行業和領域設立企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諸多房地產開發類企業外,園區還成立了一家創投企業,即現在的元禾控股。“當時招商客戶以外資為主,而且我們在規劃中要建設科教園區,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支持,所以,園區管委會決定提前布局,設立創投企業,這是得風氣之先。”沈磊解釋。
這種開局,當時并不顯眼,但為后期國企市場化轉型鋪就了道路。
“園區開發就此進入一個新的高潮,可以用萬馬奔騰形容。”沈磊表示。形成開發高峰,當然與國企全力執行政府指令高度相關。
據了解,園區的開發模式是:統一規劃、成片開發、國資持有經營。
“為什么要國資企業持有經營?因為要控制形態,完成園區功能,提升園區品質。比如獨墅湖,是要打造高品質的科教園區,比如,園區還要求建設有很多精品工程和樣品工程。而社會資本不會完全按照規劃和形態建設,政府無法把控。”沈磊介紹。
建造一座新城,成敗來自于兩個地方,一,是否有產業支撐,二,城市形態是否完善。
應該說,全面擔負著園區開發建設任務的國有企業,在蘇州工業園區的歷史上占據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業內認為,蘇州工業園區是“從無到有”的經典范例,其中國企所做獨特貢獻功不可沒。
以獨墅湖科教創新區開發為例。該區域在2002年開發建設,定位于科技、教育、創新、人才4個概念,區域總規劃面積約25平方公里,規劃總人口40萬人。經過三期開發,已經實現規劃目標,吸引了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等26所高校進駐,這些高校在獨墅湖區域均設立有研究生院,另外,還有8所國外大學,2000多家科技企業在此落戶。
“政府出資成立的國企,承擔了這個區域所有的土地招標、開發招商,可以說是為了打造精品,不計成本,如果不是國企,獨墅湖區域不會10年后成為一個新城區,起點也不會那么高。”獨墅湖科教創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沈麗娟對《上海國資》表示。
所謂“不計成本”, 沈麗娟舉了一個硬件設施的例子。
蘇州納米城二期在2014年正式投用,5.6萬平米的江蘇省(蘇州)納米產業技術研究院項目竣工投用,該項目從設計到建成歷時3年,包含具有國際水準的專業MEMS超凈實驗室設計,可實現6英寸、8英寸MEMS工藝線同時兼容。
“高標準的硬件投資,但租金只有市場價的一半或者1/3,公共的展廳則無償提供給企業使用。”沈麗娟介紹。
但這成為了園區吸引企業入駐的成功要素之一。
她介紹,獨墅湖區域剛開發時,全部都是農田,沒有企業愿意進來開發。“當時是建屋集團、地產公司等率先拿地開發。”
為引進高校,工業園區管委會特成立教育投資公司,從事建設、投資、招校、引研工作。
“教投公司建造高規格教學大樓、人才公寓、使用各種優惠政策,比如2年減免1000平方米的房租,補貼3年學校的辦公日常運營經費,稅金減免等,甚至要幫助高校外出招生或者協同解決老師的職稱、編制等待遇問題。”沈麗娟介紹。這些費用單就對一所高校,每年的支出大約就是幾百萬元。
第一家落戶的是中科院納米研究所。“當時引進來時,路還沒修通,我們帶中科院只能遙遙指了現在的地塊。”沈麗娟介紹。
現在,中科院大約有700—800人生活在這個區域。此外,中科院電子所亦將落地。
除了在本地服務外,國企還會主動與政府部門外出招商,并與教育部及各地高校溝通協商,希望能夠將科研團隊引進到園區。
第一所中外合作學校落地園區時,政府部門和國企幫助學校進行全國推廣招生。
其后,國家政策鼓勵“科教結合”,工業園區又為此特別設立了3家科技公司:科技發展公司、納米公司和生物醫藥公司,在獨墅湖區域建設孵化器,引進科技類企業。
因為先期引進了高校研究院所,這樣,引進科技類企業變得相對容易。目前,中科大、華為和微軟均在此設立有軟件園區。
伴隨著蘇州工業園區的日漸成熟,在開發建設運營中執行政府指令并發揮巨大作用的的國企,既積淀了大量資產,同時也面臨著資產負債率過高、資本回報偏低的挑戰。
轉型是惟一選擇。
改變與回歸
“雖然背負債務不低,但園區的國企持有大量優質的物業和資產,由于早期投資成本低,現在的估值則相當高,因此轉型有良好的基礎。”沈磊介紹。
他認為,這一點不象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他們經營的主業即融資,資產即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客戶只是政府一家。而蘇州工業園區的國資企業投資形成了自己各具形態的資產。比如“科教園區”的寫字樓、“鄰里中心”的商業資產、開發的周邊公寓和住宅等。
此外,開發類企業所持資產證件齊全、產權清晰。土地經過招拍掛取得,因此有房地產證和土地證。“大多數地市級政府以下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主要是基礎設施,沒有現金流,多為財政買單。但我們園區國有企業形成的資產,三分之一是財政買單,三分之二是市場買單。”沈磊介紹。
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園區國資辦一方面促使國企保增長,一方面積極推動國企走向市場,考核企業盈利目標。“園區國有企業,作為功能開發類企業,既要為政府服務,但也要樹立市場規則,培養市場競爭力。”
“十二五”期間,管委會將旗下國有企業進行系統性改變。
首先將企業按業務屬性分類管理。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房地產企業新建元集團、從事金融股權投資的元禾控股和中新集團被定為特一級企業;以服從政府指令為主,從事載體開發和服務的企業定為一級企業,比如3家科技公司、文博中心等;兆潤控股與國控公司定位為投資控股公司,是所有一級公司和特一級公司的母公司。
“初步形成了國資辦——投資控股平臺——國有企業三級監督架構。”沈磊介紹。
園區管委會同時下設類似董事會構造的投資決策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審計委員會。“投資決策委員會主要是強化企業投資約束。對于非市場主導型企業,1000萬元以上投資項目需要得到批準;對于市場主導型企業,原則上投資并不需要審核,但如成立一級子公司,那么對行業分類和投資金額都要求審核,比如是否超過凈資產一定比例,或者資產負債率是否超過警戒線等。”
此外,薪酬委員會是在考核前提下核定薪酬。“對于市場化程度高的企業,主要考核凈資產收益率,未來還會引入EVA為主要考核指標;對于非市場化企業,則一企一策,強調可控成本硬約束。”沈磊介紹,希望達成的目標是,薪酬與效益同步增長。
此外,園區國資辦對企業對外借債、擔保管控甚嚴。這亦是其控制負債率的有效方法。
“我們只允許縱向擔保和借貸,不允許橫向發生類似往來。”沈磊介紹。所謂縱向,即母子公司可以互相擔保和借貸,但子公司之間或非同一母公司下的子公司均不可發生財務往來。
這樣能形成風險隔離帶。“任何一家企業發生財務危機,都不會殃及池魚。”沈磊表示。
為了幫助企業盡快確立獨立市場主體地位,園區國資辦從2014年開始推進一項“解包還原”工程。
所謂“解包還原”,即將20余家國企因執行政府指令形成的本息債務一一核實,園區財政對20余年形成的債務進行認可,分期買單,以減輕企業歷史負擔,并以此明確企業的市場考核標準。
“原來是政企不分的一筆糊涂賬,誰也說不清。通過‘解包還原’,我們希望幫助企業輕裝上陣,還原企業本質,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未來,會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建立契約合作關系。”沈磊解釋。
據了解,經國資辦和財政局聯合認定,園區財政大約應還國企本息數以百億計,分5年償還。
此舉頗令同業震懾。園區管委會推進國企市場化的決心之大、行動之迅速以及部門利益平衡之強均可見一斑。
國資辦的部署是,在解包還原基礎上,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園區開發類企業盡快“走出去”。
一出生即迥異于同類的蘇州工業園區和浸淫其中的國企,與生俱來的市場化基因正發揮強大作用,其轉型的探索,正在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