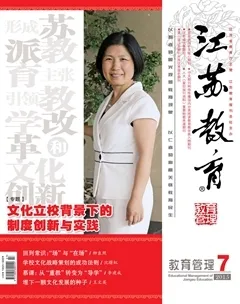曾參:孔門中精進修養且孝行突出的弟子

【摘 要】曾參是孔門私學中精進修養且孝行突出的弟子。孔子對曾參的教育體現了高超精湛的教育藝術:一是孔門問對——孔子對曾參的個別化教學藝術;二是“參來勿內”——孔子對曾參“愚孝”言行“以怒示警”的教學藝術;三是“三省吾身”——孔子指導曾參進行自我教育的藝術。此外,曾參為“以友輔仁”而建立的“同學圈”,也值得深入考述并認識其所特有的教育價值。
【關鍵詞】曾參;孔子;教學藝術;問對;反省;孝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7-0032-05
【作者簡介】李如密,南京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南京,210097)教授,教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教學論、教學藝術論的研究。
曾參是孔門私學中精進修養且孝行突出的弟子。他沒有顏回、子貢之“敏”,也沒有子游、子夏之“才”,但是他個性沉穩、專注做事、善于反省、身體力行,最終在道德學問上達到“慎獨”的境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人物。孔子對曾參的教育既有點化促悟,又有以怒示警;不但身教為先,而且引導自育。深入考察孔子與曾參的教育交往及教學藝術,對于今天教師做好教育教學工作多有裨益。
一、曾參的生活史、形象及成就
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今山東費縣)人。其父曾晳也是孔子的弟子。在孔門私學中,父子同為孔子弟子的,除了顏路和顏回之外,就是曾晳和曾參了。父子先后為孔子弟子,說明父輩對孔子教育的認可。子輩的成就超越了父輩,與得到了父輩的早期教育影響是分不開的。
曾參是孔子晚年弟子中年齡較小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參的少年時期,隨其父曾晳耕種于故里。《說苑·立節》載“曾子衣弊衣以耕”,自食其力。其早期教育,應為曾晳對其進行啟蒙,以后才入孔門學習。據考證,曾參入孔門時間應為孔子返魯之后的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時年曾參二十二歲。[1]《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以為能行孝道,故授之業。”說明曾參少時的孝行即得到孔子的關注。
曾參天資并不聰敏,甚至有些魯鈍。孔子曾說“參也魯”(《論語·先進》)。孔安國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史記解》引)。學者李啟謙認為,曾子就是一位性情沉靜動作較慢的人。他這樣的性格只是不太活潑,但不能說他腦子愚笨。[2]也就是說曾參之“魯”只是“不敏”而已,并非“不智”。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引用程頤等人的注釋:“曾子之學,誠篤而已。圣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北宋二程對曾子的“魯”做出了合理的評價,他們說:“參也魯。然顏子沒后,終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二程集·二先生語卷九》)正因為曾參“魯”,專心向學,心無旁騖,才能繼顏回之后,終得孔子之道。
曾參本人是典型的孝子。《孟子》的《離婁上》篇和《盡心上》篇載有曾參養曾晳必有酒肉、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的故事。《戰國策·燕策》載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新語·慎微》載“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于糜粥之間,行之于衽席之上”。《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載雖然后母“遇之無恩”,而曾參“仍供養不衰”。《禮記·內則》載曾參遭遇父喪時“淚如滴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后被元代郭居敬選入《二十四孝》,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孔子高度評價曾參:“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孔子家語·弟子行篇》)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曾參主要是一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論語·泰伯》)的謙謙君子形象。其實,這只是曾子思想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曾子卻又是弘毅、剛強、傲視王侯的“高士”、“斗士”,這一形象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如曾參成名后影響很大,“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為上卿”(《韓詩外傳》卷一),但曾參均力辭不就。
曾參作為儒家思想重要傳人,其弟子和再傳弟子眾多。據文獻所載,著名弟子有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子高、子襄、陽膚等。清代學者崔述曰:“圣道之顯,多由子貢;圣道之傳,多由曾子。子貢之功在當時,曾子之功在后世。”(《洙泗考信錄·余錄》)可謂公允之論。
曾參靜心修養,得享高壽。《史記》載:曾參“死于魯”。《闕里文獻考》載:“曾子年七十而卒。”張其昀著《孔學今義》稱:“曾子壽至九十。”但均不知何據。
二、孔門問對——孔子對曾參的個別化教學藝術
孔子擅長與弟子進行問答對話,是對話教學藝術大師。在孔門私學中,與孔子直接進行問對,是弟子們接受孔子教育的重要形式。孔子對曾參個別化教學的典型案例就有如下幾樁:
1.“一以貫之”:孔子對曾參的“點化促悟”教學藝術。
《論語·里仁》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孔子說:“曾參啊,我的道是可以用‘一’貫穿起來的。”曾參說:“是。”孔子出去后,其他弟子問曾參:“是什么意思啊?”曾參說:“老師的道,只是忠恕而已。”
此處所記反映的情形,應為曾參在孔門學習已有時日才發生的。從文中可知,當時在場的弟子并不止曾參一人,而孔子獨獨叫著曾參的名字說“吾道一以貫之”,可以見出孔子對曾參的器重。而曾參也心領神會地回答“是”。孔安國注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孔子沒有明說“一以貫之”的“一”是什么,曾參似乎非常清楚老師的這個“一”就是什么,而從孔子隨后沒有說什么就離開了,好像對曾參如此回答是默默認可的。觀之《論語》及其他史籍,發現能夠和孔子如此對話的弟子僅此一例。
那么這個“一”到底是什么呢?當時在場的其他弟子都不解其意,只好問曾參:“是什么意思啊?”曾參向他們解釋說:“老師的道,只是忠恕而已。”從曾參的語氣來看,是言之鑿鑿的。這些其他弟子應是和曾參一起學習的同門弟子,他們對于孔子的一貫之道顯然沒有曾參那樣深刻的領悟,這也說明孔子只將這一問題問曾參,是對弟子的學習狀況了然于胸的。
孔子對于曾參一個“唯”字的回答應該是感到欣慰的。因為據《論語·衛靈公》載,子貢也曾聆聽孔子講述“一以貫之”之道: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知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從子貢回答時的不得要領看,孔子對此是不滿意的,甚至有點失望。他先是明確否定了子貢的回答是“非也”,進而直接告訴子貢說“予一以貫之”。此后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子貢終于向孔子問道:“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對于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參是自己悟出的,而子貢則是老師告知的。
2.“聞諸夫子”:孔子對曾參的“孝行評價”教學藝術。
《論語·子張》有兩章記載了曾參向弟子轉述自己親聞孔子教誨的情況:
其一是: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其二是: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從文字記述形式來看,此兩章“曾子曰”,透露出較為特殊的信息。一是尊稱曾參為“曾子”。由此可推知,這很有可能是由曾參弟子記述的。二是曾參特別表明自己所言為“吾聞諸夫子”。其語言形式有點像佛經中的“如是我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確曾對曾參進行過這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曾參對老師教誨的尊崇。
從曾參轉述孔子的教誨內容來看,都與“孝”行評價有關。前一章孔子教育曾參說:“人的感情在平時是不會自動發揮到極致的,如果有,那應該是其父母去世的時候吧。”《論語集解》引馬融注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他事,至于親喪,必自致盡。”這也是告誡人們必須竭誠盡哀于親喪,以表孝心。后一章孔子教育曾參說:“孟莊子的孝,其他的都容易做到,而留用他父親的家臣,不改變他父親的施政綱領,這是別人難以做到的。”這和孔子對孝道的一貫主張相吻合,《論語·學而》即載有他曾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子一再對曾參進行孝道教育,受此影響,曾參終于成長為以孝見長的儒學思想家。
3.詢問“七教”:孔子對曾參的“由孝而政”教學藝術。
《禮記·王言》載:曾子曰:“敬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大意是說:曾參向孔子請教說:請問“七教”說的是什么?孔子就向曾參解釋道:執政者尊敬老人,而老百姓越孝敬父母;執政者按年齡大小封爵,而老百姓越順從兄長;執政者喜愛施舍,而老百姓越信實;執政者親近有才能的人,而老百姓越慎重選擇朋友;執政者樂于給人恩惠,而老百姓就光明正大;執政者討厭貪饞,而老百姓就以爭奪為恥辱;執政者剛強果敢,而老百姓就廉潔知恥;老百姓都分別有了榜樣,政務就減輕了。這就叫“七教”。七種教化,是治國治民的根本,教化穩定,社會習尚就端正了。執政的人,乃是老百姓的榜樣,只要榜樣端正而什么事物還會不端正。
從孔子對曾參所提問題的回答看,孔子認為執政者的德行對于老百姓的影響是直接的,因為在他看來,“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其德政就是從“上敬老”、“下益孝”開始的,而將其中的道理推而廣之,即可使“民皆有別,則政不勞矣”。指出所謂“七教”,是“治民之本也”,而“教定則正矣”。孔子對曾參的詢問,答以“由孝而政”的道理,體現的正是他一貫的“循循然善誘人”的教學藝術風格。
三、“參來勿內”——孔子對曾參“愚孝”言行“以怒示警”的教學藝術
據《孔子家語》《韓詩外傳》等文獻記載,曾晳教子極為嚴厲苛刻: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于曾晳曰:“向也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大意是:曾參耘瓜誤斷其根,曾點大怒,以大棒將兒子打昏。曾參并沒有記恨,醒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安慰父親。之后回到房內彈琴唱歌,以便讓父親知道自己身體沒有問題。曾晳教子的故事,應該是中國人“棍棒下面出孝子”這一古訓的淵源。
然而,孔子對此并不贊同,尤其是對曾參的“愚孝”言行。據載: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于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大意是說:孔子聽說了這些情況就大怒,告訴弟子們說:“如果曾參來了,不要讓他進門。”曾參自認為無罪,托人向孔子請教。孔子對來人說:“你沒聽說過嗎?昔日舜侍奉父親,父親使喚他,他總在父親身邊;父親要殺他,卻找不到他。父親輕輕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親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親沒有背上不義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沒有失去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參侍奉父親,把身體交給暴怒的父親,父親要打死他,他也不回避。他如果真的死了就會陷父于不義,相比之下,哪個更為不孝?另外,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嗎?殺了天子的臣民,又會犯多大的罪?”曾參聽后,說:“我的罪過很大呀!”于是造訪孔子而向他謝罪。
由上可見,對于曾參來說,父親曾晳之“怒”,是怒其干活不細;老師孔子之“怒”,是怒其孝行過愚。父親曾晳的教育是“棒打”,老師孔子的教育是“勿內”。棒打是身體懲罰,輕則傷其皮肉,重則危及性命;“勿內”是精神懲罰,重在觸其靈魂,激起警覺。只是“參來勿內”的教育效力還不足夠,這由“曾子自以為無罪”可以知道,孔子就再以長篇言教轉告,舉“舜事其父”為例,對照分析,循循善誘,終于使曾參意識到自己“罪大矣”,從而心服口服地上門“謝過”。或許正是這一次“勿內”教育的契機,才使曾參幡然醒悟,知道了凡事皆需要反思,在“孝”道上精進修養,終有成就。
四、“三省吾身”——孔子指導曾參進行自我教育的藝術
儒家的修養理論強調向內用力,要求做到克己內省。孔子就要求其弟子在修養過程中嚴格要求自己,“克己復禮”(《論語·顏淵》),以提高個人修養水平為重,不為外部名利所誘。[3]孔子本人即是自我教育的典范,對弟子們形成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作為孔門弟子的曾參,之所以學問和修養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憑借他“內省”和“慎獨”的自我教育功夫。
關于內省,曾參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同朋友往來是否誠實?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復習了?曾參的思維靈活性不夠,但深刻性突出。所以他非常專注,思維很有深度。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關于“慎獨”,曾參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大學》)大意是當獨處而無人覺察時,要像有許多眼睛在盯著你,許多人的手在指著你的時候那樣,謹慎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曾子認為“慎獨”首先要求“誠意”,要誠實無偽,真心無欺,要言行內外一致,在一切場合中都自覺地踐履道德準則。
《荀子·法行》有載: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遠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這段話意思是說,曾參主張不要把家人看得疏遠,而把外人看得親近,不要本身不善,怨恨他人;不可刑法臨到自己,而呼叫上天。把家人看得疏遠,而把外人看得親近,不也違反常理了嗎?本身不善,怨恨他人,不也悔之已晚了嗎?古詩說:“細流的水源,不填就不會蔽塞,車轂已破碎了,這才加大它的輻條;事情已經失敗了,這才高聲長嘆。”這還有什么補救呢?這些認識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作為孔門弟子的曾參親疏有度、嚴于律己、防微杜漸、注重自我修養的思想。
曾參一生言行謹慎,哪怕是病中、甚至臨終時刻都無絲毫懈怠。《論語·泰伯》載: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參的身份是“士”,但其寢眠之具,卻是士大夫才能享用的華麗竹席。彌留之際,當童子指出這一點后,曾參當即要求兒子換掉竹席。曾參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堅持換席,為其一生恪守“禮不逾節”作了生動的詮釋,成為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典范。
五、“以友輔仁”——曾參與同門弟子的“同學圈”考述
曾參在孔門弟子中年紀較小,但因自己注重個人修養,并主張“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在眾多同門中威望較高,形成一個頗有影響的“同學圈”。對此加以深入考述,對于認識曾參及其思想也有特殊的價值,正所謂“觀其交往,可以知其為人”。
1.曾參與顏回。
顏回是孔子早期弟子,曾參是孔子晚年弟子。對于顏回這個先進學長,曾參是非常推崇的,曾作如此評價:“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我友嘗從事于斯矣。”這里曾參所說的“我友”即是指顏回。
2.曾參與子貢。
子貢比曾參大15歲,曾參是子貢的小師弟。曾參曾和子貢一起參加季孫之母的喪禮(宋蘇轍《古史·孔子弟子列傳·曾參》)。曾參雖然年輕,但子貢對他評價甚高。《孔子家語·弟子行》載,子貢曾這樣稱贊曾參:“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對于當時在孔門私學并不引人注目的后生曾參來說,這簡直就是“知己”之論了。
3.曾參與子夏。
曾參與子夏都是孔子晚年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比曾參大兩歲。清陳玉澎《卜子年譜》中云:“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4]一語概括了曾子和子夏的學術貢獻。《禮記·檀弓》記載這樣一件事: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曾參為人耿直,他誠懇指出同門子夏之罪,一是罪在不夠尊師,二是罪在不夠敬老,三是罪在過于愛子,這正是曾參孝道思想和內省精神的表現,也使子夏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同時幫助他走出了過度的喪子之痛。曾參憤言責善,子夏從善如流,非至交之友則不能也。
4.曾參與子張。
子張比曾參小兩歲,先曾參去世,二人論道講學,互相切磋,曾參稱子張“難與并為仁”。曾參與子張確實性格氣質不同,思想有較大差異,但這并不妨害其同門之誼。王闿運《論語訓》中說:“曾、張友善如兄弟。”子張卒,最先通知的同輩中人就是曾參,《禮記·檀弓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二人親密關系可見一斑。
5.曾參與子游。
子游對禮有著濃厚的興趣,愿意鉆研也喜歡鉆研,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子游對禮往往有獨到的見解,對禮的具體儀節和內涵領悟較曾參準確,尤其是喪葬之禮,更較曾參熟悉。《禮記·檀弓上》載:小斂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就是說曾參與子游討論小斂之奠的方位,子游說安放在尸體的東面,曾參說安放在西面,而且要放在席子上面。魯末禮失,曾參見到當時所行,以為禮本來是如此,所以不知道錯誤。
6.曾參與有若。
《孟子·滕文公上》載: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意思是說:孔子死了以后,子夏、子張、子游認為有若跟孔子相貌近似,便想用過去敬事孔子的禮節來敬事他,還勉強曾參同意。曾參說:“不行!就像那用江漢的水沖洗過,用夏天的太陽暴曬過,光明潔白的無法比擬,誰能跟孔子相比呢!”《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有此事,記述如下: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可見,在這件事上,曾參的意見是明確而堅決的,并且被證明是對的。張其昀教授認為:“曾子不從,非惟其識見卓越,亦見其信道誠篤,執德弘毅,度越游夏諸賢,故能獨排眾議,著尊師之大節,此其所以為宗圣也。”[5]曾參在這件事上的篤定與堅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參考文獻】
[1]羅新慧.曾子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65
[2]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1987.136
[3]李如密.儒家教育理論及其現代價值[M].北京:中華書局,2011.159
[4][清]陳玉澎.卜子年譜·自序.叢書集成續編第36冊,上海書店,1994.581
[5]張其昀.孔學今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43
【基金項目】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孔子對其弟子的教學藝術及現代價值”(課題批準號為:DOA14020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