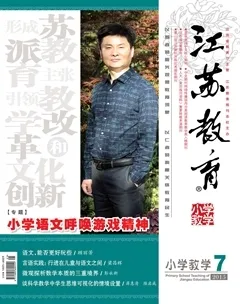“模糊”教學邊界 催生創造智慧


【關鍵詞】數學;邊界;智慧
【中圖分類號】G6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0063-02
《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2011年版)》指出:“創新意識的培養是現代數學教育的基本任務,應體現在數學教與學的過程之中。學生自己發現和提出問題是創新的基礎;獨立思考、學會思考是創新的核心。”在數學教學中,當我們嘗試“模糊”教與學的邊界,把師者切實轉變為數學學習活動的參與者、組織者、引導者,學生的主體性才可能建立,才可能點燃學生內在的創新思維的火花,數學教學也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其學科特有的育人價值。
在教學蘇教版四下《三位數乘兩位數》單元練習時,筆者利用兩位數乘兩位數的知識遷移,幫助學生認識和理解三位數乘兩位數的算理、算法,可沒想到一道思考題引發了“新舊知識間的思維沖突”。
用3、4、5、6、7五個數字組成三位數乘兩位數的算式:積最大的算式是□□□×□□=( ),積最小的算式是:□□□×□□=( )。
筆者在備課時根據“如何求兩位數乘兩位數積最大”的經驗,將最大數“7”“6”分別列在最高位,然后再列出十位和個位上的數字,比如:753×64=48192,743×65=48295,對比乘積及兩個乘數之間的差:753-64>743-65,753×64<743×65,發現與兩位數乘兩位數積最大的解答策略一樣。積最小的算式則相反,357-46>356-47,357×46<356×47,還真是“差越大,積越小”。于是筆者認為:把給定數字組合為三位數乘兩位數的算式時,積最大、積最小的策略與兩位數乘兩位數的組合策略相同。
課上筆者將這道題目作為“餐后甜品”出示在黑板上,并且讓學生列出各種積可能最大的算式,寫了足足10道:543×76,674×53,654×73,653×74,643×75,743×56,743×65,754×63,753×64,765×43。
在梳理的過程中,學生根據“7×6>7×5>6×5”確定“7和6”一定在兩個乘數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