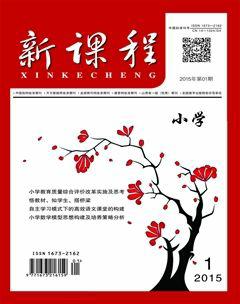感悟《落花生》
賀國強
上好一節課,說到底還是對文本的把握和研討的深度。文本選入的基本標準是文質兼美。“文”是指語言文字表達及構段構篇技巧,“質”是指思想內容、精神內核、價值取向。《落花生》一文就其“文”來講,語言質樸,簡練而生動,意蘊深刻,對話占據很大篇幅,對話的旁白皆在前面,而且極其簡單:“父親說,姐姐說,哥哥說,我說”,很接近孩子的表達方式。重點段落“議花生”一段,人物對話皆自成一段,可謂段落分明。“種花生、收花生”段為非重點段,敘寫匆匆,用短句子“買種,翻地,播種,澆水”等幾筆帶過。重點段把每個人的談話都記錄下來,寫得比較詳細,父親的談話又是重中之重,可謂詳略得當。《落花生》一文就其“質”來講,通過一家人過收獲節談論花生,借物喻人,講做人的深刻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父親在講這一道理時,用了對比的手法。既然講花生的樸實無華,默默奉獻,何必又要牽扯到桃子、石榴和蘋果呢?一位教師設計了這個環節,多好的提問啊!涉及對比手法的運用,涉及兩種人生觀。對比手法必然要突出一方,拿桃子、石榴、蘋果的“鮮紅嫩綠”與花生的“不能立刻分辨”比較,拿桃子、石榴、蘋果的“高高掛在枝頭”與花生的“矮矮地長在地上”比較,拿桃子、石榴、蘋果的“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與花生的“挖起來才知道”比較。顯然,父親積極倡導花生族的人生觀,而鄙夷桃子類的人生觀。引導學生體會這兩種人生觀至關重要,正是本文的價值取向。
一家人談論花生,姐弟們談了很多,為什么父親沒有完全認同?姐弟們的談論與父親的談論有什么不同嗎?我們著眼于花生的實用價值,而父親著眼于花生的精神內含,即花生的高貴品質,由花生的品質聯想到做人的道理,借談論花生教育子女,而且這樣的教育自然貼切,確實影響了子女們的人生,作者取名“落華生”不就是例證嗎?這也就是父親“實在很難得”參加家庭聚會的意義所在吧!既然父親談論花生的話最重要,啟迪引導了我們的人生,那么還有必要寫姐弟們的談話嗎?首先是姐弟們的談論激勵了父親的談話,其次是姐弟們的談論與父親的談論形成鮮明對比,再次是父親高瞻遠矚,一語道破花生的精髓,還有,父親技藝精湛,巧妙運用對比手法,撥云見日,讓我們明白做人的道理。
父親說“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這“一樣”究竟是什么?作者沒有概括出來,如果用一個詞概括花生的品格,怎么概括?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怎么概括呢?這樣的練習,可以進一步深化對花生品行的認識,對下一步正確理解“體面”和“只講體面”做好了鋪墊。
父親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這句話是教學的難點。這句話是父親在比較了兩種人生觀之后得出的結論。難就難在“只講體面”。難道桃子一類既講體面又為他人做貢獻不好嗎?難道花生不注重體面,只注重奉獻才是正確的人生觀嗎?因為父親身處仕宦之途,閱歷了那個年代達官貴人貪圖享樂、荼毒百姓之弊。所以,體面應該有所指,并不單單指衣著體面或者工作體面,更與講究禮儀無關。與上文父親的談話聯系起來理解,父親沒有講桃子、石榴、蘋果的一點好處,就是取其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碌碌無為之意。“只講體面”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極端享樂主義者,從不顧及他人疾苦,從未掛懷別人需求,不講奉獻,是對別人沒有用處的人。就應該像花生那樣,低調做人,踏實做事,把自己整個的聰明才智奉獻他人,奉獻社會。
怎樣做花生式的人呢?文中多處寫了母親。首段母親倡導在自家后園種花生。二段寫花生豐收了,母親倡導過收獲節,過節時,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食品,而且決定在后園的茅亭過節。以后幾段寫全家談論花生時,母親始終沒有插嘴,沒有參與談話。母親處處在背后為家庭做貢獻,張羅收獲節,母親做全家人的美食。在談論花生時,母親把話語權讓給父親,父親發表高論時,母親默默稱道,母親不就是時時為家人著想的“落花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