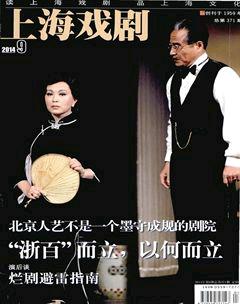越劇與“新越劇”
冷自如
浙百三十年,愛者如癡如醉,恨者咬牙切齒,痛者捶胸頓足。唇槍舌戰,針鋒相對,各執己見,褒貶不一。此間繞不過去的兩個問題:一是“新越劇”是不是越劇,二是越劇會不會變成“新越劇”。
其實茅威濤從來沒有掩飾過她做“中國式音樂劇”的野心。對于“新越劇”,只要我們還認為越劇屬于戲曲的范疇,那么“新越劇”的屬性其實不言自明。同為高度綜合的藝術形式,音樂劇和中國戲曲的確是有很多共通之處。音樂劇作為“通過戲劇、音樂、舞蹈三者高度融合來講述故事、刻畫人物的一種舞臺形態”,與王國維所言“以歌舞演故事”的戲曲似乎異曲同工。但其間不容忽視的差異,我認為是因為戲曲的“歌”與“舞”的特殊性。齊如山將其總結為“無聲不歌,無動不舞”八個字,可見戲曲并非是真的唱歌跳舞,而是一切聲音(包括念白)的韻律性,一切動作(包括形體)的美感。李春熹在總結阿甲戲曲表演理論時更確切地說道:“在戲曲中,歌具體為唱、念,舞具體為做、打,唱、念要有音樂的節奏和旋律,身段動作要有舞蹈的韻律和姿態,于是,唱、做、念、打就成了創造歌舞化的舞臺形象的基本藝術手段。”
如果說,在“歌”的方面,雖然“浙百”引入了多種音樂元素和話劇式念白,但在其“堅持浙江官話,包括流派唱腔”的理念指導下,唱念的主體仍在傳統越劇范疇內。而在“舞”的方面,“浙百”的藝術追求早已與傳統戲曲的“程式化”背道而馳。
“浙百”的藝術理念是“寫意性”,茅威濤并沒有為此做出嚴格的解釋。黃佐臨提出了“寫意戲劇觀”,他曾提到寫實與寫意的區別在于前者“造成生活幻覺”而后者“破除生活幻覺”。在此基礎上,我理解舞臺表演上的寫實性是自然、如實地反映現實,而寫意性則是對現實的夸張與變形。毋庸置疑,傳統戲曲必然是寫意的,然而只要滿足了寫意性就是戲曲嗎?我認為并不盡然,舉例來說,傳統戲曲里的扇子功和“浙百”版的《梁祝》的扇子舞都是寫意的,然而后者是非戲曲的。
戲曲中的程式化的“舞”,包括了手、腿、步、眼、頭、身等各種形體動作,袖蟒帶靠、盔帽翎發、髯口、馬鞭、扇子、云帚、手帕等服道動作以及毯子功、把子功與舞臺調度等。它是“對自然生活的高度技術概括”。從夸張與變形的程度上來說,程式化的動作是較為適中的,冉常建在《表意主義戲劇》里指出“太似生活的‘形,就沒有戲曲的美感;完全不似生活的‘形,觀眾又難以理解。因此,變形要保持適當的中和之‘度。”荀慧生大師也有著類似的看法,他說:“戲就有個別扭的脾氣:你演得不真,違背生活了,不行;真要是真了,和生活一點不差,也不行。”正是程式動作遵從著生活邏輯,觀眾才能夠憑借生活經驗和審美經驗理解程式動作的含義,從程式中體驗角色的身份、環境、性格、情緒,同時又是因為程式動作具有形式上的藝術美感,才能為觀眾提供深刻的審美愉悅。
而“浙百”以《寒情》、《梁祝》扇子舞為代表的“舞”,則更抽象,更寫意,即離生活更遠,夸張與變形程度更大,更遠離戲曲的本質而接近舞蹈的本質,即旨在呈現肢體的律動而非對生活的摹擬。換句話說,演員并不通過舞蹈動作喚起我們的生活經驗去理解人物,而是以一組肢體運動的姿態、動作、節奏、力度訴諸感官,激起情感共鳴。
這種高度的寫意風格,我認為正是茅威濤與郭小男共同的美學追求。在這一點上,他們實際上比他們所以為的走得更遠。比如《寒情》、《梁祝》的扇子舞,《藏》(首版《藏書之家》)的水袖舞等更加強調節奏、線條與構圖,無論比中國的戲曲身段還是西方音樂劇中表演性的舞蹈,都更加抽象。我認為他們所追求的,也是他們所擅長的“詩化、唯美”的寫意風格,更多地屬于空間藝術,這也正與大家所一致贊賞的小百花強于視覺元素是一致的。更確切地說,是茅威濤表演上擅長意象的創造,郭小男在導演上擅長于意境的營造。
人物意象的創造即能夠抓住角色的“意”找到傳神的“象”,并通過精準地表現人物的“象”傳遞出人物的“意”。比如說,“浙百”版的《西廂記》里,茅威濤抓準了張生的儒雅與癡狂,并賦予其“踢褶子”的“象”。我認為茅威濤對“踢褶子”這一動作的運用不是程式化的,而是造型化的。張生多次在不同情境與情緒下運用踢褶子這一動作,并非是摹擬一個精準的動作,亦非是傳達一個特定的情緒,而是“踢褶子”這組動作的線條、節奏、力度、運動軌跡結合起來的“象”正與她所想塑造的儒雅癡狂灑脫不羈的張生十分吻合。更進一步地,《孔乙己》里孔乙己貫穿全劇的、一襲白衫的儒雅造型,茅威濤扮相氣質的瀟灑俊逸,與極富匠心的側頭駝背的人體姿態,綜合而成的這一空間造型藝術,即能準確無誤地傳達出孔乙己的落魄書生形象。同樣的還有《二泉映月》里結尾處阿炳在月中拉琴,衣袂翻飛、長發飄揚的定格。
與意象相仿,意境的營造即是能通過舞美元素、人物構圖等合成的寫意空間精準地傳遞出劇本的風格與情感核心。換句話說,為了傳達劇目的精神與情感,導演更多的興趣在于視覺空間的營造。比如《梁祝》中導演用了相對而跪,兩扇相合的構圖來表現二人的兩心相通,永不離分;“化蝶”更是以漫天花雨的舞美視覺去傳達這一動作背后異乎尋常的唯美與浪漫。或許對于《步步驚心》來說,沒有比角色幽靈般在后景緩緩穿梭更能表達出穿越的迷幻氣質了。到《二泉映月》中純白簡約的舞臺,似乎也是要觀眾既能看到無錫的粉墻黛瓦,又恰能聯想到阿炳像孩童一樣單純,藝術家一樣的率真的心。
可以說,精準的視覺元素的把握與傳遞是“浙百”的獨特優勢,但它的危險之處則是容易造成表導演對空間視覺元素的過度依賴,而忽略了戲劇時間的藝術與更深層的訴諸心靈的感動。這大概就是為什么茅威濤對《梁祝》最為滿意,而評論界卻認為它誤入歧途。茅威濤探索中亟待解決的另一問題,我覺得是一劇之中“寫意”程度相差過大,造成了藝術真實的混亂。這還是在《梁祝》中有最為突出的體現,比如“草橋結拜”和“十八相送”已屬于舞蹈范疇,高度的藝術變形與現實生活已相距甚遠,但為什么還有評論以四九和銀心沒有拿行李違背了生活真實去指責它呢?我認為正是由于“戲”的部分與“舞”的部分藝術真實沒有融合統一造成的。
當然,不同的藝術形態并不意味著美學意義上的高下。是否屬于戲曲并不能成為衡量“浙百”新編劇目質量的準繩。茅威濤以一己之力摸索十幾年的新形式若是要對壘發展了數百年的越劇,這種較量本身也有失公允。若單單從藝術上來說,“中國式音樂劇”如果是茅威濤與郭小男的藝術追求,本是無可厚非的。傅謹老師不是也說“最低限度,就算為他們自得其樂,也已經是充足的理由”了么。但他接下來又說:“我所不能同意的,是簡單地把自己的個人選擇,看成是藝術發展的方向。我贊成并欣賞茅威濤自己的追求……然而,我并不認為必須把這意義放大為越劇發展的方向。”這段話所透露出的擔憂是喜歡傳統越劇的觀眾所共有的。
在我看來,“發展”卻是個偽命題,倘若越劇真有一天“發展”成了“新越劇”,實際上是傳統越劇的滅亡,而存活下來的只是稱之為越劇的所謂“中國式音樂劇”而已。因此這份擔憂指向的是傳統越劇滅亡的可能性,是其余二十多家越劇院團陣地盡失的可能性。提供了此種可能性的,說明了越劇作為一門表演藝術,它的表演手段尚未成熟就在繼承中逐步退化。無論是傳統越劇還是新越劇,都既是藝術,也是娛樂,旨在為觀眾提供審美愉悅。盡管“浙百”提出過時尚化、都市化的口號,但我認為眼下新編劇目同臺打擂,“浙百”勝出的根本原因是普遍來說越劇界不僅沒能在戲曲范疇內填補它“薄弱的家底”,甚至連繼承與維持傳統越劇唱念做表、舞美服飾的藝術魅力都力有不逮,這方面各院團無不呈現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窘境,而“浙百”靠著視覺意象所提供的審美資源彌補了越劇日漸衰退的藝術表現力。若真要談越劇的發展與振興,對于茅威濤來說,或者可以嘗試戲曲程式化的表達與其擅長的視覺意象、意境的進一步融合,《二泉映月》正是向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且收到了較好的口碑。對于其他各個院團來說,首要問題應是提高自身的藝術表現力為觀眾提供審美愉悅,一味靠流行、時尚作品的改編迎合觀眾恐怕是飲鴆止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