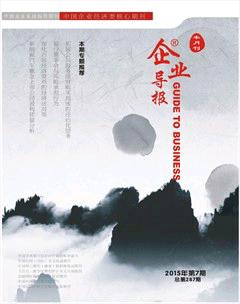女性主義對社會工作實踐的指導意義
徐莎莎
摘 要:女性主義作為外借理論,為社會工作實踐提供了全新的審視視角。本文首先回顧了三波女性主義帶來的革命性的變化,試圖梳理出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基本框架,并討論其指導意義,對社會工作實踐主題進行檢視反思。
關鍵詞: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實踐反思
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將女性反抗的聲音第一次全面地正式地引入到政治生活中,在此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眾多被喚醒的女性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從爭取政治權利、教育權利、工作權利到批判及反抗父權制意識形態壓迫,對以性別壓迫為基礎的社會不平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抗。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服務對象以女性為主的社會工作,也在理論和實踐中開始引入女性主義視角。性別視角讓社會工作開始重思“案主”和問題的本質,對專業關系中無處不在的性別壓迫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不平等有了更深入的討論。
一、女性主義理論及實踐回顧
第一波運動中出現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非常重視女性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其基本立場可以被表述為一種社會正義的立場: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里,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獲得平等發揮自己潛力的機會,男女兩性應該擁有同等的競爭機會(李銀河,2005)。其主要目標就是為女性爭取到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即在現有社會結構之內為女性爭取男性所享有的公民權利。之后的激進女性主義開始用父權制來描述男性對女性的系統壓迫,通過這套話語體系,女性被被嚴格限定在家庭中的妻子、母親的角色。激進女性主義革命性地提出了一個口號“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經歷的困擾和痛苦不只是個人生活的苦難,更是性別關系的權力壓迫下的結果。在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還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后者認為,女性問題在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將得到根本的解決。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徑是進入社會主義勞動市場(李銀河,2005)。對女性參與有薪工作的提倡首先建基于對家庭神圣性的破除,這讓女性從從屬地位走出來,并顯示出了家務勞動對于家庭利益的價值。而后現代女性主義的出現則對之前的女性主義有了一個顛覆性的沖擊。有的理論家甚至將這一新流派的出現稱為女性運動的“第三次浪潮”。對于“女性”這個詞,后現代主義認為此前的理解都是本質主義的單一化理解,忽視了女性這一群體中的差異和個別性。同時由于后現代的哲學起點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理論流派,后現代女性主義也拒絕關于社會的父權制結構的元敘事——而這正是非后現代女性主義流派的基本主張(Dominelli,1999)——轉而對現代思想中的兩分對立的本質主義、普適性知識、終極真理、話語的權力進行批判,宣揚應該建立一套女性的話語,并在關注差異的意義上提倡女性寫作自我表現的文本。
二、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工作重點一方面是在社會權力結構內爭取平等參與的機會,一方面鼓勵女性加強利用資源實現自身潛能的能力,但對社會結構沒有總體批判,這與社會工作中關注案主自身的專業起點相適應,在實踐中強化了針對“案主”自身技能提高的服務內容,比如協助案主學習育兒技能,參加家政訓練,學習如何更好地操持家務,做一個稱職的母親。作為對女性同等就業機會主張的回應,社會工作也鼓勵女性通過教育和培訓在職業發展上進階到更高階層,鼓勵女性通過有酬勞動獲得經濟獨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支持對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劃分,讓工作者和服務對象自己清楚地看到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相互作用:在謀求個人生存和福利的私人領域,國家通過福利資源的分配和身份的認定,將個人與家庭歸置于國家市場的結構中,個人生活的福祉在根本上要取決于國家對于福利的看法,對弱勢群體的看法。公共領域同樣影響到了女性的私人家庭生活,因為它也是社會政策制定的目標(Sassoon,
1987)。激進女性主義對于社會工作最大的影響,在于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實踐中以新的視角看待“案主”的身份。基于對父權制社會的批判,社會工作者開始將案主的問題歸因于社會權力結構,尤其是女性案主的問題,是被男權意識形態創造出來。在社會工作服務中,為女性賦權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大量意識提升小組的開展,這被認為在女性自我能力信心的提高等方面的不同資源創造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Jagar,1983)。除了這樣的意識提升小組外,一些社會工作機構也分離出專供女性使用的場所,比如暴力庇護所、男性受害者保護者組織,并在這些場所中引導女性相互支持,建立女性社會網絡。尊重個人自決,也是社會工作歷來傳統,而后現代女性主義對“女性”這一概念質疑,認為這沒有體現出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性,這在社會工作中就直接體現為應該尊重不同階層不同類別的女性的特點和需求,對差異性的承認和尊重也就成為必然。在以往的社會工作中,對“差異”一般會建構為不足,認為與主流群體不同就是一種缺失。而對差異的正視和重新認識,將其理解為是個人特質,是值得頌揚的。
社會工作關注困境中的人和邊緣群體以及追求社會公平的專業取向,與女性主義呼吁為女性爭取資源和機會,筆者認為這兩者在價值出發點上是相合的,也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出現并對社會工作產生重大影響和革新推動的原因。我試圖從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的結合中理解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視角的基本框架。
第一、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個人處遇與更廣闊背景上的父權結構相聯系。在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中,個人問題并不是個人品質造成的過錯,這一觀點在以往的社會工作中也是存有的,但女性主義思想革命性地將問題歸責于父權社會的建構,對問題的歸因,已經由階級分析、民族國家分析轉向了更深一層次的父權壓迫。對父權制權力結構的批判在社會工作實踐中,帶來的對案主的非批判和解放程度也是最大的。
第二、對父權體制的批判改變了對個人問題的定義與建構。每個人都在受到父權文化的壓迫和鞭撻,不止女性,男性同樣在被這文化束縛。父權制文化被創造出來,又反過來成為了鉗制人們的痛苦淵源。當人們想要從這強大束縛中逃脫出來做自己時,就會變成有問題的人。有了對父權制結構的批判視野,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在共同界定問題時會做出新的解釋,將問題與“案主”身份分離,是新的服務關系的開始。
第三、去除父權主流話語的強加;看到個人獨特性,尊重差異。對終極真理的拒絕,強調多元真理和微小敘事的認識論在社會工作實踐中直接表現為關注個體,關注差異。在撥開父權迷霧的糾纏后,展現出具有獨特性的個體。只有尊重個人的獨特性,發展每一個個體的真理,才會去理解個人的特殊境況,而不是指責其沒有按照主流話語安排來生活。對其差異的尊重有助于對問題的解構和新生活信念的建構。
第四、“賦權”的神秘能量。對權力關系的理解,尤其是在社會關系中的創造與再創造關系,是女性主義壓迫理論和靈活建構日常生活理論的根本,也是認同個體被社會建構的自我立場的關鍵(hartsock,1987)。對當下的權力結構的反抗從個人的意識提升開始,賦權滲透在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方方面面。解除精神枷鎖,重生一個強大充滿力量的自我,賦權猶如一捧靈魂的清泉滋潤了一直干渴著的靈魂。
三、社會工作中的女性主義檢視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要求將個人命運與父權制文化聯系起來,將個人的處遇置于父權壓迫的社會權力結構中檢視,對概念本身解構和對本質主義質疑,這帶來了在社會工作實踐中不停的解構-重構-解構的循環過程。
(一)對專業關系的思考。女性主義的觀點將社會工作者看作是潛在的壓迫者,“案主”與工作者的關系是潛在的壓迫關系。作為一個專業體系,社會工作有自己的基本假設,工作者在實際的社工實踐中是帶有專業化的知識、權力的,“案主”也會將工作者作為一個在問題解決上優越于自己的主體來對待。權力關系的帶入使“案主”再次進入一個被削減權能的過程,“案主”按照工作者的知識指導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會留下另一個問題,這是一個被剝奪了主體性的個體無法逃脫的。社會工作者隨時都要看到在專業關系中埋藏的父權等級關系,隨時要檢視自己是否作為了一個父權觀念的言說者,是否成為了意識形態的執行者。
(二)對工作關系的思考。在工作場所中,性別關系和性別壓迫也無處不在。在社會工作機構中,基層的實務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而管理層的工作者幾乎都是男性。在追求平等和反壓迫的社工機構中,在一個通常被認為是“女性的行業”中,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都如此牢固不變地存在著。另外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要如何處理工作和生活中性別權力身份的問題。工作者在社工實踐中是一個行動者,呼吁反抗與一切等級秩序聯系起來的性別壓迫;在生活中,工作者作為一個社會結構中的分子,在與底層民眾,包括清潔工、保姆這樣的勞動者之間依然存在著等級秩序中的壓迫;同理女性同樣在被壓迫和壓迫這兩種身份間轉換。這應該要如何處置自己的矛盾?如果社會工作者需要內化價值觀來工作,那在生活中,如何去回避這種無處不在的壓迫呢?
(三)對工作者身份的思考。女性主義對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進行了劃分。在私人領域中,個人生活的福祉并不主要依賴于個人品質和努力,在根本上取決于國家對福利資源的分配。公共領域的變化和政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某一群體的命運走向。有學者認為社會工作者“就是努力要推翻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中的父權制,從而支持女性案主與父權的壓迫作斗爭,尋求其他方式為女性案主和社會工作者賦權。”社會工作在被權力場域接受后,已然成為了政治領域中特定社會行動的工具(Dominelli,1999)。在中國本土化的專業建設中,政府的推動對于社會工作的發展必不可少,社會工作是否會化為一個政府掃除政策執行障礙的工具?要為案主的反壓迫做抗爭的責任又何處安放呢?反抗權力壓迫的社會工作者是否能抵御權力的侵蝕?
四、結語
本文回顧了女性主義的發展及主要流派,對女性主義在社會工作中的運用及在理念和實踐層面的影響做了梳理,最后從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視角出發對社會工作中的幾個核心要素做了探討。女性主義的思想在社會工作得到運用,尤其是后現代女性主義思想對社會工作沖擊極大,對“案主”等本質主義的概念有了革新性的重思,對差異性的關注也使得賦權等理念落到實處。而基于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在追求社會公平、保護權利上的價值同構,在社會工作實踐中運用女性主義視角,能更好地踐行社會工作原初價值。
參考文獻:
[1] 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權辯護[M],商務印書館,1995
[2] Dominell,女性主義社會工作[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7
[3] 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南:山東人民主板社,2005
[4] Showstack Sassoon,Gramsci's politics[M],Martin's Press London ,1987
[5] Hartsock,Rethinking Modernism: Minority vs. Majority Theories[J], Cultural criticism ,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