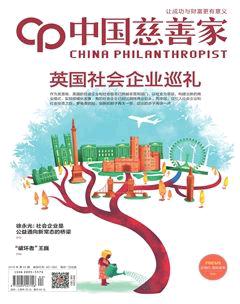沈旭:讓校園告別“校園欺凌”
原寧辰
“想發火時,停一下,深呼吸。”
陜西西安郊區的一所學校里,兩個初一學生由打鬧升級的“戰斗”一觸即發,其中一人忽然將攥緊的拳頭停在空中,亮出手腕上綠色的手環,手環上寫著這句話。
“戰斗”霎時偃旗息鼓。 兩個學生分別冷靜下來,嘗試著管理自己的情緒,并與對方進行溝通。
沈旭很開心看到這樣的結果。這個由她和團隊投入三年精力開發的“減低校園欺凌”公益項目正顯現出成效。
從2002年就投身公益事業的沈旭喜歡不斷創新和探索。她曾任綠網總協調人,后參與樂施會以戲劇方式推廣的發展教育項目,還報名參加為期3年的華德福教育小學資質培訓,創辦靈動珊瑚教育工作室,致力于藝術和治療性教育啟發,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2011年入選南都基金會的“銀杏伙伴成長計劃”,成為沈旭公益事業的轉折點。評選過程中,她被南都基金會監事何進的一句話點醒:“教育不是技術。適當的時候,應該跳出機構的發展,來看這個領域的發展。”
其后,“銀杏伙伴成長計劃”評委之一、陜西婦源匯中心主任高小賢推薦沈旭加入該機構與國際計劃在陜西開展的“減低校園欺凌”項目。“對于校園欺凌,我也關注了很長時間,當時看到這個項目時,非常高興,很想去嘗試。”沈旭告訴《中國慈善家》。
校園欺凌涵蓋廣泛,包括教師對學生、學生對教師、教師對教師、學生對學生等不同群體之間相互使用暴力,造成身心傷害的行為。考慮到如果一開始就介入老師對學生的暴力行為,對老師和學生的沖擊會很大,而介入學生之間,提升孩子行為意識的同時也能很好地減輕老師的壓力,沈旭決定首先從減少學生間的校園欺凌行為著手。
有一個三年級的小女生,在宿舍屢屢被六年級女生抽巴掌,連續一個學期下來,不曾告訴家長和老師。這并非個例。“校園欺凌是孩子之間的以大欺小或是權利不對等,比如利用身高、心理、成績上的優勢進行欺負,還有些是惡意傷害,很容易在隱蔽的地方發生,如廁所、食堂、宿舍等地方。”
遭遇欺凌的孩子會受到很大傷害,性格也受到影響。但是沈旭發現,孩子們普遍認為這是成長中必須經歷的。她意識到,要告訴孩子們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即這樣的事情不需要有。”對那些被欺負的孩子,“我們要告訴他用什么樣的方式來面對。”而對于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們有一些普遍的特質,如不被關注,想被愛,想變得更自信,我們要告訴他,怎樣才是更強大、更棒的人。”
沈旭和團隊耐心地指導老師們如何去識別,去跟兩方不同的群體對話。她建議不要給孩子貼標簽,因為欺負者和被欺負者有時可能是同一個孩子。
因為在戲劇教育方面的得心應手,沈旭一開始在這一項目中采用了很多藝術性教育的內容。雖然覺得新鮮有趣,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老師們普遍覺得很難,硬性規定的60小時課程成為他們不得不“交差”的工作量。
沈旭和團隊伙伴們意識到這件事不能“想當然”,她開始更為落地地尋找問題的所在。于是她和伙伴們蹲在地上,曬著太陽,一對一貼近老師聊天,發現老師們缺失的東西很簡單。“他們從來不了解孩子,因為沒有學過。即使學教育出身,也并不完全了解。他們會很坦誠地告訴我,他們會打罵孩子,也會為此自責、內疚,但是不知道有別的辦法可以做,至少感覺打罵這種方式一段時間內有效。”
他們也和孩子們交流。蹲在地上和孩子們一個個、一小時一小時地訪談下來,發現孩子們的要求也很簡單,“希望老師不要打我罵我,雖然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但是打罵讓我很難過,我只希望他們告訴我怎么做就行。”
沈旭改變了原來的方案。她把設定好的課程全部撤掉,第一年只做骨干教師的培訓,讓骨干教師用他們獲得的戲劇教育能力來改造課堂。在取消課時要求后,老師們創造性地將戲劇內容融合進了語文課、思想品德課,原本一兩個小時的完整架構,在45分鐘的課堂上就完成了。
學生們對這樣的課程內容很感興趣,骨干老師去縣里上公開課也獲得了獎項肯定。看到這些變化后,沈旭開始針對全校教師做基礎內容培訓。她將相關內容編寫成一套簡單易行的教材,內容涉及跟孩子溝通時如何表達,情緒管理如何做到,怎么幫孩子們建立自信,怎么開班會、制定班規,面對校園欺凌時應該怎么做等等。相關的行為規范全部細化制作成手環、卡片等,戴在手腕上,掛在書包上,時刻提醒著學生們。
事情一下子變得簡單、可執行。老師們開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他們或者在課堂花十分鐘給學生講故事,或者在課堂前幾分鐘讓孩子輪流上來欣賞自己。“老師們開始覺得跟班里孩子的關系變得不一樣了,他們減少了打罵,孩子們相互沖突和欺負的行為也開始變少。”沈旭說。
在暑期夏令營活動中,沈旭讓孩子們做了很多海報,宣傳什么是校園欺凌,同學之間應該如何更好相處。她還根據學生自己的故事排演了兩個劇本,在學校做公演。一段時間下來,學生們告訴沈旭,學校里的校園欺凌“幾乎不再發生”。
與此同時,參加培訓的老師也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夏令營的很多隊員都是來自當地教育局工作人員的子女,在一次培訓中,沈旭告訴參會教師,夏令營中一個女孩找她談話,因為爸爸覺得她撒謊,用晾衣桿打她,甚至把晾衣桿都打斷了,她心里感到非常委屈。在培訓的總結環節,一個女老師告訴沈旭,那是她家的孩子,她感到很內疚、難過。但是培訓結束后,很多老師紛紛表示那是自己家的孩子。“說明這不是一個家庭發生的事情,很普遍。”沈旭的內心也終于放松下來,“當老師們可以很坦誠地把想法講出來的時候,他就愿意做出改變了。”
沈旭和團隊還做了個“傻瓜版”指導手冊,通過走訪時積累的大量案例,對一旦出現問題,老師與學生如何更有效地溝通,每一句話該怎么說等都做了詳細指導。
這些瑣碎具體的工作讓曾經喜歡求新求變的沈旭變得落地而踏實,“原來我會很不屑這些東西,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悟性,后來發現我們成長的背景并不公平對等,老師們接受的信息量其實并不多。”
經歷了這些改變,沈旭終于找到了項目的核心解決方案:減少校園欺凌只是一個切入點,真正要做的是改善校園師生關系,創造更好的校園環境。
目前,她和伙伴們申請成立了陜西光合行動青少年教育發展研究院,意在培養一批致力于青少年教育的社工,在自己的崗位和機構中做推動。她也希望能夠進行一系列行動研究,將青少年教育過程中的經驗記錄并分享出來。當下,也有基金會正在跟她談合作,希望能夠介入服刑子女群體,探索社區教養的方式。
關于機構的未來,沈旭很清楚做可操作、可復制的項目,更容易受到基金會青睞并順利籌款,但是她認為設計“產品”的公益機構并不在少數,她希望未來團隊能更多地介入人與人的關系中。“一切都回到最初,最簡單又是最關鍵的東西就是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建立,聽到彼此的需求和聲音。”
沈旭早年學心理治療時,老師曾告訴她,到最后,其實已經不用技術,一個眼神,一句話,你坐在那兒,對方就已經知道你是否理解他,重要的是,能否把心交給對方。沈旭內心深刻地感知到這種力量,“當學生發生改變時,我能感覺到。因為在那一刻,我完全忘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