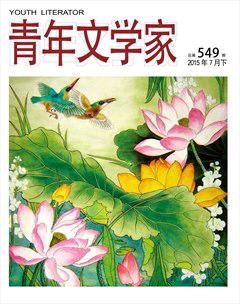論亂世下的艱難成長與復活新生
摘 ?要:借助戰爭的背景,促使崔梅玲從迷茫少女成長為一名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獨立新女性,展現出一位不諳世事的少女艱難的成長歷程,并通過她最終的蛻變與新生寄予了林語堂獨特的女性觀,并從崔梅玲獨特的人生經歷上展現出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情結。
關鍵詞:崔梅玲;成長;獨立女性;女性崇拜
作者簡介:朱翠(1990-),女,山東省泰安人,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2013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1-0-01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道主義作家,林語堂終其一生都在關注人的生活與命運,尤其是對“女性”的關注,“‘是否關注和如何關注女性成為衡定現代人優劣高下的試金石”。[1]誠然從林語堂的作品中看得出,他不僅關注女性,而且還有著獨特的女性觀和女性崇拜情結。他傾盡才情塑造女性形象,極盡描繪其婀娜多姿的外形、賢良淑德的品行及其獨立的人格思想。本文主要從他“三部曲之一”《風聲鶴唳》入手,通過崔梅玲坎坷的人生經歷,展現“抗日風雨中一個女性的心靈蛻變”[2]的過程,并從中探究林語堂的女性情結。
一、一個獨立女性的艱難成長與新生
(一)迷茫與封閉——依附男人的無知少女
小說開篇并未直接講述崔梅玲的不幸遭遇,而是對她的身份給予了保留,顯出神秘色彩。她以博雅舅媽朋友的身份住進姚家,并與博雅相識。彼此為對方出眾的外表和氣質所吸引,很快產生感情。隨著兩人關系的熟識,梅玲的身世之謎才逐漸揭開。
崔梅玲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始終處于逃跑和迷茫之中。她從不幸的婚姻中逃走,為生存而過著依附男人的寄生生活,她不諳世事,始終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在識破情人利用她進行賣國勾當后,她為追求愛情和自由,再一次選擇了逃離。
此時的崔梅玲年少無知,生活的凄苦和不幸迫使她選擇了錯誤的人生道路,不管她嫁人還是被包養,始終沒有獲得真正的愛情和獨立的精神。混亂的生活攪碎了她的生活,使她成為動亂年代的犧牲品,盡管命運給她戴上了枷鎖,但她的精神并沒有被束縛。為了爭取自由與獨立,她一次次逃亡,尋找命運和愛情的歸宿,直到遇到博雅。
(二)尋找與彷徨——沉溺戀愛的苦樂情人
為躲避追捕,梅玲逃到了姚家,她的出現彌補了博雅對愛情婚姻所有美好的憧憬。隨著梅玲身份的不斷清晰,博雅并沒有因她的過去而放棄她,相反兩人的愛逐漸加深。梅玲因博雅的愛而異常痛恨自己的過去,因此她處處小心翼翼,對博雅表現出順從柔和的姿態,甘意匍匐在他的腳下,暫做他的情婦。
盡管邁出了尋找愛情的第一步,但她依然沒有改變她的依附地位,而是沉浸在愛情里再一次迷失了自我。他們偷偷約會,盡享愛情的歡愉。但隨著梅玲的行蹤被發現,她不得不再次走上了逃亡之路,而與博雅失去了聯系。
此時的梅玲正在成長,但依然沉溺在個人的世界里,她與博雅產生誤會時,她表現出彷徨與不安,進行種種猜疑;當她與博雅失聯后,她陷入了悲痛與絕望;在與博雅誤會解除時,她又恢復了青春的張揚與魅力。與博雅的愛情始終控制著她的思想與行動,盡管她勇于追求愛情的自由,但她依舊沒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始終處于被牽制狀態。
(三)覺醒與頓悟——獻身事業的獨立女性
博雅的好友老彭在梅玲身陷危機時及時幫助她逃到了上海,在到處是戰火與逃亡的途中,兩人的關系逐漸親密。老彭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具有菩薩般的慈悲心腸。在他聽說崔梅玲的不幸遭遇后,鼓勵她說:“我覺得你仍是一個年輕而純潔的女子。你還不知世事。我希望你永保赤子之心。”[3]P144他用佛教的信念寬慰她、引導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普渡眾生、‘請慈悲,解救人類的苦難”[3]P176還讓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重新開始新的生活,給她起了新名字——彭丹妮,在老彭的幫助下,丹妮有了面對生活的勇氣。在經歷佛家思想與殘酷戰爭的雙重洗禮后,她逐漸成長為一位無需依賴別人而獨立自主的時代新女性。
丹妮在跟隨老彭收治難民的工作中獲得了新的生命,被人尊稱為“觀音姐姐”。她開始發自內心地尋求真理與欲望的解脫,最終,她憑借老彭的引導獲得了信仰的力量,使她最終決定選擇付出“無私的仁慈和同情以普渡眾生的苦難”[4]。戰爭和苦難激勵著她成長,在佛教“普渡眾生”、“慧心”的指引下,她幡然醒悟。她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個人的愛恨情仇,而是立足于當前社會實際,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并通過努力,實現了自我的人生價值,從而獲得了幸福與滿足。
二、從崔梅玲看林語堂的女性觀
林語堂學貫中西的成長背景,使他的女性觀較為復雜。他理想中的女性,既要符合傳統婦德規范的要求,又要有現代女性獨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崔梅玲即是這樣的代表,她善良體貼,具有博愛的情懷,從最初的墮落人生通過自己的不斷努力,最終投身于民族解放事業,在奉獻中實現了自我的價值與人格的獨立。
林語堂還具有女性崇拜情結,在崔梅玲身上,她為爭取個人自由逃出了夫家;為尋求真正的愛情而離開了寄生生活;在戰爭的磨難下她與不幸的命運抗爭,養成了獨立自主的品格。林語堂通過描寫崔梅玲經受戰爭洗禮后的成功蛻變,把“個人小愛”擴大為“人間大愛”以及人們對她的尊敬,表現出林語堂對女性所具有的不屈服于命運的抗爭意識、對苦難的化解能力、樂善好施的博愛情懷和獨立自主精神的贊美與崇敬,并從中寄予了他獨特的女性崇拜意識和特殊情懷。
參考文獻:
[1].王兆勝.論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J].社會科學戰線,1998,1.
[2].郭海燕.論林語堂的小說三部曲[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1,4.
[3].林語堂.風聲鶴唳.林語堂小說集[M].上海:上海書店,1989,144,176.
[4].默崎.跨文化寫作中的林語堂小說[J].鄭州大學學報,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