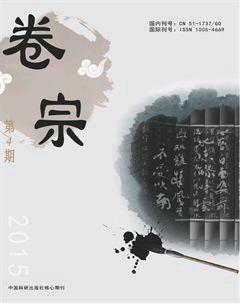從“禁碑”看明清時期的蘇州地方社會問題
摘 要:碑刻的史料價值之高歷來是史學界的共識。本文即是擬通過對蘇州明清時期碑刻中的“禁碑”的解讀,對當時蘇州社會出現的一些問題以及政府對此所進行的管理等進行一個大致的了解。
關鍵詞:明清;蘇州;碑刻;社會
21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研究在中國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趨勢,越來越多的相關資料也進入了史學家的視野和研究領域。碑刻以其獨特的文化載體的形式和其所蘊含的豐富的社會內容而成為了各路史家所關注的資料。
明清時期的蘇州,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興起,城市規模日益擴大,人口愈來愈多,社會生活也日漸多樣化和復雜化起來,該時期的蘇州成為無業游民的重要滋生地。明清時期的蘇州嫖賭、誆騙、斗毆之類的社會陋習污濁泛濫,搶劫、盜竊、謀財害命等犯罪活動十分猖獗,往往與這些不務正業的流氓無賴有著密切的關系。
1 賭風盛行
明清時期,特別是明末清初時期,吳地的賭博之風大肆盛行。“從康熙以后,無論在地方志還是在私人筆記中,賭博都被當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提出、而譴責,并屢屢被地方官府嚴令禁止。然而賭博現象非但未曾斷絕,反而形成風氣,越來越盛,幾乎達到無處不賭的程度。”
道光三十年的《吳縣禁止沿廟聚賭滋擾碑》,碑文為:“天庫前地方,向奉周宣靈王,神佑一方,素著靈應,奉旨給予祀典。前因廟基湫隘,屋宇坍塌,生等捐募建修殿宇房廊。工程敷竣,竟有閑人沿廟聚賭,以及逞酒滋事。雖經生等驅逐,得以安靖,誠恐日久復擾,稟請示禁。”宣統二年的《某圩奉憲議定禁約碑》,此碑文和上一篇不同的是,上件碑刻的重點即是禁賭,而此件禁止的內容涉及各個方面,其中和禁賭有關的內容為:“抵制茶館抽頭聚賭,私賣洋煙。”
從這兩件碑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吳地的賭風之烈、流行之廣。首先從賭博的場所來看,從日常民眾的聚居、生活之地——茶館,到本該保持一方凈土的宗教圣地——廟宇,都有聚眾賭博的行為發生。其次,再從賭博的參與人員來看,雖然這兩件碑文并未直接涉及到聚賭人員的身份、地位、職業等信息,但從碑文隱含的信息中我們也可以大致界定出來,如碑文中有“閑人”二字,再加之此類人等竟敢于沿廟聚賭,可見心中并無什么忌憚之處,必是游手無賴之徒。茶館成為賭博的重要場所,而一般去茶館的人除了平民百姓外,還包括以下人員:上至官紳士大夫,下至從事各類賤業的人員,甚至無賴之徒。可見整個社會,不分貴賤、不分男女、不分長幼全都卷入了賭博的漩渦。
2 地痞惡棍眾多、偷盜行為頻頻
明清時期的蘇州,無業游民眾多可謂一大特色。當時,對這些不務正業、滋事生非的人員的叫法也是五花八門,“地痞”、“惡棍”、“棍徒”、“地棍”、“痞棍”、“豪棍”等應有盡有,他們由于沒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干一些偷盜、行騙、豪取等事,給當時的蘇州社會和蘇州百姓造成了不少的困擾和負擔。
《江蘇按察司永禁蘇州私宰耕牛》碑,此碑文論及了耕牛的重要作用以及農民對它的依賴,“牛只雖同列于六畜,而裨益農民,其功甚大,駕車則多資負載,力田則全代耕耘。小民終歲勤劬,動需倚賴”,可見,耕牛是農民的家業之一,絕不會輕易出賣,但此時的蘇州城內出現了大量被宰剝的牛只,考慮到蘇州并無牛販往來,且菜牛也是絕少的,故絕大部分牛只是實際是農民所畜。地痞惡棍“茍非窩伙偷竊,則市肆屠戮”,“明系棍徒開局私宰,包賊消贓,以致下鄉肆竊,民不聊生”。從這件碑文中,我們看出, “棍徒”不但直接參與到偷盜耕牛的違法行動中,而且幫助盜匪銷贓,“棍徒”的這一行徑無疑讓盜賊無后顧之憂,助長了這一不法行為。
地痞惡棍的惡行雖多種多樣,但最常見于碑刻的還屬偷盜一行。陳江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一書中提及到:“其盜竊名目眾多,小至偷雞摸狗,大至結伙哄搶,無所不為。”偷盜行為如此猖狂,以致于蘇州政府不得不制定相關的政令,來對贓物的收繳作出規定, “仰典商知悉:嗣后,凡獲賊供出當贓,遵照憲飭事理,赴典認明,定案詳結。如果事關題請內結重案,吊起給主。倘一切外結竊案,追本免利取贖。”如此規定的主要原因是“盜賊當贓,分別起取之法,不致虧商累民”。
明清時期的蘇州“盜風日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游手無賴之徒劇增;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很多人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不惜抱著投機取巧的心理而鋌而走險;三、《長洲縣諭禁捕盜詐民大害碑》則提供了另一個原因,即當時政府的腐敗無能,甚至“捕盜交通”、“官盜一家”,為了獲取額外的利益,捕盜之人竟然和盜賊相溝通,污蔑陷害良善之人,極盡勒索之能事,普通家庭不得不采取一切辦法來應付這樣的禍害,這讓當地居民大受其害。即使后來事情真相大白,但已家不成家了。
3 “民風詐偽,訟獄繁滋”
明清時期蘇州的“健訟”也是出了名的。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主張德行并重、恩威并施,是以孔子的“無訟”為理想藍圖的。但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民間社會從最初的厭訟、恥訟過渡到了健訟、囂訟,甚至出現了“無慌不成狀”、“無賴不成詞”的說法。
《長吳二縣飭禁著犯之弊碑》,“犯罪應糾本人,難容株□。江左地方,民風詐偽,訟獄繁滋,海市蜃樓,不可枚舉。”此外,此碑文的內容還透露了為什么該地區會出現健訟之風。以著犯事為例,捕役的指鹿為馬、隨意添加著犯人員;惡棍的不法貪婪之心;捕役和地棍的竄通等等,這些都使越來越多的人牽涉到案件中,使當地出現了“獄訟繁滋”的現象,“及至被著之人,家破人亡,而所著之犯,仍無影響。有司習而不察,以致無罪良民陰受其禍者,不知凡幾也”。針對這一問題,政府發令:“其余一切詞訟及各項案犯,只開本犯真實姓名、住址,按照緝拿,不許著于他人名下追要。如違,原告治以無線之罪,捕快差役照誣拿例重處,該官管以失察查參,庶積弊頓除□焉。”
有關人員的故意挑唆也是蘇州地區“健訟”的重要原因之一。《吳縣抄示嚴禁自盡圖賴以重民命碑》,“而小民愚憨,每因細故,動輒輕生,其親屬聽人主唆,無不砌詞混控,牽涉多人,意在圖財,兼圖泄忿。經年累月,蔓引株連,被告深受其害”。親人自盡,而親屬在一些人的唆使下,誣告詐賴,貽害別人。這其中,訟師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此類訴訟頗多就是由訟師挑唆引起的。訟師憑藉為人打官司而獲得生活的來源,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注釋
[1]陳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頁。
[2]王衛平:《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
[3]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頁。
[4]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頁。
[5]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4頁。
[6]陳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頁。
[7]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頁。
[8]靳欣:《論明清時期“無慌不成狀”之成因》,《陜西教育·高教》,2012(10)。
[9]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頁。
[10]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頁。
[11]唐力行、王國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頁。
參考文獻
[1]唐力行、王衛平:《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2]陳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
[3]王衛平:“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
[4] 靳欣:“論明清時期‘無慌不成狀之成因”,《陜西教育·高教》,2012(10)。
作者簡介
周麗華(1988—),女,江蘇泰州,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專門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