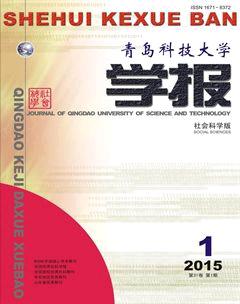相反相成 和諧人生
楊朝明 李文文
[摘 要]無論學術傳統還是文化傳統,常將儒家與道家、孔子與老子放在對立的位置上加以觀照和研究。通過對讀先秦儒家與道家典籍中的相關文獻,尤其《孔子家語》與《道德經》,可以看到孔子與老子的人生哲學實是深深扎根于西周文明土壤的并蒂之花。兩者在人生哲學的諸多方面存在極大的相通乃至相同,這也啟迪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認識先秦儒家與道家文獻的理論意義及其對于和諧人生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孔子;老子;道;相反相成;和諧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5)01-0023-08
Abstract:Both academic tradit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ten make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Taoism, Confucius and Lao Tzu be in the opposite position to observe and study. From th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specially from the Homely Talks of Confucius and Tao Te Ching,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 philosophy life of Confucius and Lao Tzu are the flowers of Bingdi which are rooted in the civilization soil of the Western Zhou. And there also exists terrific similarities and even the same in their philosophy lif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evaluat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o harmonious lif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Confucius; Lao Tzu; doctrine; opposite each other; harmony
無論學術傳統還是文化傳統,我們研究孔子與老子的關系,往往看到的是二人的差異,或者說,我們已經習慣于將儒家與道家、孔子與老子放在對立的地位上去觀照。然而,當我們研讀《孔子家語》時,又真真切切地感到他們在人生哲學方法論上的深層一致性。《孔子家語》的幾個篇章都有孔子“聞諸老聃”之類的說法,《孔子家語·致思》篇則記載孔子本人所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這是說的南宮敬叔幫助孔子一起適周問禮的事情,所以王肅注曰:“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于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這一說法不僅有《孔子家語·觀周》篇的詳細記述,而且很多典籍都可印證,二人的一致淵源有自。
孔子、老子的相通乃至相同意義重大,這對于“中國傳統思想”研究方法的補偏救弊十分必要,也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孔子家語》的價值等學術問題。我們對讀先秦儒家與道家典籍,尤其思考《孔子家語》與《道德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與老子的人生哲學實是深深扎根于周代文明土壤的并蒂之花。既然我們常常奢談儒、道之異,則不妨回到“儒”與“道”的源頭,研究他們的思維方式。在孔子、老子那里,會得到許多關于和諧人生的智慧啟迪。
一、成而必變,相反相成
西方有哲學家認為,之所以不斷有人投身哲學領域進行研究,目的之一便是追求永恒。這種追求是一種本能,最早出于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災難的躲避。今日,難道熱愛生活和躲避災難不仍是哲學研究的至高追求?實際上,中國古老的思想傳統,也是在這樣的追尋中產生、發展的。
今本《逸周書》的第一篇《度訓》,其開篇曰: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
先王建立制度,同樣是基于對民性、民生的思考,所以《度訓》又曰: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然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
順民之好惡,思想者立中補損,從而度小大、權輕重、明本末。
這里《逸周書》講述了“損益”之道,也就是關于“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的道理,后來,老子、孔子都曾談到。
老子曰: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道德經》第四十八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道德經》第七十七章)
事物往往就是這樣,常常會因為外部條件有所不足反而發展得好,或是得到好的外部條件發展反而受到束縛。這就像一個飽經滄桑的人,他歷盡了苦難,苦難反而成了他成才的條件。損中有益,益中有損,二者不以對立的屬性而存在,而是相互滲透,相輔相成。“學”與“道”就是如此,為學日有增益,為道則日有減損。“學”愈厚而“道”愈精。“道”愈精,境界越高,最后就達到無為之境了。
認識到這一點,是基于對天地運行法則的把握。老子看到,天道往往減損有余來補給不足,所以“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他看到了“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的規律,于是形成了這一認知。
孔子也對“損益”之道有深刻認識。《孔子家語·六本》記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弟子子夏詢問他何以嘆息,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孔子此言,與老子“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如出一轍。
接著,孔子談了“為學”與“為道”的關系:
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
在孔子弟子中,子夏于諸經皆有鉆研,特別注意發掘經意。他細察《易》理,《隋書·經籍志》稱子夏傳《易》,曰:“孔子為《彖》《象》《系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他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是從義理上引申發揮,因此后人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1]。在這里,作為孔子易學傳人中的翹楚,子夏被孔子的論述所折服。所以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成而必變”,在孔子本人看來屬于“天道”使然。與老子一樣,孔子認為一個人對道術的掌握越是廣博精到,就越感不足,就“損其自多”。作為學者,自認為不足之處有很多,才會“以虛受人”,由此而達至成就盈滿,不斷向上。天道所昭示的,就是“有所成則有所變”這樣的道理。
不難理解,經典的本質,乃是先賢圣哲用他們的真心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講出了真話。對于生活的真相,容易看得清楚嗎?柏拉圖打了個比喻:世界類似于一個巖洞,我們躲在洞內窺探著外面,只能看到現實世界的各種陰影。看來,身在洞內,能看到的只是生活的投射,并不見得察得生活的真諦,正如俗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說,唯有外其身,或者后其身,才能觀其全貌。
對于生活,老子有他的觀察和思考。在老子看來,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其內在的規律,有一種力量推動著它們按其自身規律而存在、運動,這種原始的動力本身就是存在。這個存在,在天地之前就已經出現,只是人們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于是老子 “字之曰‘道”。
表面看來,老子講得輕松,但他確實看到了化生一切的本源。就是“道”這么簡單的一個字,卻是中華先賢圣哲們所言、所論的中心。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嗚呼在?曰:無乎不在!”(《莊子·天下》)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孫子兵法》)
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各家各派雖自有主張,但他們有著共同的認知基礎,這就是“道”。“道”仿佛是個秘籍,掌控著天、地、人的命運,掌握著宇宙萬物的運行法則。這個認知影響久遠,直到今天。
可以肯定的是,“道”是智慧與力量的源泉。知“道”,行“道”,帶給我們的是看清真相的能力、面對困難的勇氣、增強幸福的能力。這一切,正是和諧人生的主旋律。“道”,雖然說不清楚,卻也有跡可尋。
對于這一點,老子有他的發現。老子曰:
反者,道之動。(《道德經》第四十章)
在老子看來,“道”的運動是向著相反的方向變化和行進的。事物往往相互作用,事物的矛盾與對立轉化是永恒不變的。顯然,老子的認知,源于對自然界表象的觀察: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去;黃河、長江從西部發源,流向東部的海洋;冬天到來的時候,春天就不遠了;每一座山峰的鄰居,往往是幽深的峽谷。
從這樣的存在中,老子獲得了許多啟迪。萬物的未來,將走向它的反端。萬物現在的狀態,都由它的反端發展而來。所以,老子曰: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道德經》第二章)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第七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德經》第二十二章)
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道德經》第三十四章)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道德經》第三十九章)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德經》第四十一章)
萬物負陰而抱陽。(《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道德經》第六十三章)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經》第八十一章)
可見,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是整部《道德經》的主旋律。老子的“相反相成”與孔子的“成而必變”,說的是一樣的道理。道,乃反方向行進,這可以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對于和諧人生意義重大。
二、思遠志廣,原始察終
老子曰“反者,道之動”,修持大道的機會,老天是反著給的。所以,真正的福也往往通過反端的事件而生發。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第五十八章)人們理解的禍患、困苦,如果換個角度看,也許似是而非。這意味著,人們要提升境界,要有超越意識,站在更高、更遠處去思維。
要超越常理,莫若回到常理。比如,“有之以為利”(《老子》第十一章),這個道理天下人盡知。所以孔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里仁》)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富,與貧相反,代表物質上的享有,升官發財,貨利權色都在“富”的區間。貴,與賤相反,寓意精神上的追求。被人尊重、夸贊,享有美名,這都在“貴”的范疇。許多人一生的追求,盡在于此。若是夢想成真,在世人眼中,多是有福之人。
這種“福”從哪里來?當然需要個人的努力。但是,個人在哪些方面努力,怎樣才可以修得這樣的福報,才是更重要的。
按照儒家的邏輯,一個人有德,才會有“得”。
《樂記》云:德者,得也。
《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中庸》云: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先秦時期,道與德是兩個概念,有清晰的邊界。老子、孔子都談道與德的關系。老子曰:
道生之,德蓄之。((《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道,是生發的力量,化生一切。德,是長養的力量,承載萬物。孔子曰:
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語·王言解》)
孔子認為,因為有道在,所以德得到彰明。沒有道,德的好壞也就失去了標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既然有“明德”,就有與之相對的“惡行”。如何區分和界定“明德”與“惡行”?道就是標準。因為有德在,道得到了尊崇。
人們通常說:有德才有得,有誠才有成。如何做到有德?真誠修道者有德。所以老子曰: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經》第二十一章))
德,全然地遵從道。最大的德,就是順從道。道是何物?它恍恍惚惚,深遠幽冥,它的有無虛實難以辨識。但是,就在這恍惚之中、幽冥之際、有無之間,道彰顯出了一種意象,這種意象逐漸轉為具體的形物,包含著至精至誠的動力。它真切可見,真實可信。
《大學》有云: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道所彰顯的意象,就是誠意、正心。意象轉化為具體的形物,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其中,一股力量的泉流貫穿于終始,它時時涌動,永不停息,無處不在,無窮無盡。這一切,就是“道”的作用了。
道,竟有這般力量!于是,知道、修道、悟道、得道,成為歷代志士仁人畢生的追求。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士志于道”“謀道不謀食”。志士仁人就是為大道而生的。
道是如何發生的?老子曰:“反者,道之動”。道的運行是反方向行進。那么,道的發生,就不是簡單地像“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那般美好且讓人樂于接受了。修道的機會,往往以反端的事件生發。比如遇到困厄,面對災禍。假如能夠避免,沒有人愿意在困厄與災禍中飽嘗愁苦滋味。但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理性面對不如意,超越悲苦,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孔子的一生多經困厄。其中,“陳蔡絕糧”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孔子師徒在經過陳、蔡兩國之間時,被圍困而斷糧多日,外無所通。子路想不通,提出一個問題,因為他聽孔子講過:“為善者,天報之以福;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孔子師徒積德懷義,為什么還會淪落到“窮”的境地呢?他不解地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窮,是窮困,是困厄,也是窮途末路。孔子回答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
在孔子看來,同樣面對窮境,君子的選擇是理性認知,安然地對待,堅守底線。小人則如泛濫的洪水,無所不用其極。“小人喻于利”,給小人直接的利益好處,他是喜悅的。當修道的機會降臨的時候,他根本不認識道。因為不認識,自然就錯過。
古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中說:“生活中的幸運和災禍為善人和惡人所共有。”生活中的幸運與災禍也為君子與小人所共有,但這絕不意味著善人與惡人、君子與小人就是一回事。奧古斯丁認為,這就好比“同在火里,黃金閃光,而糠秕冒煙;同受連櫚敲打,秸草扁癟,而谷粒潔凈。”同樣力度的傷害,對善人是一種考驗、凈化和純潔,對惡人卻可能是遭殃、毀滅和根除。受到同樣傷害,惡人會咒罵、褻瀆上帝,而善人會求告和贊美上帝。所以,重要的區別不在于遭受什么苦難,而在于什么樣的人在受苦。同樣受攪動,污泥發出臭氣,香膏則滿是馨香。
苦難、困厄是試金石,真正的生命成長是在困苦之中成就的。在困厄中,人的心志與追求開始萌發。這時候,孔子特別強調人應該思遠志廣,知事物之終始。孔子曰:
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孔子家語·在厄》)
人居下而憂、處身不逸,則思遠志廣。如果了解事物的發展規律,明白事物的相反相成,就是真正的知事物之終始。晉文公重耳稱霸的雄心,萌生在他逃亡于曹、衛兩國的時候;越王勾踐稱霸的雄心,萌生在他被困于會稽的時候。所以,身居下位而無憂者,思慮不遠;生活長期安逸的人,其志不廣。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司馬遷就列舉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陳、蔡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賦《離騷》;左丘失明,編有《國語》;孫子被截去膝蓋骨,《兵法》修列;呂不韋流放蜀地,代代相傳《呂氏春秋》;韓非被囚于秦,作《說難》《孤憤》。這皆為發憤之作。(《史記·太史公自序》)對于有修為的君子來講,正向的擔當是修德,反向的承負是修道。修道,是真正的固本培元,是長根的功夫。故老子云:“根深蒂固,此乃長生久視之道也。”(《道德經》第五十九章)
有了心志與追求,還需要錘煉擔當與勝任的能力。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擔當大任者,確實要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智慧與力量,這是道在生發。這個過程中,苦、勞、餓、空變成了催化劑,是對一個人心智成熟的歷練。
三、洞明天道,調其盈虛
老子在論及“反者,道之動”之后,接著論述到:“弱者,道之用”。老子告誡人們,“道”的運用,要我們保持柔弱的狀態。
道,反方向運行;真正的福氣,老天是反著給的。人生要經歷困厄,要面對困難,必然面對吃虧、吃苦。如果把吃苦、吃虧的“好處”明白透徹,苦就不苦,吃虧是福。這不是失意人生的最后慰藉,而是對于真理的真切洞察。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一個自由人的崇拜》中說,當不幸降臨的時候,我們要有勇氣去忍受,而不要抱怨希望的破滅,要有勇氣從徒勞無益的悔恨中解脫出來。這種對崇高信仰的順服,不僅正當而且正確,它正是智慧之門。這個“智慧之門”正是中國哲學家所說的“入道之門”。禪宗六祖慧能講他自己的經歷,也說辛苦受盡,命似懸絲,經歷累劫,終得正果。
面對大是大非,在動蕩飄搖之中,弦歌鼓瑟,靜定如一,這不是傳說,也不只在孔子身上才發生。如果做到如此,就能遠離憤怒、怨恨和煩惱,取而代之的是“定”“靜”“安”“慮”“得”。《大學》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人洞明天道,才能做到真正的淡定,才知道應該“止”于何處。
那么,該止于何處呢?止于大道。這就需要洞明、知悉大道。對于辛苦乃至劫難,正確、理性的態度不是抗拒,而是坦然地面對和接受,這與佛家《六祖壇經》慧能所言“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便異曲同工了。這還是源于道的運行規律,“反者,道之動”。智慧由煩惱而生,如何面對、化解煩惱,體現了人的智慧。沒有煩惱,也許就沒有智慧可言。懂得這個道理,并不是要主動找虧吃,找難受。否則,就走向了反端。
據說,蘇格拉底在被處死前留下了一段話:“時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是活在這個世上好,還是去另外一個世界更好,只有神知道答案。”這當然不是鼓勵人們要加速走向另外一個世界。對于一般人,未知、消亡、挫折、失敗總是最壞的事情。但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有結束,才會有新的開始。這樣思維,也許就不會對失敗、消亡等產生恐懼。在很多情況下,恐懼與憂患源于對結果的未知。但結果往往不是一個固定的點,更不是終點。或者講,它只是一個階段的終點,卻是另外一個階段的起點。
在談到“損益”之道時,孔子曰: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
我們很難見到自滿卻能長久的人,就像一個人趾高氣揚,他就難以聽進善言。通過對比帝堯與夏桀,這個道理更加清晰。誠信恭敬待人,用謙讓的態度對待臣下,就有千百年的名聲;如果自滿妄為,不加節制,斬殺百姓如同割草,天下人討伐他們就如同誅殺獨夫民賊。依此來看,尊敬長者,禮賢下士,調節盈滿和虛空,不讓自滿情緒發生,才能保持長久。
能夠“調其盈虛”,是明白大道的表現。既然修持大道的機會是反著的,那么就不用懼怕困厄、禍患的錘煉。禍可以轉化為福,明白了這些,進而早早行動,才可以更好地避禍趨福,因為道還是按照它固有的規律運行,它“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循環往復,永不停息。
怎樣“調其盈虛”?面對功勞、名利、富貴,人們都希望滿而不溢,都希望沒有被傾覆的危險。事實上,滿就會溢,功成名就、志滿意得時,往往就像處于“危樓高百尺”之地。這時,又應該做些什么呢?
孔子與弟子們在魯桓公廟看到一座欹器,被稱為“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之于坐側。”水少的時候就傾斜,注水適中的時候正好中正,滿了就立即傾覆。明君常常以此為戒,將它放于座位旁邊。
孔子深深嘆息:“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請教:“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家語·三恕》)
所謂“持滿”,就是既能保持盈滿,又不至于傾覆。怎樣做到呢?孔子認為,聰明智慧,就用愚笨來持守;功勛卓著,就用辭讓來持守;勇力聞達,就用怯懦來持守;富有四海,就用謙和來持守。所謂損之又損,實乃愚、讓、怯、謙之意。真正的持盈之道,是要守住“有”;而守住“有”,則離不開“損”。有功、有名,不意味著功不去、名不離。
這樣的道理,老子也有他的觀察與闡發。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道德經》第九章)
持守盈滿,不如適可而止。孔子師徒所見宥坐之器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證明。愈是銳利的鋒芒,愈是不可長保。金玉滿堂,卻不能自守。所以《道德經》第九章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之時,志得意滿,需要調節,不居功自傲,就是持守自謙之道。
其實,在天地之間,最有功者莫過于天、地、日、月。可是,“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孔子家語·論禮》)天、地的做法是: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生育、長養、滋潤,生長并不占有,做了并不仗恃,長養并不宰制。老子稱之為“玄德”。這是潛蓄而不著于外的德性,自然無為,可稱為“天德”。孔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天從來都不說什么,但春作、夏長、秋斂、冬藏,萬物受其潤澤。這源于“天”的無私、無功、無言,反而成就了天長地久。所以,老子曰:
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經》第六十三章)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德經》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道德經》第七十三章)
在老子看來,“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余食贅形。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道德經》第二十四章)惦著腳尖,會站不穩;跨步前行,終不長久;自我表現者,反而不明達;自以為是者,反而得不到彰顯;自我夸耀者,實在是無功;驕傲自滿者,反而沒有得到生長。這些情況,對于道來講,就像是殘羹剩飯,讓人厭惡,有道之士不做這些事。所以: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道德經》第七十二章)
自知與自見、自愛與自貴,其實就在一念之間,有時也相距十萬八千里。關于這些道理,老子問:“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心如明鏡,能不能執守空無,靜定如一?生命不能空度,但要有留白。在空靈之美中,才有無限的遐想。所謂的可能性、希望和夢想,盡在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談論“滿而不溢”,談論關于“損”的話題,一定在“有”的前提下。有什么?有天下之人向往的物與事,如聰明睿智、功被天下、勇力振世、富有四海等。若本來就一無所有,空無一物,沒有什么可“滿”之處,“損”又從何談起呢?先有聰明睿智,才有守之以愚。
在這里,“愚”并非“愚蠢”,而是明白四達卻不自以為是。功被天下才有守之以讓,有勇力振世才有守之以怯,先富有四海才有守之以謙。當沒有“有”的時候,一定要昂揚向上,努力進取,這才是正道。
那么,如何才能“有”?老子曰: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何時為,何時不為?何時益,何時損?無有要生有,滿時就要損。貴在身處一端,知其反端。在老子看來,要做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 《道德經》第二十八章)。說到底,雄、雌,白、黑,榮、辱,都是生活的不同狀態。對于生活,每個生命都應有理性認知。靜定、安于,是人生和諧的最佳狀態。不患得患失,也不得意忘形,不失意絕望。
四、素位而行,不愿其外
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之“反”,與“返”通用。返,就是歸返生命本來的歷程。
面對現實的生活,如何安頓自己的生命與本心?基督教普及的道理,是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更忠誠于上帝。蘇格拉底則認為人們更應該服從于神。老子、孔子等中國的先哲認為,相對于功名利祿這些現實中的“有”,人們更應該信任化生這一切的“道”。
道的特質是什么?老子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慨。(《道德經》第三十五章)
悅耳的音樂,可口的美食,對于過客來講極具吸引力。道之出口,卻如一杯白開水平淡無味,或者連白開水也不如,看它看不見,聽它聽不到,但是用起來卻永不衰竭。也就是講,無論是否“天下有道”,大道都在那里,如如不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它好像無影無蹤,其實有跡可循。
既然“反者,道之動”,那么在歸返生命本來的歷程時,微不足道的事物卻可能是至為重要的。比如,孔子強調為人處世的道理與禮節,“弟子入則孝,出則悌”之類,人人能知能行,就在舉手投足中,在視聽言說間。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往往是道的至高表達。
老子曰:“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眾人皆有余”“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春日里,桃花開,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奔往功名利祿,去爭難得之貨。在利益紛爭處,總是熱鬧得很,許多小丑,粉墨登場。于是,就有了花言巧語,有了功于算計,有了精明省察,也有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對于這些,孔子的態度十分明確:恥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
花言巧語的人鮮有仁愛之心,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要么是欲速成者,要么是貪小利者。對于這些,老子同樣痛恨不已。他自問自答,引發人們的警醒:
名與身孰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道德經》第四十四章)
名譽與生命,何者可愛?生命與財貨,何者貴重?獲得與失去,何者有害?過分的貪愛必造成更大的耗費,更多的私藏必造成更重的損失。所以,知其所足,不受侮辱;知其所止,無有危險。如此,便能長久存在。
這樣做,與“自以為是”多有不同。竭心盡力去追逐愛與財富,反而會帶來耗費與損失。所以,老子的選擇不是追逐,而是讓它發生。他看到天下萬物有這樣的表現: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經》第二十九章)
它們有的走在前,有的隨在后;有時噓氣取暖,有時吹氣為涼;有的身強力健,有的骨弱筋柔;有的厚實堪載,有的頹廢傾塌。無論如何,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所以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接受自然天成,勝過自以為是。這包括接受他人,也包括接受自己。也就是講,自己若是先進,要接受后進存在,并不飛揚跋扈。先進者所擁有的力量不是要時時憤懥,而是幫助他人,化解憂患,消除恐懼。若自己是后行者,貴在安分守己,不是不努力,而是不投機取巧,不坑蒙拐騙。所以,圣人的表現是“去”,去掉極端,去掉奢侈,去掉過分。
《論語》中亦有同樣的表達: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不憑空猜測,不絕對肯定,不固執不化,不自以為是。佛家倡導“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與之一致。那些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固執己見,乃源于一份“我執”、一份私臆、一份偏見、一份由固執而產生的執滯和郁結。
那個“我”很重要,此道理世人盡知。可是,“我”也是最大的障礙,天下人卻知之者少。“我要”“固執”“執守”本身并沒有過,如“擇善而固執”就是“誠”,就需要這樣的一念恒定。不過,怕的是這一念落腳在私己、私意與私利。如果落腳在“私”,空間就會不停地內縮,直至縮成一條夾縫,小到連自己也放不下。反之,若杜絕了“甚”“奢”“泰”,去除了“意”“必”“固”“我”,無有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同是一念恒定,信心清靜,立足于天地正道、人心公理,空間將不停地放大、外擴。還是那個夾縫,卻可以大到與天地同在。這個空間不在外,而在內。
要實現身存,需要抽身其外;要實現身先,需要靜守其后;要成就自我,需要全然的無私。如此這般,無我,成就了大我;無私,反而成其私;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有他的選擇:“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道德經》第二十章)“貴食母”,就是歸返生命本來的歷程,回復生命本來的模樣。體察虛靈的本心,信守寧靜的元神,才可回歸生命本源。老子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兇。(《道德經》第十六章)
萬物如如自然地生長,紛紜交錯,卻又井然有序。它們各自回到生命本源。如同樹根滋養著枝葉花果,但葉落歸根,再次潤養樹根。歸根是自然的表現,是靜定的舉止,是生活的回復,是生命的歸返。這是常,是常識,是常理。縱然是斗轉星移,時光變遷,真正的常如如不動,是永恒。老子提醒人們要知常,如果“不知常,妄作”,就一個字“兇”。
生命回復的軌跡,就是道的運行軌跡。按照這個軌跡,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是: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
天清、地寧、神靈、五谷豐盈、萬物欣欣向榮、侯王成為天下人的示范與導向。當侯王成為天下人的示范與導向,人間的秩序就有了定位。《大學》云:
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國人相交有信。這些道理甚易知,但又甚難行。難行在于“比較心”的生發。“若是我對他人有禮,可是他人對我無禮怎么辦?若是我對他人忠心,他人對我不忠怎么辦”?老子認為這是“中士”的行為,他們半信半疑: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道德經》第四十一章)
事實上,道,周流不殆,永遠都在起作用。它運行的軌跡是“反者,道之動”,反方向運行。《心經》有云:“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只有全然的付出,付出的全然,才可真正無掛礙。宋代大儒朱熹在其《論語集注》中曰:“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功是工夫,功是功勞。不計較付出所有的工夫,不在意是否有功勞,品德天天提升,就在不知不覺中。這樣的過程,就是修道了。
在現實生活中,人如果對“付出”與“得到”功于算計,在財福與地位方面患得患失,將“希望”和“害怕”都集中于自我,是不會鎮定自若地看待富與貴、貧與賤的,也很難有真正的超越。老子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道德經》第十三章)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很多人向往,求之不得。可老子為什么這么說呢?當有所得成為一個人的幸福源泉時,他面對“失”的時候,還能全然承擔和接受嗎?當富與貴、貧與賤的境況變化時,寵辱若驚的人往往會被摧毀。然而,看清真相寵辱不驚的人,對于自我有著真正覺知的人,會來者不拒,過往不咎,會有真正的超越。這種超越不是虛空,是真切的現實,是真實的存在。因覺知而超越,這是生活對于行道者的最佳回報。
于是,就有了《中庸》所云: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安然接受生活賦予生命的一切。是福、是禍,非福、非禍。擔得起,將得到真正的超越,品享真正的人生和諧。當生命的琴弦被調撥和諧時,上天的每一次碰觸,都可以奏出歡悅的人生樂章。
[參考文獻]
楊朝明.子夏及其傳經之學考論[M].孔子研究,2002(5):28-38.
[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