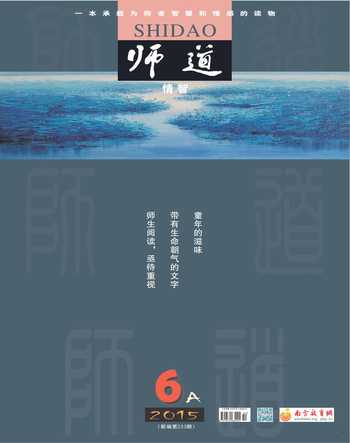慷慨凄涼:一種教育擔當者的決然姿態
初心
在當前的中國語境下,支配著我們教育生活的是行政主導的一種垂直式的管理,一位普通教師真實的教育處境很難為社會各界所知曉,他所面臨的種種困惑和糾結更難以“為外人道”。對于曾經擁抱教育理想、至今仍在堅守教育良知的教師來說,我們總是一方面希望自己從事的教育是質樸、善良、富有審美情趣的;另一方面又深感這些當然的教育追求在現實的評價尺度下微不足道,分數才是師生的硬道理。盡管辯才們常說“教學的人性化和高質量(高分數)是不矛盾的,真正地‘人性了了,‘高質量(高分數)也一定會水到渠成的”,但講大道理是一回事,從事具體教育工作的教師的感受是另一回事。我們會感到一種撕裂般的痛楚,覺得“上帝救不了你的牙疼”(舍斯托夫語),整個社會成了一種異己的、刁蠻的存在。
比如,面對一個學習落后的孩子,他落后的程度讓我們壓根就不會自欺欺人地指望他迎頭趕上甚至是后來居上,但是憑著“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孩子”“盡可能多地關愛后進生”的教育良知,我們仍會一如既往對他施以耐心、愛心和智慧,讓他有所進步,至少是感受到人性的溫暖,并在和老師、同伴的和諧交往過程中學會做人。但是形勢不饒人,我們可以堅持一天、兩天,甚至是一個月、兩個月……但我們很難“積一時之跬步,臻萬里之遙程”,始終如一地關注他、成全他。因為,我們有限的精力投入還得“面向全體”——這既是“大面積提高教學質量”的需要,也是自身利益權衡的結果。盯住后進生“死揪”,看不到“成績”,周圍同事不理解,學生家長不支持,甚至校長也予以指責,這種四面楚歌的境地何以長繼?
明明是對的,卻很難堅持;一旦堅持,必有所失。做教育到了這個份上,不僅要吃得起苦,還要吃得起虧,教師成了“寂寞的圣賢”,其心境大約只可以用“慷慨凄涼”來形容了。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借用電影《少林寺》中執儀法師的頌語自問一下:汝今能持否?
不言而喻,再難也得堅持——這樣的回答是一種明知難為而為之的決然姿態。教育改革難就難在,全社會的人都認為自己懂教育,每個人都跟教育有關系,他們對他們看不慣或影響其眼前利益的做法都要攻訐,很難形成共識。這種情況下,教師的鐵肩擔當就成了維護教育公義的最后和最有力的屏障,一顆樸素而真實的教育良心永遠是師義所在、師魂所系。只盯著事關升學率的一些數據,從來不關心孩子的個性精神,培養的永遠都是缺乏心靈自由、喪失主體人格、不會獨立思考、消泯創造精神的格式化的人。如果放棄了堅守,我們的教育信念何在?教育責任感何在?放任教育的淪落,于社會責任而言,是一種失職;于自身的人格建構而言,是一種自棄。教育的健康發展與我們每一位教師都有關。經驗告訴我們,沉默只會使教育進一步異化,不作為的“好教師”集體無意識式的作壁上觀甚至推波助瀾其實正是教育“跑偏”的主因。治理教育的“PM2.5”,讓置身其中的教師清清爽爽、本分從教,不用被迫呼吸“教育霧霾”,最需要的是來自教師自身的抗爭精神,我們不能因為體制的原因而逃避作為教師應負的責任和社會道義。
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一直強調:“教育須有信仰,沒有信仰就不成其為教育,而只是教學的技術而己。”一位教師任何時候都不該湮滅自己對真正教育目的的認同。有人把當今教師的困境比作“戴著鐐銬跳舞”,其實鐐銬之舞是為了明天鐐銬的消失——鐐銬終究會在“舞”中瓦解。我們既然已經戴著鐐銬跳舞了,那就不妨偉岸一些,奮力一些,要讓我們的精神多照耀那些需要光芒的人。我們的努力盡管目前還不能得到外界甚至是周圍的認可,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人的精神追求層次的提高,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并會引領人們的心智前行的。“真正偉大的思想者,就像雄鷹一樣,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獨的高處。”這是叔本華說的話。叔本華的精神時空深邃曠遠,一般人難以企及,但是他孤獨寂寞了一生,他很少朋友,他忍受著身邊人包括母親對他的漠視、嫉妒和詆毀,到了晚年,人們才發現這個有些古怪的老人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價值,是人類的瑰寶,所有的榮譽都伴隨著時代對他的慷慨接納紛至沓來……教育是面向年輕一代的“時不我待”的事業,盡管教育體制需要變革,但是我們絕不希望看到等到教育體制的變革已經完成得比較完滿的時候,我們的一代乃至幾代人已經被畸形的教育戕害了,這是無法挽回的損失。所以,如今的教師未必需要“超世之才”,但不可或缺“堅忍不拔之志”。我們可以持之以恒地批評現行教育制度不人道、不合理的地方,以便促進它的變革,但是另一方面尤其需要當仁不讓地堅守自己的原則,聽命于內心理性的召喚。稍微留意一下那些最優秀的教師,他們無一不帶有那種凄清孤離的情緒,彌漫在他們靈魂深處的是纏綿的哀愁和感傷,對教育、對人性執著的質疑與反思,還有那“我看透了這個世界,但我仍然熱愛它(羅曼·羅蘭語)”的孤寂無比的深沉感悟……他們迷戀工作,篤信“教師”稱號所對應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在奉獻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智慧后,體驗到了一種道德升化的慷慨凄涼的滿足。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經撰文指出,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大學如此,中小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很多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的所謂“成功教師”不就是長袖善舞、善于“經營”“過五關斬六將”而得以成就的么?現在的很多教師培訓、名師培養機制,說到底無非就是在教我們如何更加老道地去適應并滿足那些匪夷所思的條條框框的要求,目標直指那些含金量或高或低的招牌,有多少講座是真正靜下心來去探討教育文化、宣揚教育真諦的?一些原本樸實、本分的青年教師在喝了這樣的“心靈雞湯”并功成名就之后,精氣神是有了,但教師的味兒淡了,撥開那些之乎者也的修飾詞,說來說去他們的教育理想就是出人頭地。為此,他會不惜傷害自己的同事并違背教育規律進而傷害自己的學生。這樣的罌粟花一樣的教師無論有多少又有什么用呢?
一個真切地看清世界、熱愛教育、勇于擔當的教師,不應當對世俗的認同和贊美抱有過高的期望,不要奢求那些偏離正義的無聊的名望、地位,有時候我們需要忍受、享受一個人在廣漠的世界上獨自行走的孤獨,并在此過程中證悟自己的內心,確認自己的存在。這是真實的魅力,也是最美的人生。人的價值在于心靈的豐富,那種美到致極的夢幻般彌漫心靈的凄美,并不是每一個教師都有資格感受的,它需要我們卷入教育的現實,并不曾回避自己的責任,勇敢地堅守自己的內心。
作為一名教育的理想主義者,我們需要一種迎風而立的人生性格,我們需要“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我們須臾離不開自己設定的“優秀教師”的悲壯夢想。“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許只有在孤高的靈魂不斷地打量教育時,只有在心靈之弦無數次地細微顫動之后,我們才會感受到一種真正的生之歡樂。“上帝救不了你的牙疼”,但是我們最終會藐視自己的“牙疼”,并由此擁有不一樣的教育人生。
(作者單位:江蘇新沂市教育局)
責任編輯 鄒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