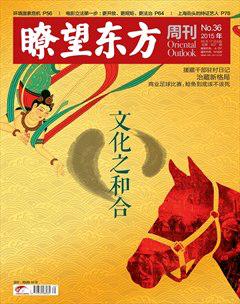歐洲語言:冷熱悲喜60年
王斯璇

1979年11月6日,在法國貢比涅工藝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在老師指導下攻讀法語
1997年初夏,張志鵬陪同來華訪問的羅馬尼亞新聞代表團。一天,羅馬尼亞廣播電臺時政部副主編納丘先生突然問他:“當初為什么要選擇羅馬尼亞語作為自己的專業?”
張志鵬一愣:“不是我自己選擇的,是領導決定的。”
作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羅馬尼亞語專業教授,他說,當年那種緣由,今天的年輕人恐怕難以理解。
如今,可能因為迷上電影《天使愛美麗》的某個浪漫細節,或是只因想讀懂原版《小王子》中的某一句話,中國的年輕人就會選擇學習法語。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丁超看來,對于中歐人文交流而言,“語言的交流是‘大交流,涵蓋很廣,而歐洲語言人才的培養,是讓交流更主動的關鍵。”
“光榮的開拓者”
1953年,武漢大學中文系,易麗君讀大一。在圖書館翻書時,偶然發現了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這個名字,繼“肖邦”、“居里夫人”之后,成為“波蘭”在她腦海中的第三個標簽。
一年后,她通過層層政審,以及“一大套留學考試”,從50名候選人中被選中,成為1954年中國赴東歐的17名留學生之一。
這是中國派往東歐的第四批留學生。
1949年10月1日起的一周之內,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緊隨蘇聯之后,與新中國建交。
1950年,周恩來曾給羅馬尼亞總理寫信,提出雙方互派5名青年學習對方的語言。同年9月,中國政府向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兄弟國家各派5人,學習語言、文學、歷史,以應外交工作之急需。
留學生們一度甚至都不被要求拿到文憑,“學三年,趕緊回來當翻譯。”易麗君說。
那時,國家急需大批通曉外語、特別是東歐語種的人才。派遣留學生的同時,教育部決定在國內籌備東歐語種的教學。
1954年,波蘭語和捷克語專業首先建在北京大學俄文系。因時間倉促,招生時甚至未向考生事先說明。
新生大會上,系主任曹靖華宣布,北大俄文系接受國家交付的光榮任務,在100名新生中挑選40人,分配到波蘭語和捷克語兩個專業。“你們將是光榮的開拓者!”
與外交同冷熱
那時,歐洲語言中使用人數較多的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已在中國高校開授。
在國家扶持下,上世紀60年代初,隨著匈牙利語、保加利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瑞典語等專業的增設,以東歐語種為主體的歐洲非通用語種群形成。
“很多國家對此都很重視。”丁超說,“這些國家都不大,民族語言是他們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軍事、宗教的碰撞沖突之中,能夠始終保持民族身份的中流砥柱。”
1956年羅馬尼亞語在北外開設之初,羅馬尼亞就給中國贈送書籍刊物,甚至每周都寄來報紙、雜志,外派的專家也很優秀,比如60年代赴華教書的羅馬尼亞專家楊·弗拉德,是著名的詩人、作家、文學評論家。
當時,中國在東歐國家傳播漢語也不遺余力:1952年,中國赴保加利亞教授漢語的第一任教師,是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語言學家朱德熙。
“當年歐洲語言在中國的推廣,與國家外交有很大關聯。”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副主任戴冬梅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60年代,中國進入第二輪外交建交高潮,特別是1964年與法國建交,推動了各大院校法語專業的招生熱——僅北外一校,1963年、1964年每年招收人數都有120人,全系總人數高達450人。
“我們系到現在本科生加上研究生才400多人。”戴冬梅說。
隨著中蘇交惡,中國和東歐國家關系轉冷,繼而進入“文革”,到70年代初,“除了招過一兩屆工農兵學員,很多專業甚至停止招生。”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院長趙剛說。
報春的燕子
第一位專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關呈遠,就是1964年法語大熱時的新生。
“在北外學了8年。”他向本刊記者回憶,“文革”中學校停課,1969年全校遷往湖北沙洋,“周恩來總理指示,這些學生還是要留下來,繼續學習,以后還會有用。”
全體師生上午教學,下午勞動,種菜,養豬養雞,挑磚,蓋房子。
一年半后,北外回京,學生回爐。1972年畢業分配,他們中有四分之一從事外交工作,不少人成為高級外交官,“讓中國在重返對歐關系發展軌道時,有了人才保障。”關呈遠說。
就是在沙洋七里湖農場蘆葦搭起的毛棚子里,青年教師易麗君有機會翻譯“周總理很關心的一本書”。
那是波蘭戲劇史上的經典之作——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1968年在華沙上演時場場爆滿,臺上臺下同聲誦讀。“活得不好最好當奴隸,不當奴隸最好當叛徒”,“大把斧頭砍沙皇”,這樣的臺詞引來掌聲雷動。
觀劇的蘇聯駐波蘭大使憤而離席,蘇聯官方下令禁演,波蘭華沙大學學生繼而發起了保衛《先人祭》演出的示威游行,引發一場政治事件。
“周總理納悶,一本書能引起這么大的社會騷動?”易麗君說,“那時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有風險,而我是無名小卒,不怕。”
7年后的1976年,《先人祭》終于出版,并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演播,名噪一時。

2013年10月17日, 英國倫敦中醫孔子學院和倫敦南岸大學學生會在南岸大學聯合舉行中國文化展示活動,向當地學生介紹和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圖為倫敦薩瑟克市副市長馬克·貝內特參加武術活動
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評價說,在那個時代,對于歐洲乃至世界語言、文學在中國的處境而言,“這是一只報春的燕子,是一朵報春花!”
1977年,恢復高考,英語教育立即成為急需。據統計,1983年,全國外語專業在校學生6萬人,其中英語專業達5萬人。
從1977年始,德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捷克語、匈牙利語、保加利亞語相繼恢復招生。北外的波、捷、匈、保四語專業甚至在1985年到1987年,就實現了全班赴對象國的“交叉辦學”。
丁超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公派出國留學很不容易,國家財力尚緊,許多骨干教師尚無出國進修機會,全班出國學習,被視為“破天荒的支持”。
小語種不是大熊貓
1989年,車琳考入北外法語系。“我們那一代,可能受了都德的影響——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如今已是北外法語系主任的她笑言。
這一年,致力于傳播法國語言的非營利性組織法語聯盟重返中國。
這個機構始創于1883年,次年便進入中國。50年代轉駐香港辦學。1989年,借改革開放、法語漸熱之機,法語聯盟重回中國內地,以合作辦學的方式推廣法語。
學生時代,車琳曾在北京第一家法語聯盟機構上過一年課,“就在故宮東華門”。
那時,中國的國際交往漸多,到法語聯盟接受培訓的人各色各樣,有想要留學法國的,有外企白領,還有外派工作者。
“對他們而言,中國市場大到什么程度?”戴冬梅說,世界各地的法語聯盟,每年都有因經營不下去而關閉的,法國一直在削減對外文化傳播預算,而“中國的法語聯盟卻可以自負盈虧”。
“歐洲每個語種的發展,和國家實力有很大關系。”易麗君說。
同在1989年,東歐劇變,東歐語言的處境著實困窘。
比如,詞典出版異常艱難。90年代初,羅馬尼亞語教授馮志臣等開始編纂《羅漢詞典》,沒有出版經費,張志鵬想到向羅馬尼亞人開辦的公司拉贊助。最終,一本嚴肅工具書中夾著一張活頁廣告,而前言里還特別提到這家羅馬尼亞公司的電話、地址。
90年代,歐洲語種在中國已開設14種。除了歷來熱門的幾個,其他普遍唱衰。甚至有人說:“小語種不要辦了,有英文就夠了。”這種聲音一直持續到2000年前后。
“這不只是一個國家的語言能力,更關乎國家安全,包括塑造國家形象。美國、俄羅斯都非常重視這個方面。”趙剛覺得,跟一個國家交往,都沒有懂這個國家的人,怎么行?
小語種干部得天獨厚的優勢在于:能夠很快地與當地民眾結下深厚友誼。“就算一個國家英語普及程度很高,但你跟他說當地語言,會立刻產生親近感,很容易交朋友,能夠很快熟悉當地的情況。”
“小語種絕對不是要被‘養起來的大熊貓。”易麗君說。
尊重與重視是相互的
2001年,轉機出現——教育部下發通知,在全國部分高校設立“國家外語非通用語種本科人才培養基地”。
這個時期,中歐關系迅猛升溫。1998年,中國與歐盟共同商定建立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關系。2003年,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2004年,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中國也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
“外交關系的強化,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企業走出去的需要,歐洲非通用語重新受到重視,英語可以替代一切的偏見也慢慢息聲。”趙剛說。
歐盟一直推行全面、包容的多語制政策,民族國家堅持推行某一種官方語言,被視作理所當然。
目前歐盟有28個成員國,24種官方語言,是世界上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最多的國際組織。一個數據是,2006年歐盟的行政開支中,有近10億歐元用于口筆譯及其他相關服務。
自2002年始,芬蘭語、丹麥語、希臘語等13種歐盟官方語言在中國高校開設,到2009年,馬耳他語在北外設立,歐盟官方語言在中國全部開齊。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是全世界開設歐洲非通用語最為齊全的院校之一。
“這種學科布局可以發揮集群優勢。”趙剛告訴本刊記者,中東歐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區域。
在文化交流中,尊重與重視是相互的。
2007年,荷蘭著名的冰島語學者帕烏拉·費爾梅登逝世,此時北外正好新設立冰島語專業,其冰島語藏書近2500冊悉數捐贈北外。冰島政府也捐贈了近1500冊藏書。
“冰島人口不過30萬。”丁超說,“我和青年教師開玩笑,這些書你們一輩子都讀不完。”
“歐洲國家非常重視自己的語言、文化推廣。”趙剛說,波蘭圖書協會有外國譯者資助項目,“你想翻譯什么書都可以申請。”
易麗君多年從事波蘭文學譯介,波蘭兩任總統曾親自為她頒獎授勛。
國家的扶持,對語言、文化傳播尤其重要。
2012年,孔子學院總部啟動“孔子新漢學計劃”,提出中外合作培養博士、來華攻讀博士學位、“理解中國”訪問學者、青年領袖、國際會議、出版資助6個項目。
之前在與歐洲漢學家交流時,孔子學院總部副總干事王永利發現,西方國家紛紛削減教育經費,對漢學的支持力度明顯下滑,學科趨于邊緣化。“各國政府高層與中國接觸增多,急需智囊支持,但傳統漢學家大多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問題發言有限。”
“孔子新漢學計劃”由此而生,鼓勵海外青年中國研究學人來華訪學研修。“要貼近當下,對當代社會產生更積極的影響。”王永利認為,培養未來的漢學家,發現當代中國至關重要。
“實際上,我們對歐洲非通用語言堅持不懈,也是出自全球化背景下,相互深度了解的需要。”丁超說。
他覺得,如今的外交需要達到雙邊交流最高級別的反應能力,為此急需高級別翻譯人才。
在重視文化多元化的歐洲,對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的重視深入骨髓。“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對各民族優秀文化的真心了解與學習,有些可能受眾不多,但咱們這么大的國家,總要有人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