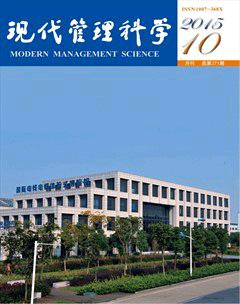中國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研究
殷金朋 賈占標 袁埜
摘要:文章運用SVAR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1981年~2013年間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私人投資以及通貨膨脹的效應,以考察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問題。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現存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和私人投資存在短期與長期的“倒U型”負向效應,在中期則表現為“單峰型”的正向沖擊;國債規模已經成為解釋經濟增長、私人投資及通脹變動的主要因素。總體而言,中國現存國債規模不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征。
關鍵詞:國債規模;可持續發展;SVAR模型
一、 引言
中國自1981年重啟發行國債以來,國債規模大幅增加,發行規模從期初的147.81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16 949.32億元,國債累計余額2013年達到86 750.46億元;與此同時,雖然赤字率、國債負擔率、居民應債率等國際常規指標顯示規模水平正常,但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在2007年高達46.48%,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安全限值20%。國債規模的迅猛擴張態勢引起了學術界對當前國債規模風險及可持續性發展等問題的普遍關注。因此,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嘗試構建有別于常規國際指標體系的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以期對中國國債規模的可持續發展進行實證分析。
二、 文獻回顧與述評
當前國際上有關國債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主要遵循的研究范式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常規國際指標體系,即以特定的債務可持續發展指標上限作為標準,并認為滿足標準的國債規模是可持續的(Reinhart et al.,2010;Cristina & Rother,2012);二是以政府預算約束為條件推導國債可持續性數理方程(Niklas & Markus,2012;Saeid Mahdavi,2014);三是基于國債對宏觀經濟影響視角,將國債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擠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等定義為國債政策的經濟約束,指出若擠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明顯,則國債規模不可持續;反之,其是可持續的(Lucian,2011;Atish et al.,2013);四是基于家庭層面的微觀視角研究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Chalk,2000;Agenor & Yilmaz,2011)。
國內學者在20世紀初主要依據第一種研究思路,且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國債規模存在應債能力寬松而依存度較高的矛盾(劉溶滄和夏杰長,1998;賈康和趙全厚,2000; 周佰成等,2002)。近年來學者多以滿足非蓬齊博弈條件(No-Ponzi-Game)作為檢驗標準,從政府預算約束著手研究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胡紹雨和申曙光,2013;王亞芬,2013)。隨著市場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完善,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私人投資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越發受到重視,諸多學者依從第三種研究范式對國債規模可持續性問題展開了探討。劉立峰(2001)、洪源和陳英(2005)認為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取決于相對規模的變化,同時還應考察對經濟增長、民間投資等的影響。馬拴友等(2006)利用月度VAR模型指出國債對實際利率和通脹作用微弱。王玉華和劉貝貝(2009)通過VAR模型分析顯示,國債規模對居民消費有正的引導作用,但存在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楊子暉(2011)研究表明公共債務的增加通過影響未來稅負預期,使兩者互補性減弱,減少當期消費。王亞芬(2012)利用SVAR方法研究了公共資本對私人資本和產出的動態影響,認為中國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具有先擠入后擠出的效應,且產出對公共投資的沖擊更為敏感。
綜合文獻可知,學者對于國債規模可持續性發展問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各異。國外學者對于國債規模的研究比較充分,多注重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應用。國內學者研究多局限于常規國際指標體系的靜態分析,或是利用協整檢驗等工具考察國債規模對宏觀經濟某一方面的影響,采用動態計量工具綜合分析國債規模可持續性發展的較少。作為一種橫向比較方法,各指標特性及敏感程度在不同研究中的不同引發了學者的質疑,其限值的劃分也存在較大爭議(朱柏銘和徐利君,2001)。近年來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方法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財政政策沖擊效應的標準方法之一,因此也是分析國債規模對宏觀經濟運行動態影響的較好工具。鑒于此,本文基于國債規模對宏觀經濟的動態影響視角,研究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擠出效應及通貨膨脹效應的影響,構建國債規模、產出、民間投資以及通貨膨脹四變量的SVAR模型,以期研究中國當前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問題。
三、 研究設計
1.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本文實證研究以1981年~2013年為樣本空間,選取了國債規模(積累余額,BS)、產出(GDP)、私人投資(PI)和通貨膨脹(CPI)四個系統變量。由于私人投資無官方數據,本文采用楚爾鳴和魯旭(2008)的處理方法,從資金來源入手,將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作為政府投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減去國家預算內投資得到私人投資。由于通貨膨脹率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聯系最為密切,因此本文用CPI替代通貨膨脹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4)、《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2000-2014)、國家統計局網站、財政部網站和中經網等。其中1981年~1984年間CPI缺失,采用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予以替代。為了減少數據非線性的干擾,文中對系統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2. 模型構建。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由Blanchard和Quah(1989)在非約束性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基礎上提出,依據變量的協方差矩陣和相關經濟理論施加相應的約束條件,得到結構脈沖響應函數,進而分析變量對經濟系統的動態響應。根據需要,本文構建的四變量SVAR模型如下:
A0yt=f(lnBS,lnGDP,lnPI,lnCPI)
=?鬃0+?鬃1yt-1+?鬃2yt-2+?鬃3yt-3+?濁t,t=1,2,3,…,T(1)
上式中變量和參數矩陣即可表達為:
A0=1 -a12 -a13 -a14-a21 1 -a23 -a24-a31 -a32 1 -a34-a41 -a42 -a43 1·yt
=lnBSlnGDPlnPIlnCPI·?鬃m=?姿11(m) ?姿12(m) ?姿13(m) ?姿14(m)?姿21(m) ?姿22(m) ?姿23(m) ?姿24(m)?姿31(m) ?姿32(m) ?姿33(m) ?姿34(m)?姿41(m) ?姿42(m) ?姿43(m) ?姿44(m)
(m=0,1,2,3),?濁t=?濁1t?濁2t?濁3t?濁4t
其中?濁mt分別表示作用各變量的結構式沖擊,?濁t是協方差為單位矩陣的白噪聲向量,即?濁t~VMN(0k,Ik)。
由于SVAR模型中含有4個變量,需要施加6個限制條件才能滿足模型的可識別性。根據經濟理論,本文施加如下約束條件:(1)國債作為一種金融資產,通過改變資產結構影響私人投資與通貨膨脹預期,從而作用于產出,即國債對產出、私人投資及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假定a12=0,a13=0,a14=0;(2)產出與系統內其他變量之間具有當期影響;(3)私人投資的增加勢必將拉動當期產出的增長,進而帶動當期私人投資與國債規模的增加,即私人投資與系統內變量呈同期關系;(4)通貨膨脹對系統內其他變量的影響需要一個傳導過程,因此假定a41=0,a42=0,a43=0。至此,在滿足了模型可識別的條件下,建立起了本文所需的SVAR模型。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1. 模型基礎性檢驗。SVAR模型需要在設定滯后階數的基礎上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AIC和SC準則,得到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為5期。并且ADF統計量表明,在顯著水平10%上,系統變量均拒絕有一個單位根的原假設,其為一階單整序列。這意味著所選取的四個變量可以構建穩定SVAR系統。
2. 協整檢驗與參數估計。本文采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Juselius協整方法檢驗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從Trace及Max-Eigen統計量看出,系統存在2個協整向量。SVAR模型根的倒數均位于單位圓之內,即該模型是穩定的。根據Sims等(1990)的研究,當系統變量存在協整關系時,利用原水平變量建立的VAR模型是可以識別的。因此,可得SVAR模型的參數值為a21=5.57,a23=1.30,a24=46.74,a31=17.40,a32=-4.62,a34=-16.06。
3.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依據已識別的SVAR模型計算出脈沖響應函數,以描述國債規模對中國經濟的動態影響(如圖1)。其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階數(年),縱軸表示沖擊作用的響應程度(0.000 1),實線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從圖1可得:(1)對于國債規模1單位的正向沖擊,GDP表現出了短期“倒U型”負效應,中期則呈現“單峰型”的正效應,而在長期中的反應類似于短期的“倒U型”負效應。這表明國債在短期中并不利于經濟增長。可看出,第17期轉為反向作用,且整體上呈負向影響,即中國現存國債規模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且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2)對于國債規模的一個正向沖擊,私人投資(PI)、通脹效應(CPI)顯示了與GDP響應(不同的是通脹表現為“雙峰型”正效應),即初期為負向影響,中期轉為正向影響,在第16期前后又轉為負向作用,并逐漸收斂于零點。整體而言,其對私人投資和通貨膨脹的影響也是負向影響,而且相比GDP與CPI的反應程度,PI的負向影響更為明顯。這表明中國現存國債規模對于私人投資存在先擠出-后擠入-再擠出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通脹效應。(3)綜合計算可得,國債規模1單位的正向沖擊,在中期將帶來峰值分別為0.072 5(第13期)、0.126 5(第12期) 和0.030 1(第12期)單位的經濟增長效應、擠入效應和通脹效應;在較長期中的經濟增長效應、擠出效應與通脹效應分別下降0.569 8、0.757 6及0.068 7單位。
4. 方差分解。在脈沖響應函數基礎上,結合方差分解探討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效應、擠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的相對貢獻度(見圖2)。
從圖2可得,現存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私人投資及通貨膨脹影響的相對重要性。(1)在初期,GDP的變動除受制自身因素外,第4期后主要歸因于私人投資及國債規模,且私人投資的解釋力度要一直高于國債規模。雖然國債規模和私人投資在前4期均快速增長,但私人投資逐漸減弱,國債規模逐漸增強,呈現出此消彼長趨勢。國債規模從第5期對GDP的解釋程度不斷加強,在中長期與私人投資形成抗衡之勢。(2)私人投資的波動受自身的影響在初期迅速減弱,第13期后穩定在36%左右;GDP和國債規模的解釋程度在短期呈現對稱式的增減趨勢,但第8期后國債規模的解釋程度逐漸增強并超越GDP,穩定在35%左右。(3)通貨膨脹對自身的波動解釋在短期迅速較弱,在第8期后穩定在9%左右;國債規模與私人投資對其解釋程度逐期上升,中長期均穩定在30%左右;GDP對其解釋程度在長期中最為顯著,在第21期穩定在40%以上。總體而言,在較長期中私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遠高于國債規模,國債規模對私人投資的影響要略大于GDP,GDP與私人投資對通脹的作用要小于國債規模。
五、 主要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SVAR方法實證分析了1981年~2013年間中國國債規模對經濟增長、私人投資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以考察中國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主要結論如下:(1)脈沖響應函數顯示,經濟增長和私人投資對于國債規模的沖擊均表現出初期和長期的“倒U型”負效應,中期“駝峰型”的正效應;通脹效應則在中期表現為“雙峰型”的正效應。綜合而言,經濟增長、私人投資對于國債規模的沖擊均表現出了較為顯著的負向效應,也就是說,中國現存國債規模總體上不利于經濟增長,并產生了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通貨膨脹效應,不過這種弱化效應十分微弱,可忽略不計,這與馬拴友等(2006)研究結論相近。(2)方差分解顯示,在解釋GDP增長、私人投資與通脹效應的波動因素中,國債規模成為了僅次于私人投資的重要因素。
總體而言,中國現存國債規模不具有可持續發展特征。在我國保持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背景下,國債作為重要宏觀調節工具,其管理已逐步地完善,而我國國債規模的不可持續性可能由于龐大的或有債務和地方債務引起,應該進一步厘清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地方債務管理與監督,加快地方融資創新,完善地方稅收體系,積極發揮國債的宏觀調節作用,保證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立峰.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問題研究[J].財貿經濟,2001,(9):12-17.
[2] 賈康,趙全厚.國債適度規模與我國國債的現實規模[J].經濟研究,2000,(10):46-54.
[3] 洪源,陳英.國債可持續發展的實現:一個綜合分析框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5):19-22.
[4] 馬拴友,于紅霞,陳啟清.國債與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J].經濟研究,2006,(4):35-46.
[5] 朱柏銘,徐利君.公債規模的“度”應當如何把握[J]. 財經研究,2001,(10):17-22.
[6] 何代欣.國債適度負債規模理論——模型特征與非線性模擬[J].財貿經濟,2015,(5):5-19.
基金項目: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項目號:68150003)。
作者簡介:殷金朋(1987-),男,漢族,山東省泰安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稅收與公共支出管理;賈占標(1987-),男,漢族,河南省南陽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政府預算;袁埜(1991-),男,漢族,天津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金融工程。
收稿日期:2015-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