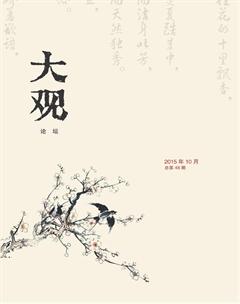淺析影響白族文化開放性的政治原因
謝學惠
摘要:本文對白族文化的開放性、宗教信仰的豐富性等特點的歷史成因作了分析和闡述,說明大理白族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其它先進的各民族文化,同時也表明了白族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極大的豐富了我國的民族文化,對我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關鍵詞:白族文化;開放;政治依附性
白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在我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白族的漢化程度較高,社會發展非常快,文化發達,文盲率最低。這都取決于白族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和接納。白族不僅有自己獨特而濃厚的民族文化,而且還有與外來文化融合后的豐富多樣融合式文化。白族文化是以自身的文化為主,融合眾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結果。在數千年的歷史中,白族文化融合了眾多的文化種類如:漢族文化、古越文化、荊楚文化和氐羌文化等。他們促進了白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這是白族文化發展的一個特點。
漢族文化對白族文化的影響很早就開始了。東漢漢武帝時期曾多次發兵進軍云南,欲將征服“西南蠻夷”。滇國被征服后,漢武帝派大批漢人到滇池地區屯墾并在滇國推行了郡縣制。其間曾派兩司馬(司馬相如、司馬遷)隨軍入滇。據史料記載大理人張叔盛覽對儒學情有獨鐘,向司馬相如學習作賦的方法,他后來成了一位頗有點名氣的賦家,著有《賦心》四卷,他是大理最早的漢文化傳播者。大理人今天能夠非常自豪地稱自己的故里為“文獻名邦”,張叔盛覽功不可沒。至今大理白族人民仍然認為對于白族文化的開始,司馬相如的功勞是最大的。唐朝時期,統治南詔的白蠻以開明大度的姿態,以“仿唐”學漢為契機,主動積極的引進了漢族的先進文化。南詔的統治者為了更好的學習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以漢文為南詔國的通行文字,將黑蠻已有的古彝文和白蠻已有的古白文用漢字代替。統一推行只用漢字,利于南詔人民學習漢族文化,這一措施的推行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扼殺了和白族文字的發展,影響了民族文化的完整保存,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這一措施的推行對白族文化帶來的積極影響。他加快了南詔全民接受先進文化的步伐,使南詔相對落后的文化迅速向先進文化過度。為燦爛的大理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二:提倡學習以儒學為主的漢族文化。六詔統一之前。蒙舍詔詔主細奴羅時,就積極推行儒學,他勸子民學習儒學,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到了細奴羅的孫子勝羅皮時,在國中修建“孔子廟”,至此,白族人民學習儒學之風興起。后來南詔國建立,便開始提倡學習儒、釋、道三教。從此對漢文化的學習推廣到了整個南詔國范圍內。統治者還分批派出南詔子弟前往成都學習漢族文化。第三:請精通漢文化的文人學士到南詔教授漢學。其中最重要的是漢人鄭回。鄭回是俘虜,但是因為他精通漢學,閣羅鳳不僅不殺他,反而很器重他,尊他為師,讓他為南詔王室培養人才。鄭回是南詔國四代帝王的老師。除了閣羅鳳,他還教授閣羅鳳之子鳳迦異及孫子異牟尋、曾孫尋夢湊漢學。異牟尋在位時,還讓鄭回出任南詔的首席清平官。第四:掠奪漢族人口,把俘虜中的工匠、藝人引入南詔開發資源,傳授技藝,南詔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可以說是這些工匠藝人用血汗和智慧造就的。慢慢的這些工匠藝人中的一部分人和白族融合,帶來了漢文化與白族文化的又一次融合,從而極大的豐富了白族文化。這兩種文化越融合,就越創造出白族獨特的民族文化。為白族的文化發展帶來了新的血液,新的細胞,為大理燦爛的民族文化增添不少光輝。
除了漢族文化,白族的文化中還有氐羌文化的元素,白族先民的來源之一是氐羌。約再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紀,由于匈奴向南擴張氐羌族群被迫離開,從青海高原南遷進入云南西部與當地土著氏族融合。兩族融合的同時也就把氐羌文化融合到了白族文化之中。在大理點蒼山發掘的新石器和陶器明顯帶有西北文化的特點。在大理發現的半穴居遺跡,與西安半坡原始人的半穴居式房屋屬同一類型。在大理出土的石斧石鑿與華北同時代的石器同式,石刀流行的半月式,也與華北出土的同時期石刀相同。由此可見,白族文化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接納和吸收其外來的先進文化,并且已經融入到了白族人民的生產生活中。
此外,白族文化中還融有巴蜀文化,公元前3世紀初,秦始皇先后派李冰等人開鑿從四川宜賓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從而打通了蜀國與滇國之間的通道,溝通了滇蜀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李冰攻下蜀國以后還迫使蜀民沿“五尺道”南遷,到滇池一帶。這促使了蜀和滇人的大匯合。人是文化的載體,人到哪里,文化就被帶到哪里。因此,這次蜀民與滇民的大匯合,自然也就帶來了滇蜀文化的大匯合。
白族文化除了和以上三種文化的融合外,白族文化中還能找到緬甸、老撾、越南等國文化的影子。可見白族的文化并非是一種單一的文化而是一種多元融合、和諧發展的文化形式。它不僅推動了白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白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和溝通,促進了民族團結,社會穩定。
宗教信仰是白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討論白族文化的時候,白族的宗教信仰是不得不作為一個重點來討論的,它的基本內容概括起了大理歷朝歷代白族人民生產和生活的所有習俗。白族自古就居住在蒼洱地區,由于這里交通較為便利,環境氣候較適于農業發展,加上接受漢族及外來文化比較早、影響較深,因此這也就決定了白族宗教的豐富性。白族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中原宗教極深的影響,道教和佛教是白族地區最常信仰的兩種外來宗教。南詔時期,佛教早已傳入,并開始盛行,大理的崇圣寺,三塔及劍川石寶山的石窟,都是佛教的重要建筑,說明佛教在南詔已經有相當的傳播。到大理國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已經盛況空前。佛教文化不僅普及于人民大眾,而且深入到國家上層建筑,成了大理國左右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意識形態。從佛教文化在大理的傳播中我們可以看到,白族吸收佛教文化,也如同吸收儒家文化一樣,經過吸收消化,使之融入到白族自己的文化當中,而且成為大理宗教崇拜的一個重要部分。在大理22位國王中,竟有一半出家為僧,把功名利祿卻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這只有大理國才有,在中國歷史上都很少見。道教對白族的宗教信仰的影響也非常深刻,在大理白族的本主文化和道教文化可以說是已經融合成了一體,道教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把忠烈之士列入他的神團體系中,而白族的本主神系的發展也這樣。道教的神系常以“帝”“君”等為封號,而白族的本主神系也同樣用這樣的封號。道教的神像常手執寶劍,白族的本主神像也多數與道教的神像相同。可見道教對白族本土宗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也說明了道教在白族地區很早就傳播并且已經被融合到了白族自己的文化中。在大理有很多白族人同時信仰本主、道教和佛教。在這里,佛教和道教已經和本土宗教本主融為一體。
白族燦爛的文化是離不開各族文化的影響和滲透的,其中漢族文化對于白族文化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漢族文化能對白族文化產生如此影響,其根本原因在于大理白族由于地處我國偏僻多山的西南部,是我過歷史上西南邊疆一個相對比較弱小的少數民族政權。長期以來其政權的穩固性一直受到北方的漢政權和周邊其他政權的威脅和侵擾,這樣的局勢下,白族為了保全自己的政權不被周邊強大的政權吞并,在政治上對漢族政權有很強的依附性。
白族早在三國時期就開始與漢族有了政治文化往來。那時候洱海周邊居住著很多個民族部落,各部落一致推舉了以為大酋長號稱“白王”,名果仁,建立了一個“白子國”。傳至十三代孫龍右那,那時正值三國時代的蜀漢丞相諸葛亮南征,在滇東一帶平定了雍凱、高定和南蠻王孟獲等叛亂之后,諸葛亮鑒于永昌郡和葉榆(進大理)白王未參與反叛,還支援蜀軍,為了安定云南局面,仍封龍佑那于故地,號建寧國,從此地方便安定無事。龍佑那又傳了十五代,傳至張樂進求。唐髙祖時,張樂進求曾率領輔臣大姓楊農棟等人入朝朝見。張樂進求受封為首領大將軍、西洱河大首領,楊農棟受封為右將軍。其他受封的還有洱海地區大姓多人。唐太宗貞時期,張樂進求的繼承人細奴羅請求臣屬唐朝,唐太宗封細奴羅為陽瓜州刺史(管轄今魏山地區),此后細奴羅的重孫皮羅閣通過唐王朝的幫助于公元七百零七年統一六詔,進而統一了全滇,正式建立了隸屬唐朝版圖的南詔國。并一直保持著君臣關系。公元九百十六年時,宋太祖冊封大理國“白王”為“云南八國都王”。宋仁宗慶歷四年,仁宗皇帝冊封大理國國主孝德皇帝為“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 可見,白族的政權,不論是白子國、南詔國還是大理國其政權的建立和統一都得借靠于漢族政權的支持和肯定,其政權才可以得到長治久安。從白子國、南詔國開始,白族即以開放的胸襟,主動積極的學習漢族先進的科學、文化,對儒、佛、道文化的精華釆取兼收并蓄的態度,又使各種流派的文化為我所用,從而促進了白族自身的繁榮與發展。
正因為白族歷史上對中原漢族有這諸多的政治依附性,使白族沒有特別強悍的名族個性,也缺乏自由獨立的思想,白族人對于外來的事物總是寬厚包容,兼收并蓄。這種民族性格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本民族的每一個個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族性格決定民族命運。正是由于白族這種獨特的民族性格,才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使白族人民面對外來先進文化時持有一種包容、接納、吸收的態度。從而使漢族文化及其它先進的,有價值的文化被白族文化所吸納。在吸收先進文化的基礎是,使自身得到更好的發展。數千年來,白族發展成為了一個比較先進的民族,這都與其獨特的民族性格分不開。
【參考文獻】
[1]趙寅松.白族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楊憲典.南詔大理國演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白族簡史編寫組.白族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4]白族簡史編寫組.白族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