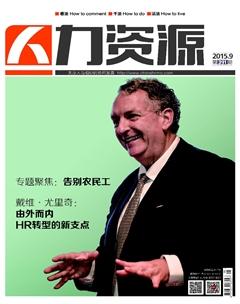企業留住新生代 過客不再羞答答
劉仲
互聯網上流行各種“體”,前些時日網上有一封水漆工的準女婿寫給丈母娘的“掃盲體”:
“阿姨,端午見面,看您很擔憂,好像對我們水漆工有誤解,所以給您寫幾句,算是掃盲吧。……你說刷漆很臟很累,其實干啥都有辛酸淚;你說刷漆的身體都很壞,其實刷水漆無污染無危害;你說我起早摸黑賺得少,其實遠超大學生那三瓜兩棗;只要您同意我和您女兒結良緣,我保證買房不找您借錢!”
讀之讓人慨嘆,這個小青年很有文采嘛,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說話很大膽嘛!同時,它更掀起了一陣人們對于“職業歧視”的熱議。其實,深層次分析,這不單單是對一種職業的“誤讀”,也恰恰映射了一類群體——打工青年,正面臨的尷尬與難題。
城市與鄉村間,可是過客?
現實社會中也存在各種“體”,比如被貼上標簽的“80后、90后”群體,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群體,海外歸來的“海歸”群體,當然也少不了炙手可熱的“公務員”群體,無需深究這種“群體”劃分是來源于社會學還是統計學,它已被人們約定俗成的接受。敢給丈母娘寫“掃盲信”的打工青年(小楊)也屬于一個群體,叫做“新生代農民工”。姑且這么叫,因為好多專家學者曾建議取消“農民工”這一帶有歧視性的稱呼,筆者在這一點上,很贊同崔永元說過的一句話“有人建議廢除‘農民工’這個稱謂,我看大可不必,如果農民工都是公務員的待遇,大家巴不得被叫呢,怎么叫不是大事兒,怎么對待才是核心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詞最早提出還是在2010年1月31日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指出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而后,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積極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的文章,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指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登記為農村戶籍而在城鎮就業的人群。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生長在農村,初高中畢業后進入城鎮就業;也有隨打工的父母在城鎮長大的農民工子女。
“新”是相對于“舊”來說的,既然被劃歸為一個群體,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于父輩的老一代農民工,也有著自己鮮明的時代特征:一,處在體制變革和社會轉型的新階段,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使他們的需要層次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能夠更迅捷地接受現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價值觀與開放式的新思維,成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傳播者。
二,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于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位于城市的底層,因此,在城鄉兩端都處于某種邊緣化狀態。
筆者曾經結識過一位80后打工青年小路,他在北京一家汽車制造廠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在此之前,他先后在東莞、深圳、杭州工作過。聊天時,他告訴我,“這里房價太高了,買不起,城市只適合工作,不適合生活。”當被問起“為什么不回到農村種兩畝田,搞點副業發家致富呢?”他笑了笑說,“你真是不了解我們農村的實際情況啊,回不去了。家里的幾畝田收入不高早就轉包給了大戶,雖然國家有政策鼓勵回鄉創業之類的,可是像我這樣一沒資金二沒技術的實在不知道回去該干什么,好像我們那里開車的也不多,我要是修車也沒什么好市場。況且,熟悉了城市各種便利,起碼回到農村洗浴、交通、網絡問題就讓我頭疼。”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小路的選擇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樣——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攢的錢、父親的資助,加上借外債,蓋起了新房。可是蓋了房子以后,還要出來打工,因為要用打工的錢還蓋房子欠下的債。
可以說小路正是千千萬萬打工青年的代表,有夢想,夢想在城市安家,又被城市的冷酷拒之門外;有無奈,回不去的鄉村,現實的需要只能讓他們又背起行囊,跟著同村的伙伴或親朋,繼續游走于各大城市,或因為工資低、條件差、遭受克扣等原因離開,再踏上征程……他們是城里人口中的“過客”,是老家鄉鄰眼中熟悉的“陌生人”。或許他們自己也習慣了“過客”的心態,在城市中追尋著自己時代賦予的夢想,盡管這個夢想或許只是“買房一定不向丈母娘借錢”的苦澀。
現實與未來間,何為靠山?
人社部2015年5月發布的數據,中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7395萬人,其中年齡為16歲至30歲之間的年輕農民工占比33.3%,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數量近1億,可是社會能提供的就業崗位仍然要面對著經濟下行的壓力,這是我們的現實;如此基數龐大的勞動群體必將影響中國的經濟走向,他們過得好不好關乎中國的未來,而他們中青年一代的夢想更不容輕視,這是需要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一代農民工待遇不公來實現的,也就是說,現階段我國各大中城市的財富之所以能夠在短時期內實現巨額積累,是因為上一代農民工把自己創造出來的相當一部分價值“無償”獻給了城市。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的薪酬待遇十幾年來并沒明顯提高,依舊低廉的工資待遇,與城市定居的高昂成本,已成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礙之一;現在的城市資源,以及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尚不能相互轉換,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權益保障又很難落地;教育公平難得享受,子女城市入學、升學難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正因為這種種問題的難以解決,他們又迫切需要尋找未來的出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漂泊就成了他們的常態,由此,農民工的“短工化”也就加劇了企業的“用工荒”。
“此生若能幸福安穩,誰又愿顛沛流離?”輾轉全國多個大中城市,做過流水線工人、庫管員、保安的28歲小劉如是說。“如果有可能,我更希望把打工城市視為第二故鄉,在那里安心工作、生活,可是企業關注我們遠不如我們關注企業多。他們更愿意把我們當做生產的‘手’而不是生活的‘人’,我似乎感覺不到這個城市的溫暖和安全。”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抽樣2000名全國各大城市中16-35周歲農村打工人員,“你認為對于成為一個城里人什么最重要?”排名前三的答案依次是“工作”“住房”“社保”,不能不說,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現實與未來,最重要的靠山就是“工作”,那關乎他們的夢想、他們自我價值的實現。
政府與自身間,企業為基
縱觀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移民問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進程。國家政府層面也一直在致力于解決新生代農民工變身為“產業工人”“新市民”的種種難題,比如國務院新近出臺《關于大力推進并幫助農民工返鄉創業若干意見》、廣東省政府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我省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等讓我們看到了政府的扶持力度,但宏觀層面的收效畢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積極參與技能培訓、
加強管理知識學習、增強自身競爭力,通過個人奮斗實現定居城市的例子也越來越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變化。但對于一個群體來說,階段性的外來因素與單獨個體的蛻變從來不是其命運根本性改變的依托,對于一個群體來說最可靠的是一個叫“組織”的東西,或者說“人與組織的協同發展”才是人力資源最可寶貴的財富,而企業恰恰是這個“組織”的基石。
所以,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企業應該承擔起責任。現在來看,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和未來,企業必須打破“農民工生產體制”,這個體制包含兩個方面:“工廠權威管理體制”和“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正是這兩個制度的存在,使得當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困難重重。
首先,企業需以人為本,摒棄“工廠權威管理體制”,留給新生代農民工公平感與安全感。“工廠權威管理體制”是指以高強度與長時間的簡單勞動、微薄的工資待遇、嚴苛的管理制度、危險的工作環境等為特征的現代工廠制度。這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得以確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企業得以迅猛發展的一種生產體制,它是以壓榨一代農民工的勞動價值為代價的畸形發展,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二、三產業主力軍時代的到來,它需要企業以一種積極的態度讓落后的管理體制退出歷史舞臺,實現社會生產的公平。
由于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經歷,他們對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相比于老一代農民工更重視工作的發展前景與意義,更看重企業的管理文化。這一特點在受過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對于打工仔為主要勞動力的餐飲行業來說,海底撈為什么你學不會?很多人去學海底撈都是去觀察文化、工作氛圍,但是有個根本的東西創始人張勇自己也多次強調過,海底撈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摒棄了工廠那種權威管理體制。
海底撈員工為何這么敬業?用張勇說過的話就是——“把人當人看”。這首先是要滿足員工的基本需求。海底撈為那些離開家鄉、離開父母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新的“家”,滿足了這些員工來到城市的“基本需求”。海底撈“關愛員工”的做法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些做法中,有些是制度化的,比如新員工入職關愛、高標準的宿舍和員工餐、各種各樣解除員工后顧之憂的后勤保障和福利;有些是融入了企業文化的,比如各級管理者的對下屬的關愛行為。海底撈通過內部培養、內部評級和內部晉升制度,基于貢獻和能力的、兩倍于同行水平的收入提供了員工自我成就的舞臺,成全了這群農村年輕人的夢想,幫助他們“用雙手改變命運”,這是海底撈員工敬業的“安全感來源”。
其次,企業內部應避免“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的出現,切實保證新生代農民工權益。“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是指造成我國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卻在農村養家、養病、養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當前的城鄉戶籍制度。企業在這一點上并非無能為力,對于企業來說,不能只要勞動力的生產而不關心勞動力技能培訓,不能只關心勞動力作為“工作人”的條件而不滿足其“自然人”的生活、感情需求……要留住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簡單靠工資、福利及培訓已不能順利實現,這時依法為其繳納社保、保證其合法權益;有條件的提供夫妻員工宿舍、職工子弟小學;企業代表依法與由工會或經民主選舉的民工代表就分配水平、支付方式及調整辦法等進行平等協商等,都將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
與新生代農民工接觸最多的是企業,工資由企業撥付、成長由企業提供晉升渠道、權益由企業提供基礎保障……讓“過客”不再羞答答,在你、在我、更在企業,請一起努力留住他們,共筑公正、公平的中國夢。 責編/劉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