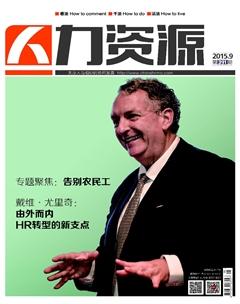若有煩心事,老而難養矣
寇斌
身陷“老而無養”的尷尬
凌晨4點,56歲的環衛工人劉國富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先接好水管,給1000多米的街道灑水,然后開始清掃。一直到快7點,滿頭大汗的他回家吃飯。早飯后,他還要繼續另一份保潔工作。雖然遠離家鄉,無法和親人團聚,但相比于在家務農,他對目前的收入還比較滿意。
在大連務工的刑利民已經62歲了。他說,近幾年,土地實行流轉。沒有了土地,村里的剩余勞動力一下子多了起來。由于大多數人都沒有技術,只能無奈地選擇進城干些體力活。他說他從前背100斤的貨物走上9樓,大氣都不喘,現在掄起10斤的錘子砸兩下墻就覺得身上發虛。即使是這樣他也不會選擇在家休息。用他的話說,這是為了以后干不動的時候攢點“活命錢”。
年齡大、沒技能。很多進入城市的高齡農民工,不得不選擇環境比較惡劣的建筑業,以及保安、家政、環衛等一些低端服務業。而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缺少基本的社會保障。“如何養老”是很多高齡農民工并不愿多談的話題。在他們眼里,只要身體允許還能打工,就不會停歇,即使有了傷病也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用他們的話說,“進一次醫院,半年的積蓄就沒了,大病小病忍一忍都能過去。”
隨著時間的遷移,當年第一批走進城市的農民工大都跨入了老年行列。2008年底,國家統計局著手建立農民工監測調查統計制度,對農民工群體的數量、流向、結構、就業、收支、居住、社會保障等情況進行摸底調查。數據顯示,2009年至2012年,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與總量連年攀升,且大都集中于制造業、建筑
業和服務業等低端崗位,其中尤以建筑業為重。
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暫停了公布50歲以上農民工的占比數據。該報告也取消了之前的“農民工年齡構成”一欄,而是改用“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來代替。如果將老一代農民工視為高齡農民工,其比重達到15.2%,絕對數量超過4000萬。今年4月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高齡農民工的絕對數量更進一步沖高至4685萬人,占比上升至17.1%。
如此龐大的弱勢群體,其生存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200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的通知》將農民工納入到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范疇。隨著2010年《社會保險法》的頒布實施,農民工終于完全融入社會保險體系中。
雖然從2010年起,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不再排斥農民工,但由于加入社會保險晚,已經影響到農民工社會保險繳費年限的計算。根據現行規定,農民工累計繳費15年才能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未達到15年的,無法領取養老金。
有專家建議,改革繳費率較高的養老保險制度設計,降低企業和農民工個人的繳費比例,從而調動企業積極性,也讓中老年農民工有能力和信心來繳納養老保險。但隨后有反對意見稱,在養老金支付能力堪憂的背景下,這一改革勢必遭遇較大的阻力,即使多年后此項改革順利落地,一部分高齡農民工也早已老去,能否享受到改革的紅利,仍是個未知數。
對于高齡農民工養老難題,人們自然會想到現行農村養老制度“新農保”,但“新農保”不是免費午餐。按照要求,參加“新農保”的農村居民可按不同繳費標準繳納養老保險費,參保對象在退休前繳錢越多,日后領取的養老金也越多。但正常情形下,農民工從一開始就不是新農保的服務對象,而是打工所在地城鎮綜合養老保險的參保主體。從2014年起,中央要求各地在三年內將此項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并軌。因此,目前青年一代農民工將來的退休養老已有基本的制度可供托底,而高齡農民工退休養老困境,短期內恐難消除。
不僅如此,勞動維權也是另一個困擾高齡農民工的問題。據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社會法研究所副所長金英杰分析,目前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是以勞動關系的確立為基礎的,現有法律規定了法定退休年齡男性為60歲,而高齡農民工一般高于60歲,超過退休年齡繼續就業,勞動關系存在與否及工傷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爭議不斷,導致高齡農民工工傷保險權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養老“三道保險”仍需完善
面對困窘——2014年7月,國務院將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從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70元。在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體系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也得到有效的累積和接續,雖然養老待遇逐漸得到改善,但依然難以解決這一代人的養老困境。對此,專家又開出了“三道保險”,即土地養老、返鄉創業就近養老,以及社區養老。客觀來講,這“三道保險”本身還需要完善鞏固,只有先推進這“三道保險”的改革,做好養老保險保障的筑底工作,才能談得上相應的可靠保障。
先看土地養老。2014年底,中央提出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成為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但目前農民尤其是高齡農民對于土地的收益大多是一次性獲益補償,也就是因為土地所有關系轉租,獲得一次性補償金,但這筆錢能不能保障他們的養老到底,很少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
再看返鄉創業就近養老。無論農民工最終在哪兒養老,政府的財政保障必不可少。對于高齡農民工來說,“返鄉創業”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難度頗
高,更不能指望高齡農民工通過返鄉創業來實現就近養老。對于返鄉創業實現就近養老的方式,更適合沿海東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中青年農民工,甚至也只適合他們中的極少部分。
最后看社區養老和自助養老。這是這三點建議中較為“靠譜”的一項。但是也應該注意,社區養老最關鍵的是資金籌措等問題。政府相關部門還應增強責任意識,對于城鎮化速度較快的地區,需要格外重視社區養老機構的政府投資和財政補貼,未雨綢繆,為將來大批農民工返鄉創業養老做好硬件準備,而目前社區養老和自助養老還大都停留在紙面上。
“補板”農民工養老體系
高齡農民工正在過度地消磨著健康,而亟待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和他們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他們難以體驗夕陽之美。讓農民工也有一個幸福的晚年,這不只是體現出國家的文明與進步,更關系到數千萬高齡農民工實實在在的民生。
2012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了《關于國家社會保護底限的建議書》,在當前世界面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再度強調要對有需要的個人和社會群體提供安全保護,并希望世界各國對此作出可靠的承諾。這與中央最近一直強調的“保基本、托底線、救急難”的精神基本一致。
《建議書》中提到:各成員國要重新確定提供社會保障的選擇順序,優先考慮那些目前未受保護的、貧窮的、弱勢的社會群體,譬如在非正規經濟組織中的工人及其家庭,要為這些社會群體在他們的整個生命周期中提供有效的、基本的社會保障。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高齡農民工尤其是“超齡農民工”,正是這樣一個需要國家保護的社會群體。他以為,政府和社會需要對農民工至少提供以下的保護:
其一,根據國情,將2億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制度中并不現實,因此對收入在一定標準以下或參保年限已經達不到最低繳費年限的農民工,應允許他們自愿選擇是否參加養老保險。
其二,在未參保的農民工結束勞動生涯后,國家應該向他們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現在的“新農保”主體部分其實就是一種普遍享有的福利性老年津貼,但問題是支付標準太低,應盡快使其相當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其三,按累進原則,而不是按企業規模,向企業征收社會保護稅。企業利潤越大,所繳稅率就越高,這也同時解決了企業對社會保護責任的問題。
其四,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每個勞動者在銀行開設個人養老賬戶,勞動者為養老而儲蓄可獲稅收優惠,國家應保證這樣的超長期儲蓄可以得到較高的利息。在勞動者因老年、非職業關聯的傷殘和死亡而有需要時,就可以動用賬戶中的存款。
其五,一旦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便進入人生最痛苦的階段。因此,國家有責任向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和針對長期照護的社會服務。可以從完全失能老人做起,一旦完全失能,他們的生存期是有限的,因此國家的負擔也是有限的。
其六,對于勞動年齡階段的高齡農民工,其從事的行業和工種,國家應該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勞動保護。 責編/張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