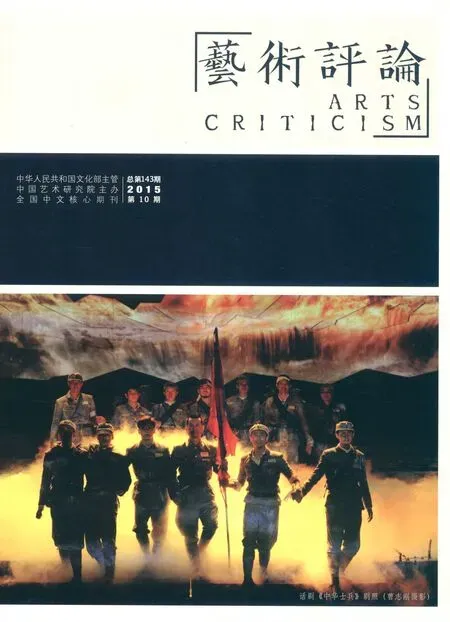《刺客聶隱娘》的追求
唐宏峰
《刺客聶隱娘》的追求
唐宏峰
風吹樹葉,自成波浪
《刺客聶隱娘》(以下簡稱《聶隱娘》)開篇第一個鏡頭就預示了一場在當下院線環境中極為不同的觀影體驗。黑白影像,中近景,一棵矮樹下有兩頭驢子,蟬躁之聲,之后鏡頭緩緩平移,窈七(聶隱娘)和道姑一黑一白站立在樹下,道姑說:“此僚置毒弒父……”黑白影像中那兩頭矮樹下的驢子像極了黑澤明的畫面。一種久違了的膠片電影的質感,在影片不同慣常的畫幅和銀鹽化合反應帶來的顆粒感等方面充分表現出來,而文言對白、黑白影像(或后面高飽和度的色彩畫面)、長時間靜止的畫面、滯重的鏡頭運動和內斂的人物,都立刻彰顯出影片高度的形式化追求。但影片最終證明這種極致形式沒有導致所謂“形式大于內容”,而是形式本身成為內容,形式融化為一種液體般的氣質,流淌在電影的每一個角落,造就一個寧靜、絢爛和準確的影像世界。
第一個鏡頭之后,窈七飛身刺僚,無知無覺,之后鏡頭變為仰望樹冠,風吹樹葉,嘩啦啦作響。“風吹樹葉,自成波浪”,這是電影剛剛發明之時,人們對盧米埃兄弟的影片所具有的那種真實自然的特質的描述。《聶隱娘》中,大僚撲地,突然風起,樹葉嘩響,立刻讓我想起這句充滿詩意的話。克拉考爾說:“電影熱衷于描繪轉瞬即逝的具體生活——倏忽猶如朝露的生活現象、街上的人群、不自覺的手勢和其他飄乎無常的印象,是電影的真正食糧。盧米埃的同時代人稱贊他的影片表現了‘風吹樹葉,自成波浪’,這句話最好表現了電影的本性。”[1]正是在盧米埃紀錄電影的基礎上,克拉考爾將電影的本性定義為“物質現實的復原”。升騰的煙霧與不停晃動的樹葉,最好地區分了電影與之前種種粗糙的表現簡單重復動作的活動圖畫,體現出電影前所未有的能力。盧米埃的觀眾曾驚異于《嬰孩喝湯》背景中在風里搖擺著的樹葉,贊嘆《鐵匠》中“蒸汽慢慢上升,一陣風忽然又把它吹散”,“這種景象,用封登納爾的話來說,就是‘實地捕獲的自然景象’……給人多么深刻的真實感和生命感。”[2]電影具有對自然細膩紋理的真實捕捉能力,這種能力被華語電影遺忘已久,侯孝賢重新拾起了它。
與早期電影類似,在《聶隱娘》優美的自然外景中,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電影中一處最長的風景固定鏡頭,是晨間林木和遠山倒映在湖中,雪白而濃稠的霧氣緊貼水面回旋縈繞,鏡頭耐心地固定不動,看著似有生命的霧氣周而復始。影片結尾處的核心段落也極妙地表現了霧氣,道姑站在深谷之上,谷中霧氣逐漸上升,窈七上來拜別師傅,鏡頭只是幅度很小的平移以容納人物,之后長久固定地看著霧氣越來越濃,人如立于霧中。《聶隱娘》給觀眾帶來的觀影挑戰,最主要在于長時間靜止不動的鏡頭,長鏡頭向來是侯孝賢的招牌,但此次更極致,以往是鏡頭不動,而鏡中人物在俗世中紛繁活動,但《聶隱娘》不僅鏡頭固定,鏡中事物也極少變化,所以造成畫面靜止的感覺。不過,事實上,恰恰是在靜止中,侯孝賢精細地表現自然的運動,鏡頭停留在那里,他想讓觀眾看見的內容也在那里,是自然的律動,比如煙霧的宛轉漂移;是人物的氣息,比如窈七在簾后、屋檐或無所不在的某處站立觀看,一動不動,而驚心動魄。《聶隱娘》無比安靜,侯孝賢讓自然和事物本身說話,讓影像本身構成內容,而非形諸于口的語言。這正是“物質現實的復原”,是“電影的本性”,在這個意義上,《聶隱娘》恰恰是寫實的,一草一木、重巒疊嶂、亭臺樓閣,在鏡頭中獲得某種光芒。克拉考爾曾描述自己第一次看電影的體驗,“使我深深感到震動的是一條普通的郊區馬路,滿路的光影竟使它變了一個樣。路旁有幾棵樹,前景中有一個水坑,映照出一些看不見的房屋的正面和一角天空。然后一陣微風攪動了映影,以天空為襯托的房子開始晃動起來。污水坑里的搖晃不定的世界——這個形象我從未忘懷過。”[3]《聶隱娘》中大量長時間的固定鏡頭與靜止畫面,根本上應該這樣理解——這是電影這門視覺藝術的根本屬性,它展現自然與事物,好像我們第一次看見它們。影片采用大量中景、遠景,極少近景和特寫,鏡頭運動簡單、緩慢,都是這種自然復現的要求。影片中外景多是遠景,人物在自然中行進,鏡頭的運動常是以空鏡開始,緩慢平移,人物入畫,隨后鏡頭跟人物,最后鏡頭止,人物出畫,空鏡。一個鏡頭中景物變化很少,連景別也沒有變化,就是那種穩定細膩的自然。藝術是可見世界領域的偉大教師,它教導我們如何觀看。
《聶隱娘》的聲音設計也與這種自然復現的視覺相匹配。電影前所未有地將蟬鳴作為基本的環境音,在其上附以對白或音樂,而對白稀少,音樂極度克制,各種細膩的環境音成為主要聲源(蟬鳴、蟲聲、鳥叫、開門的吱吱聲、柴火的噼啪聲等),蟬燥林靜,鳥鳴山幽,聲音層面也突出了影片的寧靜特質。在這部影片的獨特形式中,畫面與聲音一起構成自然的復現,它讓我們看,最純粹的、單純的用眼睛看,而這已經是電影久違了的東西。
簾與風,純粹的觀看
《聶隱娘》的畫面由兩種反差極大的內容構成,內景極盡奢華唐風,外景則主要是水墨般的清麗山水。在田興府一場戲中,由屋內拍屋外,鏡頭朝向門口,室內的黃色與紅色裝飾物和燭光暖光源構成一個橘紅色的邊框,而屋外則是清冷藍色。這個鏡頭構成了影片美術的基調。從《海上花》開始,侯孝賢進入對電影美術的極致追求當中。《聶隱娘》的美術師黃文英用建筑、家具、器物、服飾、屏風和簾帳等,精心打造出一幢幢華美堂屋,恰如其分的人物在其中活動。影片的美術師在唐代繪畫中攫取靈感,艷麗的色彩在膠片顆粒中達致飽滿。這里格外要提及影片中簾的應用。
唐代紡織文化發達,織物繁盛。《聶隱娘》中人物服飾是那種厚重的質感,層次豐富,也反映出這一點。而各種簾帳在影片中的巧妙使用,前所未有。幾乎在所有的內屋中都有層層疊疊的簾子,有竹簾、布簾和絲簾,薄厚粗細不等,尤其是輕盈的絲綢之簾,四處懸掛。簾可卷起,可放下,重重隔隔,隔而不斷,有效豐富了空間的層次;簾與風是絕配,簾輕盈,隨風飄動,增加畫面的動感;同時,簾上都繪有精細圖案,隨風忽明忽暗,似透非透,近看遠觀,效果迥殊。在田季安與胡姬在內闈長聊一場戲中,簾的運用絕妙,絕美。層層疊疊、薄如蟬翼的簾子在微風與燭光中搖曳,鏡頭在簾后,凝視床前二人,隨著簾動,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美麗的光斑晃動,空間的豐富層次和調度性被極大增強。窈七站在簾后更暗而幽深的處所,聽著田季安講述自己之被拋棄,站立不動,面無表情,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全部轉化為平靜,只有簾子的飄忽不定與晦暗不明,暴露了人物內心的波動。
站立不動、觀看傾聽的“隱”,比劍術神妙、無使知覺的“隱”,更是聶隱娘的本質。影片經常表現窈七在房梁、簾后、林間默立觀看,看小兒嬉戲、看舊日戀人寵妾,很多時候,即使影片沒有給出窈七的身影,也會讓人感覺畫面是她的視線所見。有一場戲,表現侍衛夏靖的在堂屋高層快速走過,察覺到異樣,又折返回來,觀察一番無所獲,再次離開,鏡頭沒有給出窈七的位置,但我們知道她在某處看著他的徒勞。聶隱娘的看是如此耐心,一方面是其刺客身份所要求的伺機出動,而另一方面,她內心的不忍與糾結,才是長時間沉默觀看的真正原因。在影片中,窈七的主要行為恰恰是觀看,而非武打。聶隱娘的視線是影片隱而不彰的線索,影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是經由她眼過濾的自然與人世。“風吹樹葉,自成波浪”是要看的。觀看就成了《聶隱娘》最本質的東西。在這里,視覺的重要性大大高于敘事,這不是新浪潮之后電影史的反敘事流派,而是回到電影誕生之初,感動過克拉考爾的那條雨后街道。
以平正寫奇幻,可以選擇的人
聶隱娘的故事屬于中國刺客游俠的源長傳統。在這一傳統中,女俠自然少,但唐代尤其多,以聶隱娘和紅線女為代表。女俠的故事通常更奇幻,聶隱娘和紅線女都是唐代末年藩鎮割據時代的刺客型殺手,自小被道姑收養訓練,善輕,入宮殿或軍帳如入無人之境,直刺人喉或徑取大印,具有奇幻仙俠的色彩。這類故事本可以拍得非常神妙激烈,但顯然侯孝賢意不在此,相反,他刻意淡化那種奇幻,卻并非取消,而是用一種相反的態度來表達,用平正來表現奇幻,用清冷來表現激烈,形成一種表里對立、內外張力極高的狀態。
電影中,窈七隱身術高超,去到哪里都如入無人之境,但影片沒有一次直接表現其飛身的絕技,而是刻意回避,總是直接展現其身處某地,這樣就使得奇幻的成分不是正面呈現,但也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神妙高蹈。這就是以平正寫奇幻。小說中甚至有聶隱娘鉆進某人腹中的情節,這些都沒有在電影中出現。影片的武打風格為近身格斗,強調一招直敵,沒有神仙似飛來飛去的武功。而在情感表現上,人物內心的痛苦與輾轉,都化為無表情的臉孔和無動作的身體,隱娘是平淡的目光、緊閉的嘴唇和直挺的身板。侯孝賢用清冷來表現激烈,冰火相鄰,張力十足。
與隱娘形象類似,《聶隱娘》中其他人物也都恰如其分,道姑的凜冽、公主的孤獨、聶父母的疼惜、忠義與周旋、田季安的暴躁、念舊與在政治亂局中的處處受鉗制、田元氏的強悍與野心、磨鏡少年的純真,在極少的篇幅與筆墨下,都得到準確表現。盡管影片故事被極度省略,人物卻還是飽滿鮮活的,每個人物所牽扯到的情節線索如草蛇灰線隱匿在對白與行動當中。故事高度簡約,但格局仍在,唐朝末年亂世,藩鎮割據,各方勢力爭雄,刺客泛濫,所有的人物都是在亂世中依據自己的價值觀行動,包括道姑、公主娘娘、田季安、田元氏。隱娘初始為道姑所代表的朝廷勢力服務,鏟除各地勢力,希圖恢復統一,但最終體味到政治之無序與無意,用最簡單的人道與不忍之心來引導行動,選擇“不殺”。這個故事表面清冷,內里卻是大時代的動蕩、價值的崩塌與個人的選擇。唐人傳奇中,作為刺客的聶隱娘更換了自己的雇主,投奔了原本要殺的人,只因那人水平更高。禮崩樂壞,臣亦可換主,隱娘擇夫擇主的自由,是時代文化的體現。電影雖然完全更改了小說中隱娘擇主的核心情節,將其改編為一個被拋棄與被犧牲的女性悲歌,但內里,那個說出“弟子不殺”、劃破師傅衣裳的聶隱娘,還是那個具有選擇權的唐代俠女。一方面是“青鸞舞鏡”的孤獨,被拋棄、被犧牲;另一方面則是世亂之際,朝綱之外,個人可以選擇的自由。一切都在影片最后一個鏡頭中得以體現,聶隱娘與磨境少年和采藥老人一起,長久地走在荒草與青山之間,節奏鮮明的片尾曲響起。隱娘再次孤獨地離家遠走,但這次是自主的選擇。
風吹樹葉,自成波浪。侯孝賢的內心是真的寧靜醇厚,才會在電影的里里外外、男女老少、聲音畫面等各方面,總力貢獻出一場寧靜又絢爛到極處的藝術。他恢復了電影“觀看”的本性,呼喚人們耐心細致的眼睛。
注釋:
[1][3]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M].邵牧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3、2.
[2]轉引自薩杜爾.電影通史(第一卷)[M].忠培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314-316.
唐宏峰: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