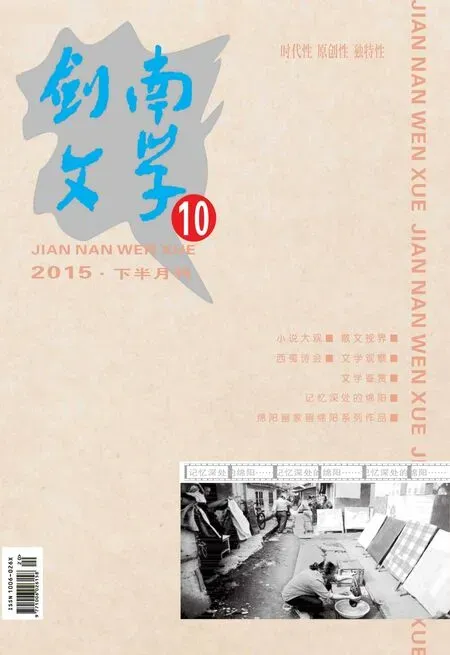東北詼諧文化的軀體與語言狂歡——以二人轉為例
■張 健
隨著東北二人轉、喜劇小品等在全國的流行,東北詼諧文化似一股新鮮血液流遍大江南北,極大地刺激了國人的神經,其主要體現在軀體動作和語言兩個方面,其形成和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這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如出一轍。
一、狂歡理論
前蘇聯思想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歡理論根植于中世紀非現實世界與現實世界截然分明的對峙,當時的現實世界是嚴肅和禁欲的,人們渴望能夠摘掉偽裝灑脫生活,于是人們在這樣一個由狂歡節和廣場所營造的非現實世界中使人性得以盡情的釋放。狂歡世界有四要素:時間因素、空間因素、軀體因素和話語因素(趙勇,2002)。人們在狂歡節卸掉偽裝,在極具感染力的廣場上演與現實世界截然相反的狂歡,人們通過極度夸張、變形、戲仿的身體語言,強化了內在軀體與外在軀體對話的渴望,人們得以在完全平等的前提下進行真誠的交流。在這樣的非現實時空和怪誕軀體的影響下,語言也與之相應地通俗化、口語話、俗語化和狂歡化了。
二、二人轉中軀體與語言的狂歡基礎
東北二人轉主要來源于東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蓮花落,是北方地區漢族的一種民間說唱藝術,邊說邊唱,載歌載舞。現在被全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是新型二人轉,這種藝術形式已經不拘泥于最初的秧歌和蓮花落,在商業利益的影響下,二人轉在舞臺上呈現出的還有歌曲演唱、相聲、脫口秀、拉丁舞、絕活、雜技等,已經與時俱進地發展成了一種“雜劇”。二人轉植根于東北農村,那里的群眾一呼百應,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內容貼近生活實際,家長里短、人際關系、打情罵俏、甚至于有關性的暗示都會出現在舞臺上,肢體動作和表情滑稽夸張,有些堪比或趕超了雜技表演中的小丑,丑旦間的逗哏和調笑貫穿始終;采用東北方言,語言極度口語化,語言直白,對一些敏感話題譬如性也毫不避諱,這打破了任何一種中國傳統的戲曲曲藝形式的常規,這種原生態的粗鄙的戲曲形式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真實而新奇的審美感受。正規戲曲對觀眾造成了審美疲勞,當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后,人們蜂擁追捧也在情理之中,這造就了狂歡化的新型二人轉。
三、二人轉中軀體與語言的狂歡表現
東北二人轉的表演手段可以概括為“說、唱、做、舞、特技”五大部分。軀體因素是狂歡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在二人轉中有極為生動的體現。二人轉中的做功用身段和動作輔助演唱,手、眼、身、法、步協調運用;舞功以跳東北大秧歌為主,也不乏其它民間舞蹈和武打,特技要求有耍扇子、耍手絹等雜技性的絕活,舞臺效果勁爆。
東北二人轉的來源之一是東北大秧歌,所以在新型二人轉的表演中動作眼神、手勢、軀體動作的豐富多彩是一大亮點,其共性是夸張、扭曲、挑逗。二人轉的軀體動作有三大絕活:不倒翁,即傾斜站立,與地面保持30 度角;手絹功,要求一塊手絹不但能在身上各部位轉得眼花繚亂,在空中飛來飛去;傻子戲,要求惟妙惟肖地模仿傻子的行為舉止。這些接地氣的軀體動作拉近了演員與觀眾的距離,使大家能夠同處于同一個平等的平臺,能夠被大眾所喜聞樂見。
話語是狂歡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東北二人轉的另一來源蓮花落是一種自說自唱的漢族曲藝藝術。新型二人轉的說唱功主要來源于此。二人轉唱詞以七言和十言為主,兼有長短句式;說功分“說口”、“成口”(亦稱套口)和“零口”,丑逗旦捧,語言風趣幽默,招人討笑。之所以二人轉的說功詼諧幽默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東北方言的采用。東北方言是多元文化的結晶,受滿族、朝鮮族、蒙古族等語言的影響,東北方言具有了自己鮮明的特色。 很多字音受滿語等語言的影響,具有了獨特的發音,如“你干啥去”被讀成“你嘎哈切”;“上街”被讀成“上該”。受外來語影響也很大,如東北小孩喜歡玩的羊的關節被稱為“嘎拉哈”,葵花籽被稱為“毛嗑”。一詞多義也是東北方言的重要特征,如“蔫吧”既可以指菜葉子失去水分,也可以指人沒有精神。東北方言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生動形象,“快點兒”叫“麻溜兒地”、“慢點兒”叫“慢兒慢兒地”、“不參與”叫“溜邊兒”、“太過參與”叫“欠兒欠兒地”,詼諧幽默。東北話還因其獨特的重音強調而具有俏皮色彩,如當你對某人的所作所為不滿意時,你說“那你就那樣吧!”,用東北話說則是“那你就那樣式兒的吧!”而且會把重音放到“式兒”上,詼諧俏皮此起彼起。
其次,二人轉語言的獨有特點。在二人轉的說口中,俗語和歇后語大量使用,俗語其實就是俏皮嗑兒,通俗易懂、人人皆知,幽默風趣,充分體現了東北方言的鮮活和接地氣的特點,如“瞎么杵子上南極——根本找不著北”。 諧音的應用也到了極致,如“產房傳喜訊——人家生(升)了”,這都是東北人民真實的生活體驗。二人轉的語言還具有很強的修辭性。首當其沖的就是押韻,不論出口的是不是詩歌,往往都是以押韻腳的形式出現。一語雙關的應用如“帥有個P 用?搞不好還不是被卒子給吃掉!”此“帥”非彼“帥”。仿詞被大量應用,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崴”,讓人感覺既熟悉又陌生,對常用語句的某個成分作些許改動,在已經失去新鮮感的舊詞的基礎上增添新意,給人們帶來無窮樂趣。同義詞反復使用也是二人轉語言的一大特色,如“你看人家多英俊、瀟灑、帥、帥呆了!”多個同義詞的使用會增強語言色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東北方言的幽默風趣與二人轉獨有的豐富的語言形式構成了一席豐盛的詼諧語言狂歡盛宴,因其蘊藏著東北人的直率與豪爽,說者聽者容易達到共鳴,給人以幽默詼諧之感。
四、東北詼諧文化中軀體與語言狂歡的現實意義
在新型二人轉給人民帶去歡樂的同時,唏噓之聲甚至唾罵也伴隨出現。二人轉具有很強的親民性,但有人認為二人轉有些言語和行為不雅,尤其是一些粗口和對殘疾人的模仿,言辭粗鄙,嘲笑生理缺陷,把自己的歡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因此被一些文人視為低俗文化。
凡事都有兩面性,我們不能因為二人轉等戲曲形式中以上問題的存在就對其進行全盤否定,畢竟這些詼諧的藝術形式在東北農村以致全國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熱心粉絲,而且我們絕對不能否認其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歡聲笑語。問題在于如何在表演中擯棄這些不良因素,揚長避短,使之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大廈增磚添瓦,為中國夢的實現貢獻力量,這是我們要深思的。
結語
以二人轉為代表的東北詼諧文化從軀體表現到語言應用都充分展現了其狂歡特點,其表演中所呈現的軀體動作的降格以求、語言的自由豪放,使得表演者和觀眾能夠產生共鳴,達到狂歡效果,深受群眾喜愛。然而一些粗鄙言辭和軀體行為又使一部分觀眾難以接受。這個山芋的燙手問題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以使以二人轉為代表的東北詼諧文化能夠沿著良性發展的軌道不斷傳承,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