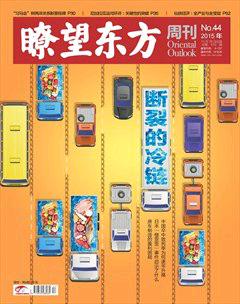眾說
方方敗訴,文藝批評如何自處
因在微博上質疑湖北籍詩人柳忠秧為評魯迅文學獎“到處活動”,湖北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方方被告侵犯名譽權。近日,該案一審判決方方構成侵犯名譽權,并判決“方方立即刪除針對柳忠秧的微博,刊登道歉聲明并向柳忠秧支付精神撫慰金2000元”。
然而,方方本人卻表示“就算抓我坐牢都不道歉”。另有少數聲音指因“證據不足不過硬而輸官司”的方方“沒有法律思維”。
法律能塑造文藝批評的樣貌嗎?怎樣塑造一個好的、純粹的文藝批評環境?如何使用作為倡導或平衡價值觀、審美觀必備手段的文藝批評?
敗訴與“形而上”的道德勝利
劉巽達(《上海采風》雜志主編、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作家)
道德輿論和文藝批評何用?倡導或平衡價值觀、審美觀。方方對“跑獎”行為的道德譴責,以及對柳忠秧詩歌水平的文藝批評,就是在行使這個功能。
在社會轉型期,在價值觀混亂的當下,法院不能只以“技術派”的立場對待案子,更要以“思想派”的立場“把舵”案例的導向意義。因為法律的普適作用和溢出效應不容忽視。
法官如果缺乏博大的胸懷、廣闊的視野、堅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被所謂的“過硬細節”牽著鼻子走,一不小心便傷了大眾的心。
對于“方方敗訴”坊間不乏有這樣的解讀:柳忠秧為了評上獎,確有“跑獎”行為和事實,但還不至于“把所有評委搞定”。所以,在支持者眼中,方方的敗訴也只是部分敗訴。雖然方方肯定會上訴,并且“坐牢也不道歉”,但這一切法院或許并不意外。
從法院的立場來說,判方方“敗訴”,絕對是輕打一板;而方方絕對認為是重打一板,乃至是非不分。站在各自角度看,都情有可原。
但如果“看客”不能洞悉法院的尷尬和智慧,而是走向兩極——或由此認定“法律和道德就是兩碼事”,或認定“中國的法律無益于主持正義”,那么這樣的判決有何積極意義?
一個“常識”必須強調:某些情況下,法槌的塵埃落定并不是真理的塵埃落定,贏了案子并非等于贏了人心。柳忠秧們如果覺得“勝訴”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無一絲一毫的反思和檢討,那么,即便方方們再一次“敗訴”,也是充滿道德勇氣的“形而上的勝訴”。
法院與常人該如何達成共識
王嶸(上海漢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
“彭宇案”中,法官判定彭宇撞倒老太太,判決的推理思路是“如果彭不是肇事者,他就不可能主動將老太太送醫”。不管此案真相如何,但這種反智推論方式,令公眾難忘。這次柳忠秧訴方方案的一審判決,同樣讓我無語。
為什么明顯屬于常識范圍內的是非判斷,法官和常人無法達成共識?
事實上在這起“方柳紛爭”當中,真正導致事件發酵的主因,恰恰是柳詩本身所呈現的文學水平。方方說“就算法院判我輸,難道他的詩就變成好詩了?”,點到了問題的實質。
我覺得法官對柳詩文學水平的判斷,好像被省略、被跳過了,或者,被隱在判詞背后某個暗處。公眾從一審判決中得到的印象,是法官在判決這類名譽侵權案時,根本不看作品本身。柳詩寫得再差,我也認為被告必須提供直接證據,證明評委被搞定了,否則就構成侵權。你得舉證。舉不足?那沒辦法,我判你輸。
如果僅從訴訟實務的角度出發,我承認被告方方在涉案微博中說柳“把評委全部搞定”,表達的是她的主觀推測,而不是一個目擊事實,但這個推測是有基礎的。讓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人們從判決中如果更多讀出這樣的信息,法院似乎保護那樣的創作、那樣的參評行為,這是不是游離了常識,與常識相悖呢?
如果這類判決滋長、增多,法院的權威和公信力會不會受到傷害?這是不是應該警惕呢?
用好法律,百家爭鳴
馬慶云(影評人、書評人)
方方說要上訴。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把這場官司從名譽侵權方向轉到作協內部對作家的公開批評上來。湖北作協主席方方當然可以公開批評自己的會員。司法的有趣之處就在這里,換個角度,沒準就能打贏。實際上,用好法律,在法律范疇內進行爭論,正是百家爭鳴的好事情。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繼續期待方方與柳忠秧的第二次司法較量。
方柳之爭,更大的意義在于極大震懾了到處“跑獎”的行為,正本清源,要拿作品說話,而不是拿獎項說話。
此外,是不是應該取消對文學獎獲得者的獎勵制度。這其實是個大系統。現在,要是哪個作家獲得了文學獎,會在單位得到對應的獎勵,對評職稱等也有作用。這有點像大學的獎學金評定制度。
文學獎為什么就能在社會上顯示出這么重要的表象來呢?實際上,還是因為我們都太懶了,喜歡用一個外人給的標準來衡量作者。因此,我們在見面的時候,往往都先報頭銜。頭銜,實際上就是標簽,人與人之間,最懶惰的了解方式,就是彼此看標簽。
標簽橫行的社會里,我們能不能換一種不懶惰的相處方式呢?比如,看一個作家,我不管你獲得了什么獎項,我讀你的作品,自然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好壞,我有一家之言。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其實挺難。我們這個社會,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最缺少的就是個體對價值的獨立判斷。文學這東西,沒有誰好誰壞,還真得讀者們自己打分才行。
回頭來看這次訴訟,法院依法來判,沒有錯;道德不與法律齊平,而有自己的追求,也沒有錯。兩者較勁,或許也是一種好現象。
文學不純粹,批評也難純粹
劉宏偉(資深媒體評論員)
今天的人們會容易輕信局內人爆料行業黑幕,因為確實總有太多弊病根本無需證偽。但思維的跳躍和閱讀的碎片化使人會喪失基本的判斷力和對真相的追求,因為反對者的“天然正義性”會讓他們只注重發泄情緒本身而忘記思考事情的原委。這次事件中尤為明顯。
比如,對一個人的作品不僅看世俗評價,或許更看其在文化傳承上的過渡作用和在藝術嬗變中的革故創新。
再者,就實質而言,評委是湖北作協請來的,如果評選結果真的有問題,該被問責的首先應當是湖北作協,應當改進評選機制、實現真正的程序正義并自罰識人不明。
有人說作家應當是一個國家的良心,正如文學與國家關系的言意之辨:一旦國家沒有了文學,社會就像一輛夜間行駛的車輛,而車燈則被蒙上了。
復盤整個方柳之爭,反映出當下文學的某種舉步維艱。并非所有的道德問題都要歸咎于資本逐利,也不能推導出社會轉型期道德普遍滑坡的結論。社會是由個體組成,個體的道德狀況其實就是社會百態的最真實的捕捉。在有關“魯獎”這些年的事件中,幾乎每一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維護著自己所認為的公平正義。
如何調節輿論監督與對輿論的自身監督,如何減少輿論暴力和輿論盲從,如何擺正政治宣傳和文學創作的關系,如何理順出版審查、意識形態和創作自由的紐帶,這無疑是文學挽回急劇下降的社會公信力的突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