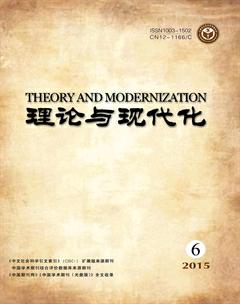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經驗及啟示
張世飛++++曾慶桃
摘 要: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中,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歷史經驗,如理論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根本原因、充分利用多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保證、追求傳播效果最大化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然要求等。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不僅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能夠實現大眾化的關鍵,更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一步推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5)06-0005-06
在“五四”時期,中國還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這決定了不可能運用常規條件下的國家機器、宣傳陣地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但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五四”時期卻使馬克思主義不僅在當時的知識界、工農群眾中較為流行,而且在當時的北洋政府及基層軍隊內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19年6月23日,北洋政府內務部在給陸軍部的一封信中說:“準陜西督軍電稱,陜省近日郵件中發現一種印刷品署名士兵須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詞意不外提倡共產及無政府主義,并詳述法國式革命與俄國式革命之區分……”[1]個中經驗,值得深思。
一、理論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根本原因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經驗可以從很多角度去概括。如從傳播方式來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創辦報刊、發表文章、翻譯經典著作等形式,向青年學生和工農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從傳播受眾及效果來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注重針對不同層次的受眾群體,努力追求傳播效果的最大化等。但是,從傳播內容來看,能夠真正滿足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才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實現大眾化的根本原因。①正如毛澤東1949年9月16日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中所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2]那么,馬克思主義是怎樣滿足了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來分析。
(一)唯物史觀為中國社會改造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
李大釗是中國傳播唯物史觀的先驅。在他的主持下,《晨報》副刊在1919年5月5日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刊載了5篇馬克思主義的譯著,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河上肇作,淵泉譯),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1919年9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號和第6號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3]概述唯物史觀的要點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另外,《新青年》除發表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外,還發表了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評》、起明譯的《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陳啟修的《馬克思研究》、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等文章,這些文章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介紹和闡述。后來,1920年1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主張運用唯物史觀考察中國社會:“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4]楊匏安等人也注意到唯物史觀的學習和宣傳,1919年11月,他在《廣州中華新報》連續刊載的《馬克斯主義》中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了詳細的解說。1919年至1922年間,李達在《民國日報》發表了《什么叫社會主義》等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而且還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唯物史觀的宗教觀》等多部唯物史觀的著作。1921年后,陳獨秀也撰寫了《馬克思學說》等介紹和宣傳唯物史觀的文章。總之,“五四”期間,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唯物史觀是改造中國社會的強大思想武器,故在介紹和宣傳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始終把理論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需要放在第一位,始終把它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法論。
(二)馬克思經濟學說揭示了社會變化的規律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了學習和傳播,而且對馬克思經濟學說也有一定的研究。1921年3月,李大釗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中指出:“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3](277)闡述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同時也非常希望中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下,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另外,1921年1月,陳獨秀在《社會主義批評》一文中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認為“現代分配方法的缺點”就是“工人血汗所生產所應得的,被資本家用紅利底名義掠奪去了。”[5]1922年4月,陳獨秀又在《馬克思學說》一文中,重點闡述了剩余價值,并指出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而且,1920年10月,《國民》雜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譯載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此后,一些闡述介紹《資本論》的通俗讀物也開始翻譯刊載或出版,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介紹了《資本論》第一卷。從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論述來看,盡管他們的理解有不夠精當之處,但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還是有一定研究的,對中國社會變化的規律也有了較準確的認識。
(三)科學社會主義解決了中國社會革命的領導者、依靠力量、道路等問題
1919年9月,《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從多角度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入分析。例如,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方面,他認為階級以及階級斗爭產生的原因是剩余勞工,進一步指出中國的階級現狀及如何發動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斗爭。關于政黨和政黨聯合方面,李大釗認為是國家政治發展進步的表現,總結了中國將要建立新型政黨應該具備的三個特點:“平民勞動家的政黨”、“強固精密的政黨”、“與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相呼應”,[3](19)即提出必須在中國建立我們自己的無產階級政黨。同時,他在1923年的《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中發出號召,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組成“民主聯合陣線”。關于革命和專政方面,李大釗系統地從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方式以及革命的領導權及力量角度分析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政權的觀點。關于民主和法制方面,李大釗對民主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積極提出民主的實現途徑,還提出“實事求是”、“以民為本”[6]的法制觀。這一時期,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等早期共產黨人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主張發動工人運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總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從階級斗爭入手,證明社會革命的必要;又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證明社會革命的激烈;再從經濟學的角度說明社會革命產生的深層次的原因。這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最初的過程或模式,有力地證明了社會實踐對理論的迫切需要。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期才得到廣泛的傳播。
二、充分利用多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保證
思想和理論要想快速宣傳,采用正確的傳播途徑是必不可少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利用多種傳播方式,為探索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立下了篳路藍縷之功。
(一)創辦無產階級報刊,使其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1919年5月,“五四”時期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刊物《新青年》設立“馬克思研究”專號,李大釗任主編,該專號主要是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1918年12月,陳獨秀為配合《新青年》的政治斗爭,在北京創辦《每周評論》,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和世界革命動態,該刊曾刊發了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等重要文章。1919年1月,《國民》雜志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正式出版,于第2卷第1號發表了李大釗的《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等文,第2卷第2、3號連載了《馬克思歷史的唯物主義》的譯文,第2卷第4號發表了《蘇維埃俄國底經濟組織》、《蘇維埃俄國底新農制度》等文章。1919年5月5日,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晨報》副刊也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并從5月5日到11月11日發表了5篇論著,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勞動與資本》、《馬氏資本論釋義》等,使得該刊成為除《新青年》外的又一個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此外,“五四”期間,李大釗還協助一些進步青年創辦《新潮》、《少年中國》、《新生活》等報刊。1920年11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版了《勞動者》,把領導工人運動作為中心工作。同月,《共產黨》月刊在上海創辦。1921年7月,李大釗在北京創辦《工人周刊》,后成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報。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創辦這些報刊,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二)發表大量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8年至1919年,《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先后發表了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進行宣傳。1919年8月,《每周評論》第35號又發表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對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闡釋。同年10月李大釗在《國民》雜志社成立周年紀念大會上提出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思想分析“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期間,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李達、楊匏安等人也撰寫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據統計,“五四”時期發表在各類報刊雜志上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就多達二百多篇,這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是十分少見的。有人評論說:“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云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7]可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發表大量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使更多的人了解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后,國內掀起了一股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學習熱潮,大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被翻譯和出版,如1919年4月,《每周評論》第十六號“名著”欄刊登了《共產黨宣言》節譯——《無產者和共產黨人》。[8]總體來說,“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直譯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10月新青年社出版李季譯、蔡元培作序的英國人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1921年1月武漢的利群書社(惲代英創辦)出版了惲代英翻譯德國人考茨基著的《階級爭斗》,1921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李達翻譯德國人考茨基著的《馬克思的經濟說》和荷蘭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觀解說》,等等。二是轉譯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19年5月北京的《晨報》刊登了陳博賢翻譯的日本河上肇作所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淵泉翻譯的柯祖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1920年8月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陳望道轉譯日文《共產黨宣言》,等等。三是轉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19年11月北京《國民》雜志第2卷第1號刊登了李澤彰轉譯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920年10月《民國》雜志刊登了費覺天轉譯自俄文版的《馬克思底資本論自敘》(即《資本論》第一版序言》),1923年8月北京《今日》第3卷第2號刊登熊得山節譯自俄文版的《國家的起源》。總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五四”時期翻譯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發表、出版,使更多的中國人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四)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激烈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從1919到1922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也遇到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干擾,主要包括“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等思潮。如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倡實用主義以及溫和的改良主義,由此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論。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對胡適的主張進行了回擊,先后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批駁胡適。李大釗在給胡適的復信中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3](3)其實這是李大釗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萌芽。之后,李達等馬克思主義者又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梁啟超等人就“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無政府主義”等問題進行激烈論戰。李達在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1號發表了《談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在《共產黨》月刊第四號發表《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文章,對張東蓀、梁啟超等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進行批駁。后來,還有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蔡和森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何孟雄的《發展中國的實業要采取什么方法》等文章,都是與一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論戰。
此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還利用大學課堂、講座、論壇、圖書館等形式,在大學校園內向進步知識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如在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利用書刊的借閱傳播馬克思主義,使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為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毛澤東、周恩來等進步青年開始走上革命道路。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在北大當圖書館助理的時候,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9]
三、追求傳播效果最大化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然要求
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傳播過程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注重傳播內容和形式,還十分注重針對不同受眾的特點,追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效果最大化。
(一)注重在進步學生和青年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引領他們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利用各種形式,向進步學生和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正直進步有為的青年。其中,受李大釗影響最大的是北大青年學生,如劉仁靜、袁玉冰、譚平山、鄧中夏、蕭一山、羅章龍、任國楨等。這些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又在全國撒下革命的火種。例如,江西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員袁玉冰就深受李大釗等早期共產黨人思想的影響,五四運動后,他成為江西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21年6月,他創建了江西地區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并主編《新江西》,開設“介紹進步書刊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1922年9月,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期間結識了革命先驅李大釗。不久,經李大釗的介紹,入學不久的袁玉冰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袁玉冰把革命的火種帶到江西,為江西黨團組織的建立和革命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注重在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
除向進步學生和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外,李大釗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還通過創辦刊物、舉辦工人業余學校等形式,向工人群眾灌輸馬克思主義。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上海首先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些組織一建立,就開始了在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一是改組《新青年》。《新青年》自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號始,以嶄新的面貌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二是使《覺悟》成為共產黨的外圍刊物。通過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團結進步知識分子。三是出版黨內刊物《共產黨》。除刊登馬克思、列寧的一些重要著作外,還分享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建黨的一些經驗,下發給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閱讀。四是培養干部,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外國語學社”從1920年夏至1921年冬,培養了一批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送來的干部。1920年,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也先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五是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1920年8月,《勞動界》周刊在上海問世,并積極發動工人寫稿。該刊在勞動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已把馬克思主義新思想傳播到工人中去。后來,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幫助下,上海機器工會、上海印刷工會等組織也相繼成立。②六是指導各地進行建黨工作。1920年6月,陳獨秀、俞秀松等人決定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領導人(書記)。在陳獨秀等人的指導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和青年團的組織相繼建立。
(三)通過創建各地黨組織,最終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活動有:一是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要搜集馬克思學說的德、英、法、日各種文字的圖書資料,并加以編譯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就逐漸成為黨的外圍組織,發揮著吸引群眾擴大影響的作用。后來會員發展到120余人,不僅有學生,而且有工人參加。二是開展工農運動。1920年11月7日,《勞動音》周刊創刊,以提高工人的覺悟,促進工人的團結,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為宗旨。1921年5月1日,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幫助下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此外,北京共產黨組織還進行了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指導北方各地的工人運動及幫助建立革命組織等工作,對北方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3月,鄧中夏、劉仁靜、張國燾等北大青年學生秘密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10]跟其他進步團體如“新潮社”、“國民雜志社”等一樣,視李大釗為導師。“黨支部與青年團和其它一些革命團體常在這里集會活動……”[11] 1920年12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校內發起公開簽名,主張“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12]并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影響,上海、廣州、濟南、武漢、長沙等城市也先后成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社團組織。比如,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創建共產主義小組和開展工人運動。1920年秋至1921年,上海、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但性質相同,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后來,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又積極發展下屬組織,成立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們分別在全國各地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另外,也創立工人刊物、學校、工會組織等,不斷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工人運動。這些,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且直接促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結 語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寶貴經驗,不僅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礎,對于當前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理論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的經驗啟示我們,理論必須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是當前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根本動因。充分利用多種方式的歷史經驗啟示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多種傳播方式,這是當前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保證。追求傳播效果最大化的歷史經驗啟示我們,必須加強對受眾的分析,使傳播效果最大化,這是當前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然要求。
注釋:
①彭明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并把它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夠迅速傳播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另兩個條件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參見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頁。
②參見《中共上海黨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站。
參考文獻:
[1]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1001)3227[Z].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
[4]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7.
[5] 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38.
[6] 張世飛.李大釗: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先驅[J].政治學研究,2010,(4).
[7]潘公展.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J].東方雜志,1921,(4).
[8]每周評論,1919,(6).
[9]斯諾.西行漫記[M]. 北京:三聯書店,1980.127.
[10]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N].北京大學日刊,1921-11-17.
[11]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史事綜錄[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482.
[12]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通告[N].北京大學日刊,19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