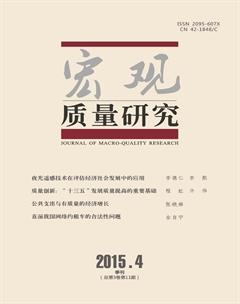直面我國網絡約租車的合法性問題
摘要:我國網絡約租車市場發展迅猛,對其合法性的爭議也隨之興起。但當前相關討論存在著忽視實踐多樣性和誤讀國外經驗等問題,有必要予以澄清。論文總結了我國網絡約租車實踐的多種模式,并對照美國法相關經驗,以我國現行法為依據探討了各模式的不同發展空間,進而從風險規制角度探討了建構我國網絡約租車制度所應防范的交通安全、信息安全、社會穩定等不同風險,主張基于輔助性原則和比例原則選擇具體規制方式。
關鍵詞:網絡約租車;風險規制;輔助性原則;比例原則
一、引言
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在手機終端啟用特定軟件即可方便操作的網絡約租車服務(以下簡稱“網約車”)成為可能;其以便利快捷而受到消費者(乘客)和服務提供方(司機)廣泛歡迎的同時,也引發了激烈的法律爭議。
在我國,網約車軟件于2011年出現,并迅速風行于市。早在2013年,交通運輸部即頒布《關于規范發展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的通知》(交運發[2013]144號)和《關于改進提升交通運輸服務的若干指導意見》(交運發[2013]514號)表態鼓勵“創新電召服務模式”,“推廣手機智能召車軟件,建立多層次、差異化的運輸服務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出行需要”等。但是,擬議中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迄今未見公之于眾。各地政府則態度不一:廣州市政府牽頭與企業合作打造網約車平臺,上海市政府則和企業合作研究網絡約租管理試點方案;與此同時,私家車提供的網約車陸續在北京、南京、大連、沈陽等地被明令禁止,多地交管機關以“非法營運”為由查處從事專車服務的私家車主,并引發糾紛。據報道,繼2015年4月濟南中院受理被罰車主狀告交管執法機關的“專車第一案”之后,北京海淀法院于2015年9月受理了一起受處罰專車司機狀告約租車平臺的案件;除此之外,也出現了因租賃非營運車從事專車營運發生交通事故而保險公司拒絕理賠引發的訴訟。這些新型案件顯示出,網約車法律定位不明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已經給社會生活造成了現實的麻煩。
二、經驗觀察:我國網絡約租車的不同類型
雖然不過短短數年,網約車在我國實際上已經先后現了若干不同的運營形態,至少包括了如下六種不同的類型。
最少爭議的是,的士司機和乘客自愿使用手機約車軟件通過網絡平臺完成約租車。這種網約車形態,只是運用一種新的技術手段更為便捷地完成了傳統的“打車”活動而已。乘客從傳統的路邊招手改為在智能手機上按鍵發出打車意愿,的士司機則從傳統的“招手即停”或“接受電召”改為按鍵搶單。從法理來看,這種應用只是使的士司機和乘客能夠更加方便快速地找到彼此并達成合意,并未改變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主體以及雙方核心權利義務:的士司機仍然是像以前一樣按乘客意愿將其送達目的地,并仍按傳統的計價方式(起步價加按里程和時間所計價格)收取費用。這種形態不僅未引起合法性質疑,還受到了各方歡迎。不少傳統出租車公司主動仿效,結合原有的電召平臺,開發自己的約車軟件,以提供網絡約租車服務。
隨后,很快出現了出租車公司要求旗下的士司機必須安裝特定約車軟件的做法,甚至在旗下車輛統一配發預裝約車軟件的用戶終端并要求不得卸載,引發一些不習慣智能手機使用的司機不滿。以法理來看,此時種情況已經涉及出租車公司與司機之間勞動合同或經營承包合同關系內容變動,但對乘客而言,涉及的法律關系及權利義務仍無實質變化。
在這兩種形態中,網約租車服務的提供者仍是傳統的出租車。對這兩種形態網約車合法性的質疑主要是一些約車軟件所提供的“加價”功能。在軟件企業看來,當無出租車愿意應答(如高峰期或偏遠地段)而乘客又急需用車時,讓乘客選擇加價(付小費)以吸引出租車司機“搶單”是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價格杠桿,合理分配有限出租車供應的有效方法,能夠使最有需要的乘客盡可能快地打到車。但是,這種“價外加價”的做法,違反了出租車實施統一定價和禁止議價等既有規定,因此被一些地方政府的交管部門明確否定(湯旸,2013;陳琳,2013)。
使事情發生重大變化的,是軟件企業拋開出租車公司,與汽車租賃公司和勞務派遣公司合作向乘客提供網絡預約租車服務。即所謂的軟件企業(提供平臺)、汽車租賃公司(提供運營用車)、勞務派遣公司(提供司機)與乘客的所謂“四方”模式。這種情形下,網約租車服務的提供者不再是傳統的出租車了。新的法律主體用新的方式達成了合意。就法理而言,有執照的汽車租賃公司向有需要的客戶出租車輛,有執照的勞務公司向有需要的客戶提供司機,均為獲得正式許可的活動。至于軟件公司為三方提供平臺使乘客得以同時就租車和雇司機達成合意,也并未違反禁止性規定——事實上,業者之所以采取這么復雜的操作模式,正是為了不違反“汽車租賃不得配備駕駛人員”這一明文規定。因此,此種形態的網約車,合法性雖受到一些質疑,但仔細推敲起來,可以說并無問題。
使問題真正復雜化的是,私家車主帶著個人車輛(登記為“非營運”)加入了網絡預約車服務。不過,議者很少注意到的是,同樣是私家車從事網絡預租車,又有不同形式。
第一種是所謂的“順風車”或“拼車”,即私家車主和“搭車者”使用約車軟件通過網絡達成合意,車主自駕而搭車者順路同行并向車主支付商定費用(多稱為“分攤費用”)。因為個人汽車是屬于私家車主的財產,車主作為合法的財產所有者,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理論上和一般社會觀念中,這種搭便車并不屬于“經營”,因而并不存在獲得經營許可問題。如上海市政府曾頒布通告,區分了“收費搭載乘客行為”和“非法客運經營活動”,前者被上海市政府2010年4月第32號令(《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查處機動車非法客運的通告》)認為是合法的民事交易活動。在拼車軟件出現之前,這種搭便車活動即久已存在,使用拼車軟件達成搭便車的合意,并未改變車主及搭便車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其合法性也應無問題。當然,這種合法的民事交易活動與“非法營運”的界線在理論上是清晰的,在實踐中卻存在難以分辨的邊緣情形(桑本謙,2011)。不過,在當前有關網約車爭議中,這種形態因為規模較小影響不大,并未引發多少關注和議論。
私家車加入網約車的第二種形式是,私家車主將自己的車“掛靠”(不實際過戶)在汽車租賃公司,同時自己“掛靠”在勞務派遣公司,從而形式上滿足前述“四方”模式,只是結果上看,汽車租賃公司提供的車正好屬勞務公司提供的司機所有。事實上,這種以協議方式將私家車交給租賃公司“代管并出租”的“掛靠”,早在網約車軟件出現之前即已存在。這種“假”四方模式,違反了一些地方“租賃車輛應當為租賃經營者所有”的明文規定。有不少地方在確認前述四方模式的合法性的同時,明令禁止此種“掛靠”(葛妍,2014)。
私家車加入網約車的第三種形式是經軟件企業允許其接入其提供的打車平臺向乘客提供預約車服務,包括所謂“專車”(較貴)或“快車”(較便宜)。其中,“快車”無需向軟件企業付費,而“專車”需向其交納一定的管理費(通常是提成)。是否應當基于“非法營運”而查處以這種形式提供服務的私家車主,是我國當前有關網約車爭議的焦點問題;相較前幾種形態,這類網約車涉及的法律關系也最為復雜:除了私家車主這一新增法律關系主體之外,軟件企業顯然也已經超出單純提供的“信息服務”的角色而成為權利義務并不明確的一方主體。
三、現行法下我國網絡約租車的合法性疑難
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上述至少六種網約車的不同形態,其中前五種形態在現行法下合法與否的評價較少爭議:未改變傳統打車活動主體及關系的的士司機使用打車軟件、尊重現行許可制度的四方協議模式和作為合法民事交易活動的“拼車”,可認定為合法;而的士“價外加價”和私家車“掛靠”汽車租賃公司,則被認定為違反了現行規定。引發最多疑問的,是最后一種模式,即私家車直接接入約車平臺提供約租車服務。在此集中分析最后這種模式即私人網約車服務的合法性疑難。
(一)無法借鑒的美國經驗
在美國,網約車于2010年興起,直接沖擊了傳統的出租車行業,并引發相關法律訴訟。在紐約, 電召車服務協會曾狀告紐約市政府和紐約市出租車委員會,要求停止網約車的啟用,法院判決駁回了其訴訟請求(Black Car Assistance Corp. v. City of New York, 110 A.D.3d 618 (2013))。目前,有一些州開始通過行政規章甚至議會立法正式承認網約車合法性,同時明確了對其的監管規范,如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2013)和科羅拉多州(Colorado Legislation,2014);還有一些地方,以謹慎觀望態度試探著部分允許網約車的運營,如西雅圖市2014年3月制訂的試行規則中對網約車施加數量限制(王軍,2015)。
在美國,私家車提供的網約車服務目前是以約租車而不是出租車的定位而合法化的。因為美國法區分了傳統出租車與約租車服務:傳統出租車可以巡街攬客,而提供電話等方式預約租車服務的,不可巡街攬客。兩種租車服務實施不同的準入許可和從業規范(王軍,2015)。在這種既定法律框架下,網絡出租車更接近約租車而不是巡街的出租車。因此,Uber等公司在美國多地主張,網約車不巡街攬客不是出租車,因此不受(巡街)出租車相關苛刻法規拘束(財新網:2015)。
但是,在我國,要通過這種美國式策略(即強調網約車不是出租車)來使網約車避開出租車運營相關法規,看來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國就準入許可和從業規范來看,并不存在出租車和約租車的美式區分(《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出租汽車實行揚手招車、預約訂車和站點租乘等客運服務方式”)。傳統上,我國巡街的出租車,同時也可接受預約——在網絡預約普及前,主要是通過電話預約(即所謂“電召”)。而且,如前所述,在移動互聯網技術普及后,傳統出租車比私家車更早廣泛采用了網絡約車軟件,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這種應用看來受到了各方歡迎。若要求傳統出租車司機放棄這一技術,既無合法依據,也無合理理由,并且難以監督實施。事實上,一些出租車公司曾明確要求自己的司機停止使用第三方約車軟件,但因為遭遇強烈抵制且監督實施成本高昂而不得不放棄。考慮到這些因素,通過傳統出租車業務與約租車業務的分立來解決網約車這一新興業態的法律定位問題,是美國“特色”經驗,我們無法簡單照抄。
就此而言,我國交通部于2014年9月頒布(2015年1月1日實施)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其中第三十條規定,“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只能通過預約方式為乘客提供運營服務,在規定的地點待客,不得巡游攬客”,是一條未曾考慮我國出租車經營的歷史和現實,生搬硬套美國法成規的規定。而且,在預約出租和巡街出租并不存在不同的準入和從業規范的前提下,此條規定在實際實施中只意味著:“已經接受預約的出租汽車駕駛員在完成預約服務之前不得再巡游攬客”,這與美國法的相關規定,只是字面相似,而制度意涵卻大相徑庭,并不能解決我國網約車的法律定位問題。
(二)探索中國路徑
就經營模式本身而言,私家車提供的網約車與出租車提供的網絡約租服務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前者司機是兼職司機而后二者是專職司機;前者所用車輛是私家車而后二者是營運專用車輛。這兩種不同,正是其在我國多地被執法部門認定為“非法營運”的根據。因為在我國現行出租車運營許可制下,合法從事包括約租在內的出租車營運,前提條件是三證具備:①經營資格證(即出租汽車經營許可);②駕駛人員客運資格證;③車輛營運證(《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以個人車輛(非營運車輛)從事網約車的私家車主,并不符合我國現行出租車許可制度中的這些規定。
但是,將私家車通過網絡平臺所提供的客運服務與傳統出租車服務中的電召車歸為一類,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中,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法律解釋。
我國現行法律區分了包括“出租車”“汽車租賃”和“班線客運”。出租車與汽車租賃的區別在于,汽車租賃只提供汽車而不提供駕駛人員。出租車與“班線客運”的相同之處是同時提供汽車和駕駛人員,區別則在于班線客運應有“明確的線路和站點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八條)。一個例外是《道路運輸條例》所規定的“包車”,和出租車一樣同時提供汽車和駕駛人員,一樣“應當按照約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線路運輸”(《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十九條),但并不屬于出租車,因此不需要獲得出租車經營許可。因此,這里留下了一個可能的解釋空間是,私家車提供的網約車,是否可以視為“包車”?當然,按照現行法律,包車服務提供者,同樣要獲得客運經營許可。但在現行法框架下,相比出租車行業所受總量控制、價格管制和準入限制等全方位管控,包車服務行業所受規制明顯要少得多。
2014年7月,國家交通運輸部正式印發了《關于促進手機軟件召車等出租車電召服務有序發展的通知》。該通知規定,打車軟件將逐步納入統一召車平臺管理。考慮到私家車提供的網絡車定性上可能有別種解釋,嚴格說來,這一通知僅適用于出租車提供網絡預約服務的情形,并不能當然涵蓋私家車使用約車軟件提供“包車”服務的情形。
換句話說,就同時提供汽車和駕駛人員、按約定起點終點和線路運輸而言,私家車主提供的網約車,與傳統的出租車和傳統的包車,均有共性——整體比較而言(如表1所示),甚至可以說與傳統的“包車”相似度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為何要選用更為嚴格的出租車相關規范而不是寬松得多的包車相關規范規制私人提供的網約車服務?規制者對此負有論證責任。
表1私人網約車與傳統出租車及包車的對照
傳統出租車 傳統包車 私人網約車
服務內容 按約定將乘客送達目的地
合意方式 電話預約或招手即停 電話預約或機構所在地(不巡街攬客) 網絡預約(不巡街攬客)
車型 車型統一、大眾化定位 車型不一,豪華車為主 車型不一
價格 統一定價 市場價 統一定價或市場競價
駕駛員 專職 專職 兼職
但是,本文也并非主張私人網約車就是現行法規范上的“包車”。因為,正像私人網約車與傳統出租車存在重要差異一樣,仔細對比私人網約車與傳統包車,也會發現它與傳統的“包車”仍有重要差異。
概括而言,私人網約車與我國現行有效的實證法規范上已有相關規定的傳統“出租車”“汽車租賃”和“班線客運”和“包車”等全部租車運營形態均存在重要差別。換句話說,私人網約車不像前五種網約車模式那樣依據現行有效的規范即可明確其合法或不合法。就現行法規范中找不到恰當的對應物而言,私人網約車已經超出了現行法規范可以覆蓋的范圍。因此,論者在做基于實證法分析和判斷時,不宜簡單地宣稱它是合法的或者是不合法的。
(三)網約車的特殊性
試圖依據現行法律條文對私人網約車的合法性進行判斷,或者試圖依據現行法框架對私人網絡車實施規制的論證,很難在嚴格意義上完成。因為如表1所示,私人網約車,客觀上與傳統的出租車和包車有相同之處,但也有既不同于傳統的“出租車”,也不同于傳統的“包車”的特殊性。質言之,私人網約車之所以能作為一種自發的市場活動而興起,正是因為它與久已存在的傳統出租車或包車有著實質的差異,滿足了傳統出租車或包車不能滿足的市場需求。歸根結底,其新穎性源自所有網約車服務形態所共有的因素,即對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新應用;而這一因素,是現行法律相關規定制訂者沒有考慮過也不可能考慮過的因素。
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客運方式,網約車的運營依賴于前所未有的技術手段,方便快捷地將分散的供給信息與同樣分散的需求信息互相匹配,大大節省了供需雙方達成交易的成本,并因此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在舊的技術條件下不得不“閑置”的社會資源。具體說來,這種技術不僅使既傳統的士司機減少了空駛(減少了尾氣“排放”),還使私家車主進入約租車服務成為可能:若無網絡約車軟件的出現,有自己職業而只能利用零碎業余時間從事約車服務的私家車主,與潛在的顧客取得聯系并達成合意的成本將過于高昂;若無GPS、電子導航等技術應用,非專職司機也很難克服“路不熟”的障礙而提供對乘客而言“可接受”的運送服務。
表2私人網約車與“黑車”的比較
“黑車” 私人網約車
服務內容 按約定將乘客送達目的地
合意方式 路邊拉客 網絡預約
車型 車型不一 車型不一
價格 不透明的“黑市”價 透明的統一定價/市場競價
駕駛員 專職或兼職 兼職
過程監管 無 軟件全程實時監測
查證追責 難以查證,難以追責 可追溯記錄,容易查證和追責
進而言之,這種對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也使得私人網約車與那些未取得營運許可即以私人車輛從事非法客運服務的傳統“黑車”有了實質性的差別(如表2所示):傳統“黑車”屬地下交易,駕駛員和車輛的信息均不透明,乘客方議價成本高且以現金支付,監管和追責均十分困難。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私人網約車,駕駛員和車輛信息軟件均有記錄,且向乘客即時顯示;交易和支付全程均有網上實時追蹤和記錄,便于監管和追責。
四、從風險防范角度看我國網絡約租車規制之道
綜上,在現行法框架下,我國當前形形色色的網約車營運模式,大部分是合法的。合法性有疑問的,主要是出租車使用網約軟件時的加價功能、違規“掛靠”和私人網約車服務。其中,前二者合法性判斷較為簡明(可以確定違反了現行規定)。私人網約車服務,情況則有所不同:它是在新的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出現的“全新”現象,在既定立法框架中難以歸類。這些都是從既定實證法規范出發并基于既有規范的分析,并未涉及既有規范本身是否合理。考慮到前面分析所援引的既有規范是人為選擇和設計的,本身未必合理;特別是,即使在制定時合理的規范,也可能隨著社會變遷而成為不合理的;因此,還有必要討論,在新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對網約車這一新興市場交易模式,實施規制及選擇特定類型規制方式(當存在其他選擇時)的理據。
如前所述,新興的各種網約車,區別于各種傳統約租車形態的關鍵因素,在于對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應用。眾所周知,人類文明的發展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對于一項明顯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的新技術,原則上應予支持鼓勵而不是妨礙甚至打壓。但是,硬幣的另一面是,科技的發展應用往往伴隨著需要警惕和防范的風險,這些風險中有一些無法以個體化方式應對,需要通過政府規制等集體化方式予以處理(金自寧,2014)。
(一)伴隨著網約車的風險
伴隨著網約車的風險,可以分為新舊兩種。
舊的一類是小汽車出行方式的固有風險,指以傳統形式從事小汽車客運服務亦存在的風險。主要是交通安全風險,即只要是小汽車出行方式就內在地伴隨著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防范此類風險已有較成熟的經驗,包括了事先確定的安全標準和責任保險制度。
從已有經驗來看,防范交通安全風險的技術標準主要指司機和車輛兩方面的標準。即司機應當具備相應的駕駛技能,車輛本身也應具有良好性能,能夠滿足客運服務的技術要求。這些技術要求在實際操作中會轉化為更為具體明確的一系列標準。如對司機駕齡的要求、對從業車輛的行駛年限和里程的限制,強制檢測和強制報廢的技術標準等。
同時,考慮到此種風險不可能削減為零,在采取了可能的事先防范措施后,交通事故仍有一定的機率會發生。許多國家均確立了交通事故責任保險制度,以保障乘客和第三方在交通事故發生后能得到及時救濟。
移動互聯網的出現,使得預約車合同的合意可通過網絡達成,但預約車合同的實際履行,仍在線下以傳統方式(即小汽車出行)完成。因此,傳統上與汽車客運相關的風險仍然存在。因此,在網約車服務中,此類風險仍需防范,也就是說,適用于傳統客運服務領域里的司機和車輛相關安全標準和責任保險制度應當適當延伸適用于網約車。
除此之外,傳統的客運相關規范中還有一些其他要求也是著眼于交通安全的,如關于連續駕駛時間的限制,著眼于避免司機疲勞駕駛(《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二條),也應適用于網約車。事實上,由于移動互聯網技術使得網約車全程記錄和實時監測成為可能,禁止司機疲勞駕駛相關規范的監督實施成本將大大降低。
網約車因為應用移動互聯網新技術而“新增的”風險,則主要是個人信息安全風險問題。在使用約車軟件時,司機和乘客都必須向平臺提供一定的個人信息,這些信息中有一些,如手機號和所在位置,不僅僅是平臺掌握,對司機和乘客而言也是透明的。這些個人信息的提供和透明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司機與乘客之間的信任從而提高了交易達成的可能性,并方便了約車平臺作為第三方對交易過程實施監督(約車平臺大多受理來自乘客和司機雙方的投訴,并會對“違約”者實施包括“驅逐出平臺”在內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面也伴隨著個人信息被濫用和泄露的風險。如已經出現網約車司機電話騷擾乘客的事例(李妍,2015)。特別是,當約車軟件與電子地圖(精準定位、即時追蹤)和電子支付(操作簡易即時到賬)相結合,一方面提高了用戶體驗,另一方面也擴大了乘客個人信息安全問題。
相對于小汽車交通安全方面的風險防范,網約車中的個人信息安全相關風險的防范,當前并無現成經驗可用。事實上,互聯網技術應用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方面的風險防范是一項全球性難題。我國迄今并無一部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法,個人信息安全保護主要依賴其他法律法規的原則性或相關性規定,存在較多空白和含糊不清的地帶。在此背景下,網約車中個人信息安全的諸多隱患,值得特別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風險有些因為“網約”新技術的應用而有所降低,有些反而升高。前者相比同樣是私家車主提供客運服務的“黑車”,私人網約車信息透明而易于監管;就此而言,不宜將私人網約車與黑車同等對待。后者如載客途中使用打車軟件會分散司機的注意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害乘客和道路安全;就此而言,禁止行駛途中使用打車軟件的地方規定有其正當性。
(二)衍生的社會穩定風險
網約車是在新的技術條件和社會經濟背景下產生的新興客運服務模式,與舊的行業秩序之間難免發生沖突,從而形成社會矛盾,引發社會穩定風險。這種風險有多種可能的來源:傳統出租車受到新的競爭者挑戰,出租車公司和數量龐大的司機既得利益受損,可能采取抵制行動;同樣數量龐大(并在不斷增加)的從事網約車服務的私家車主,也可能因認為傳統行業壟斷利益和政府對新技術應用的抑制不合理而采取抗議行動。
但是,強調有必要謹慎防范社會穩定風險,并不是主張一成不變地維持現狀或保守特殊群體的既得利益。在此,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同樣應當明確自己“裁判者”而非“運動員”的角色。這就意味著,面對市場自發涌現的新技術應用,政府的任務,并非直接介入市場運作,在新舊技術、新舊經營模式的競爭中決定何去何留,而是維護公平競爭:既為創新留下基于公平競爭的發展空間,也要公平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具體而言,一方面,對新技術應用加以限制的正當理由,和政府對私人自主自治領域實施干預的一般理由一樣,也應基于社會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特定個人或特定行業的特殊利益。網約車沖擊了傳統的出租車行業,使從業者(包括出租車公司和的士司機)利潤減少甚至由盈轉虧,并不是政府限制網約新技術應用的正當理由。若是政府部門為了保證自己所組建平臺的業務量而禁止對其形成直接業務競爭的第三方平臺,則是赤裸祼“與民爭利”,亦是定位嚴重錯誤。就此而言,交通運輸部于2014年7月9日所頒《關于促進手機軟件召車等出租汽車電召服務有序發展的通知》,要求各地方交通運輸主管部門“著力營造開放、公平、規范、有序的健康發展環境,積極鼓勵支持各類出租汽車電召服務方式協調發展,推動建立高品質、多形式的出租汽車服務體系,保障人民群眾享有均等化出行服務,為人民群眾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并在支持城市建立出租車服務管理的信息系統平臺的同時,具體指出“平臺運轉不得影響手機召車軟件正當功能和良性競爭”,反映了對政府職能定位的清醒自覺。
另一方面,傳統出租業所受沖擊應當區別不同情況予以妥當處理。如果出租車公司和司機預期收入因為正常的“市場風險”而減少,則應由作為市場主體的投資者自行承擔。如果是因為傳統的出租車管制制度的不合理導致出租車在與網約車競爭中不公平地處于不利地位,則應通過變革傳統制度不合理之處來解決。事實上只要改變傳統出租車的特許制度,同樣應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專職出租車服務,相對于私人網約車而言具有明顯的專業優勢,二者公平競爭的結果最有可能呈現出專職出租車為主,私人網約車為補充(提供共享服務、彌補高峰期或偏遠路段運力不足)的發展格局。
最后,如果因政策變化導致了出租車業者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損失,則政府有必要給予適當補償。這種情形應限于政府推出新政策時對舊政策執行遺留問題的處理,如:政府向企業或個人有償出讓出租車經營權時附有限制許可總量的承諾,而當新的技術和社會條件出現,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實施放開數量限制或大幅度降低準入門檻等新政,導致出租車經營者資產明顯貶值。在這個意義上,杭州市在放開出租車牌照的數量及價格管制同時退還當初收取的出租車經營權出讓金,是具有相當合理性的過渡辦法。
(三)選擇如何規制
確認存在需要防范的風險之后,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是選擇如何規制。就輔助原則(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而言,只有“特定公眾和組織無法自主實現某種目標時,高一層級的組織應該介入,但僅限于出于保護他們的目的;并且,高一層級社會團體或者政治組織只能處理那些低一層級的社會團體或者政治組織無法獨立處理而高一層級的機構又能更好完成的事務”(熊光清,2012),因而并非所有的風險都需要政府出手;就比例原則(余凌云,2002)而言,在確認需要政府干預時,也需要在多種可能的規制方式中選擇真正合乎比例的某一種或某幾種。
我國實證法上,這種選擇之基本精神的最佳體現(劉莘,2006),當推《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范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二)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三)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
網約車這一新興客運活動的風險規制,也可以運用《行政許可法》第十三條類似的層次來分析政府應當如何具體確定對網約車相關風險的規制。
首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政府不應干預。在網約車活動中,個人通過約車軟件完成拼車和搭便車等民事活動,就屬此種情形,參與者作為完全責任能力的民事主體,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訂立和履行合同,應當風險自擔責任自負。若非存在欺詐脅迫或違約等情形,國家公權力機關無需也不應介入。
第二,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政府應當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優勢。網約車軟件的“加價”功能,就屬此種情形。價格是競爭市場上供需雙方找到對方的信號,它是市場發揮有效分配有限資源功能的關鍵所在。對價格的干預必然帶來市場機制的失靈。網約車軟件的加價功能,是運用市場機制分配有限資源的一種方式。它的出現,使得原本很難打到或打不到車的乘客有可能打上車,而且移動互聯網還使得不同司機/車輛之間的競爭(即“競價”)成為可能,使得有需要的乘客能夠以更低(比沒有競價時)的價格與司機成交。限制競價的結果只會是“有價無市”,因為理性的司機會發現出車不合算而選擇休息(“交班”),同時導致有需要的乘客無車可坐;整體而言,這是社會資源的雙重浪費。
第三,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規制應當采用自律優先的合作治理(朱迪·弗里曼,2012)的方式。網約車興起不過數年時間,尚無行業組織。但是,如前所述,立法滯后帶來的不確定性已經給從業者造成了現實的麻煩,因此,從業者們為了交易的便利,試圖自行建立相關規則。如2015年3月16日,合并后的滴滴快的發布了《互聯網專車服務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標準》,內容涉及提供網約車服務的車輛和司機的準入條件、營運中對車輛的實時追蹤全程記錄,還建立了司機和乘客的雙向評價機制以及交通事故的先行賠付保障機制。展示了約車平臺作為中介機構的管理意愿和管理能力。事實上,因為“身臨其境”,約車平臺的確能夠更直接地發現相關問題,以更低成本收集管理所需信息,提出有針對性的具體對策。與政府相比,約車平臺也能更直接便利地完成對司機/車輛的核查,對日常運營的實時監測和事后追責等。只是,同樣因為“身臨其境”,平臺有出于偏私(如排擠新的競爭對手等)設置不合理條件的可能,因此,這種“自律”規范的合理性不能免于政府的監督。這時的政府監督,更多是“后備”式的,即在發現已有“自律”規范有問題時才出手糾正或補正。可以預期的是,在發揮網絡平臺的優越性和積極性的前提下,輔以政府的“后備”監督,應可達成網約車領域平臺自律加政府監督的合作治理狀態。
第四,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規制方式能夠解決的,不應采用許可制(以普遍禁止為前提事先批準)等對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權利和自由限制更多的規制方式。政府風險規制可采用多種方式:如信息披露、標準、事先批準/許可、經濟工具(費和稅)、公有制、價格控制、特許等(安東尼·奧格斯,2008)。對具體規制方式的選擇,應合乎比例原則,即所選擇的手段能達成所欲目標(適當)、對公民權利侵害最小(必要)、且相對于達成的目標而言,所付出的代價是合理的(狹義合比例)。以擬議中的網約車輛8年報廢規定為例,此規定目標顯然在于安全性考慮。但這一手段是否能達成目標、是否對公民權利侵害最小以及代價是否合理,均是有疑問的。因為車輛的實際性能與行駛年限并不必然相關:使用頻率極高且保養不善的5年齡車輛完全可能比8年齡車輛的車況更糟糕,從而更不安全。如果采用對實質車況的“強制檢驗”手段,同樣可以達到保障車輛性能符合安全標準的目標,對公民權利的影響卻沒有“強制報廢”那么嚴重。即使經過測算,實質性能檢測實施成本高于采取以車齡為報廢標準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也有必要區分不同的報廢時限:私人網約車是私家車主利用業余時間機動提供服務,每年提供客運服務的實際時間,遠低于全天候在崗的專職的士,因此對于的士而言合理的報廢時限,對于私人網約車輛就不盡合理。而且,考慮到乘客可能寧可乘坐車齡較長但行駛里程較短而不是車齡短但行駛里程長的車輛,在堅持車輛性能檢測均應達到安全標準的前提下,也可以考慮信息披露強制這一更溫和的規制方式,即強制網約車向消費者披露車齡、行駛里程等信息,同時將是否乘坐的決定權交還給消費者。
五、結語
網約車服務的興起,以移動互聯網技術、智能手機和小汽車的普及為前提條件,居民出行需求多樣化是其驅動因素,公共交通供應相對不足則是其激化因素。雖然當前全球多國均面臨著網約車作為一種新興出行方式、新興商業形態所帶來的沖擊,但是,各國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的不同,決定了不可能存在普適的應對之道。如美國人習慣于依賴法院尋求紛爭的解決,因此在美國,甚至一些原本政策/政治色彩濃厚的問題都可能被“法律化”而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可以預期在網約車問題引發的一系列訴訟中美國法院將又一次通過訴訟澄清相關規制制度。但在中國,出現網約車這種新狀況,首先處理相關紛爭的,通常是一線行政部門而不是法院;同時作為不承認案例法的制定法國家,面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我們也更多地寄望于立法機關而不是法院來發展法律。但是,無論是通過立法、行政還是司法部門來處理,應對得當的前提是對問題本身有真正的了解和判斷,因此本文的分析和討論首先立足于對實踐經驗的觀察。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我國當前網約車的不同模式,其共同的特點和優勢在于運用了移動互聯網技術,大大降低了供需雙方找到彼此并達成合意的成本。在現行法下,多種網約車實踐實際上也擁有合規發展空間,不宜一律認定其為不合規或違法。在現行法下合法性有疑問的私人網約車,不同于專職司機以營運車輛提供的網約車服務,其獨有的優勢在于整合社會閑置運力,機動性地提供個性化的客運服務;正是這一特點,能夠補充傳統客運服務的不足,并促進社會整體福利,在規制中不宜忽略此獨特優勢。為網約車實踐提供了應用技術支撐的網絡平臺,則因為有條件(也有動力)比政府更加便利地實施對車輛和司機的監管,對于網約車相關規范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總之,網約車這種市場自發涌現并已經表現出強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政府不宜簡單以其沖擊舊秩序為由就一禁了之。就交通安全風險、個人信息安全風險和社會穩定風險等已經被認知到的具體風險而言,政府應當積極關注并研究如何防范,但在確定如何規制時應當秉持輔助性原則并應受到比例原則約束。當然,對于一項在全球范圍內也不過才出現數年的新事物,企圖在當前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相關問題是不現實的;重要的是認識到,當新問題出現時,規制思路和方法本身也應與時俱進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安東尼· 奧格斯,2008:《規制:法律形式與經濟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Anthony I. Ogus, 2008,“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China Remin University Press.]
[2]陳琳,2013:《北京打車App禁止加價,未經許可不許嵌入廣告》,《北京晨報》7月2日。[Chen Ling,2013, “Beijing Ban Renting-Car App, no advertising without permit”,Beijing Morning Post,On July 2.]
[3]財新網,2015:《Uber在全球:同樣的模式與不同的麻煩》.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06-26/100822728.html?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aixin.media.baidu.com&utm_campaign=Hezuo
[4]葛妍,2014:《市客管部門昨就專車作明確界定,私家車、掛靠車等不得提供有償租賃》,《南京日報》11月19日。[Geiyan, 2014,“Authorities defined the Zhuanche, private cars shall not join the car rental”,Nanjing daily,On November, 19.]
[5]金自寧,2014:《風險行政法研究的前提問題》,《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1期。[Jin Zining, 2014,“The premises of risk administrative law”,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1.]
[6]劉莘,2006:《輔助性原則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行政法學研究》第4期。[Liu Xin, 2006,“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and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4.]
[7]李妍,2015:《給專車1星評價招來400騷擾電話?》,《廣州日報》8月14日。[Li Yan, 2015,“One star evaluation for diver draw 400 crank calls”,Guangzhou Daily,On August,14.]
[8]桑本謙,2011:《釣魚執法與后釣魚時代的執法困境》,《中外法學》第1期。[Sang Benqian, 2011,“Entrapment and the dilemma of enforcement in the era of post-entrapment”,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1.]
[9]湯旸,2013:《上海出租車禁用約車軟件加價》,《新京報》5月27日 。[Tang Yang, 2013,“Shanghai bans the price-increasing through App”,The Beijing News,On May 27.]
[10]王軍,2015:《美國如何管理網絡約租車》. [Wang Jun,2015,“ How the U.S. manage the car-rental online”.]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7-15/100829095.html
[11]熊光清,2012:《從輔助原則看個人、社會、國家與超國家之間的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5期。[Xiong Guangqin,2012,“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dividual, community, nation and super-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5.]
[12]余凌云,2002:《論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法學家》第2期。[Yu Lingyun, 2002,“On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Jurists Review,2.]
[13]朱迪·弗里曼,2010:《合作治理與新行政法》,商務印書館。[Judy Freeman, 2010,“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New Administrative law”,The Commercial Press.]
[14]Colorado Legislation, 2014,“ SB 14-125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Regulation”. http://www.legispeak.com/bill/2014/sb14-125
[15]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CPUC), 2013,“Decision Adop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While Allowing New Entrants to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Decision 13-09-045 September 19, 2013), ”http://docs.cpuc.ca.gov/PublishedDocs/ Published/G000/M077/K192/77192335.PDF [retrieved 2015/7/8 11:19:08]
An Analysis on the Legality and Risks of “Renting Car with Driver Online”
Jin Zining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Renting car with driver online in China has sparked controversies on its legality and ris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varieties of different models of related practices, discuss separately the legality of each model under our positive law; then to analyze the risks concerning renting car with driver online, including the risks of road accidents, information leakage/misuse and social instability. Although precautions are needed, this paper argues we should decide the specific way to control those risks with def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Key Words:renting car with driver online; risk regulation;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責任編輯汪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