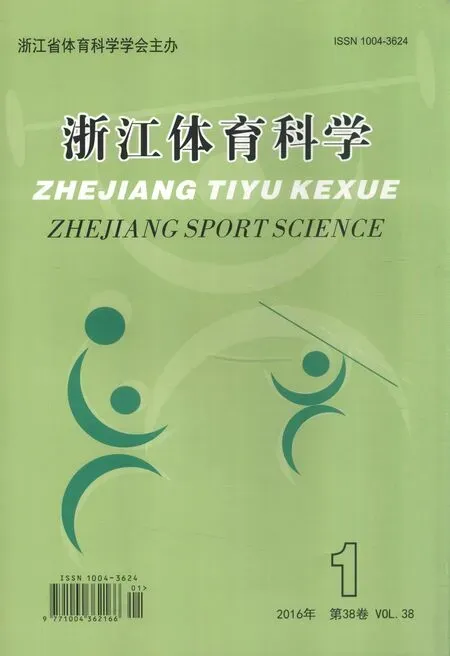身體觀視域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研究
王春燕,肖煥禹
(1.南通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江蘇 南通 226006;2.上海體育學(xué)院,上海 200438)
?

身體觀視域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研究
王春燕1,2,肖煥禹2
(1.南通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江蘇 南通 226006;2.上海體育學(xué)院,上海 200438)
在人類社會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的今天,人們在機器大生產(chǎn)下將身體解放出來,在對身體認(rèn)識的回歸與走向的爭論下,人們開始重新反思、審視、考察休閑的本質(zhì),重新開始認(rèn)識與重視休閑的生活方式和休閑理念。中國古代休閑理念有著相當(dāng)久遠的歷史,在儒家、道家、禪宗思想體系中休閑理念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受其影響古代體育項目中對休閑的理念表現(xiàn)得較為明顯。因此本文就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影響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的價值及發(fā)展的偏頗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古為今用,傳承發(fā)展,提出我國休閑體育未來發(fā)展的參考之策,同時以期可為西方文化主導(dǎo)下體育異化帶來的人的缺失性認(rèn)識帶來一定的補償價值。
1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
“身體是介于生理軀體和意識主體之間的第二種類型的‘實存’,它既是一副活生生的充滿肉欲的軀體存在,同時又是意識和知覺的主體,是身心交融一體的,是具有主體精神和生命意義的所在。”精神與軀體皆由同質(zhì)而生,身體是多維度、多層次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力量同時又與對其進行塑造、刻寫、滲透的自然、社會、文化復(fù)雜互動著,它既是自然的產(chǎn)物又是文化的產(chǎn)物,并不是處在特定的歷史時刻以至其規(guī)定性隨著歷史、地域、種族、性別等而生成變化著,對身體的關(guān)注即是對生命的終極關(guān)懷[1]。
身體是外來詞,中國古代很少將身體兩字連用,即便連用也是“身體力行”之類的動作,指向性很明確而不是直接指代人體。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身體觀其內(nèi)涵是極為豐富的,可以簡括為德的身體、氣的身體、形的身體和禮的身體,即精神的、自然的、物質(zhì)的和社會的四重屬性,整一不可分割,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儒家和道家的身體觀。儒家身體觀之要義:社會化的身體觀,認(rèn)為身體承載了社會道德倫理價值,具有階級差等性,表現(xiàn)出典型的整體觀特征,最具代表的思想家為孔子、孟子與荀子。道家身體觀之要義:自然化的身體觀,認(rèn)為身體承載了自然的意義,身體具有個體超越性,是一種重人貴生論,最具代表的思想家為老子與莊子。
2身體認(rèn)識下的休閑和休閑體育
體閑是具有多重含義的復(fù)雜概念,從不同的視角有不同的解釋。從身體觀角度理解可以將它與人的本質(zhì)聯(lián)系在一起,體閑本身是一種精神體驗,是人的社會性、生活意義、生命價值存在的享受,最真實的本意實質(zhì)上是一種身體和心靈的高度自由。身體本身的主客一體性決定了身體既是休閑行為的實踐者又是體驗者和感受者,身體對于人的休閑方式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當(dāng)今,休閑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全新的生活理念和價值取向,成為了社會發(fā)展的文明標(biāo)志,休閑精神是體育得以發(fā)展和延續(xù)的內(nèi)在動力源泉,休閑體育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有利于人類自身發(fā)展的高級生活方式,是人類自我的一種回歸,是一種人生境界,一種生活態(tài)度也是人類的自我解放和完善。在休閑體育中人類可以找回自我,可以面對自我、體驗自我、享受自我并最終達到塑造自我、完善自我,這也是休閑體育在今天興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在休閑體育中人類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3傳統(tǒng)身體觀指導(dǎo)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的體現(xiàn)及價值
3.1 以宮廷貴族休閑娛樂為主體的禮制體育:修身重德,“禮”于社會
在我國古代宮廷貴族主要以禮射、田獵、樂舞、蹴鞠、馬球、下棋等體育項目為娛樂的主要內(nèi)容,所有這些休閑體育活動無不帶有一定的禮教色彩,要求君子仁人能夠嚴(yán)格遵守儒家社會道德倫理規(guī)范即“克己復(fù)禮”,時時刻刻控制身體與生俱來的感覺與欲望并注意日常生話中的一言一行,如射禮中“射”與“禮”的結(jié)合,要求射者“內(nèi)志正,外體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以言中。”(禮射可以說是我國較早的一種較為典型的體育休閑模式),唐代木射將“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作為取勝標(biāo)記;投壺之“修身、觀人”,司馬光的《投壺新格》中提出:“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還有《蹴鞠圖譜》中言,“踢球應(yīng)以仁為主”。此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身體,各有各的規(guī)矩,這種身體的階級差等性的社會化身體觀,規(guī)范與限制了具體的身體實踐與操作過程,具有明顯的階層性及一定的自律作用,如西周有針對不同階層人群的大射、燕射、賓射、鄉(xiāng)射;《捶丸經(jīng)》云:“捶丸雖若平等,而尊卑之序不可紊亂[2]。”這些體育活動強調(diào)社會道德倫理價值在體育文化中的控制作用,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合理性,強調(diào)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和諧與平衡狀態(tài),充分體現(xiàn)儒家從共生中體悟獨在的休閑理念,說明個體只有和社會和諧相處才可以發(fā)展,也就是只有在人與社會的共在中才能達到個體獨在時的休閑感受。這些體育休閑活動中主要確立的是“仁”的思想,只有達到“仁”境界才能體會到休閑的快樂,即生活與生命、個人與集體、個體與個體的和諧發(fā)展,實質(zhì)上是一種精神上休閑的至高境界。
但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古代的體育項目往往都以皇室貴族的喜好為指向而在民間興衰,如馬球、捶丸在唐代興盛一時,在后世宮廷中出現(xiàn)很少又因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至清代中葉以后趨于衰落;蹴鞠在明代朝廷宴會取消其表演,主要流行于下層社會,娛樂層次和社會價值低下,至清代邁向衰亡。而皇室宮廷、貴族士大夫推崇的又都是封建禮教為思想指導(dǎo)的體育活動,這便形成了我國特有的以倫理道德、封建禮制為主要指導(dǎo)思想的體育活動形式,這種影響一直至今,如被視為“國術(shù)”的武術(shù)中依然有“未曾學(xué)藝先學(xué)禮,未曾習(xí)武先習(xí)德”的基本規(guī)定,“對御不爭第一籌”“勝亦可喜,敗亦無憂”,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見儒家的“尚仁”,墨家的“兼愛”等思想在規(guī)范人們的體育行為和平和體育氣氛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3]。“仁、義、禮、智、信”成為理想人格的標(biāo)準(zhǔn),“仁德”、“仁禮”成為禮制體育追求的最高層次,在表面直觀的身體運動后面蘊藏著本民族豐厚的道德思想內(nèi)涵,彰顯了古代體育文化的倫理價值與社會價值,充分體現(xiàn)儒家整體性的社會化身體觀,即追問的是身體存在于家國社會中的位置與意義,主張從人的生物超越性中提升人之社會超越性和人之精神超越性。由此可見禮制休閑體育對我國體育格局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當(dāng)代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中各種行為失范現(xiàn)象,對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指導(dǎo)下禮制體育中社會道德倫理價值的追問未必不能夠成為走出這此價值混亂困境的良途。因為對社會而言,政府所提倡、民眾所遵循的社會道德倫理是社會良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當(dāng)這樣的社會道德倫理理想由對人進行被動控制轉(zhuǎn)化為人的主動遵守,當(dāng)規(guī)范內(nèi)化為人對自身自覺的約束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秩序的規(guī)范與調(diào)整。
3.2 以節(jié)令習(xí)俗為載體的民俗體育:娛樂身心,豐富生活
我國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繁多,運動形式千姿百態(tài)。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開始民間體育娛樂活動就有秋千、飛鳶、龍舟競渡、牽鉤、釣魚,此外還有具有后世雜技特點的跳丸、弄劍及斗雞、走犬等比賽娛樂活動。至秦漢時期祭禮祭儀讓位于事實上的娛樂,形成了一些適應(yīng)農(nóng)時季節(jié)、以節(jié)日節(jié)令祭儀為組織形式的民俗體育,此后元宵觀燈、陽春拔河、端陽競渡、重九登高、中秋賞月等民俗活動在各朝代盛行,如唐代舉行盛大的拔河比賽,清明節(jié)有放風(fēng)箏、蹴鞠、步打球、蕩秋千、劃船和戲水,魏晉后增加了騎馬、射箭等演武性活動,南宋時還有舞草龍,明清時期又增加了舞火龍、點塔燈、走月亮、冰嬉等民俗活動。豐富多彩的民間體育活動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而且都具有休閑性和濃郁的喜慶色彩,寄托了人們美好的愿望,其形成不僅是民族文化的傳承結(jié)果,更是民族倫理道德的反映,倘若沒有民族共同維護的道德情感、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規(guī)范,任何一項民族傳統(tǒng)體育都很難在民眾心中長期享有被遵從和愛戴的位置,人們也很難表現(xiàn)出心悅誠服的態(tài)度,這充分體現(xiàn)了身體承載的社會倫理道德價值及“仁”的休閑思想。
再有這些活動有強烈的自娛性與娛他性,首先人們在美麗的自然中不知覺間就受到美的熏陶,寓于審美享受之中而得到心靈的塑造、情感的凈化和精神的升華;其次人們借助健、力、美融為一體的體育活動盡情地展現(xiàn)彼此的氣質(zhì)、體魄、技能、膽略與智慧,交流著微妙的情感,從而滿足了人類心理上的各種欲望,使運動者和觀賞者都能通過此類活動調(diào)節(jié)情感、愉悅身心、陶冶情操,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因此,民俗體育的本質(zhì)不在競技而在于給人以心靈的滿足和休閑,可以說它促進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群、群與群,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充分體現(xiàn)了儒家社會化身體觀下的從共生中體悟獨在的休閑理念和道家身體觀所追求的個體生命的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及休閑追求的自我心理體驗與自然的交融,彰顯了生命價值的追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俗體育蘊藏在人們的生活中,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豐富的體驗享受,其特殊的娛樂、健身、趣味、民俗等特性以及民族的情感性使其具有較強的民眾參與度,可以在全民健身活動中更好地發(fā)揮其作用和價值。其次,作為凝集群體內(nèi)成員共同情感和民族共同心理的一種特殊文化,其對強化社會的集體意識和增強群體的凝聚力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再次,當(dāng)今世界體育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影響已遠遠超出體育本身,我國傳統(tǒng)身體觀下的民族體育具有較高的體育本質(zhì)功能,對其的傳揚必然會引發(fā)人們對競賽主導(dǎo)下的競技體育的又一次反思,特別是人們麻木追捧的政治體育、功利體育等的反思,在今天休閑體育大行其道趨勢下彰顯其獨特魅力,越發(fā)的美麗動人、生機勃勃。
3.3 以導(dǎo)引養(yǎng)生為主體的養(yǎng)生體育:強身養(yǎng)性,生命追求
我國古代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認(rèn)識到運動是最好的養(yǎng)生方法,《荀子·天論篇》記載:“養(yǎng)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yǎng)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在這種“生命在于運動”的思想的推動下,明確主張通過身體運動來健身治病導(dǎo)引術(shù)應(yīng)運而生,《莊子·刻意》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jīng)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dǎo)引之士,養(yǎng)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段錦”、“易筋經(jīng)”、“五禽戲”、“二十四節(jié)氣導(dǎo)引法”、太極拳等。這一類的體育活動,這些功法在今天看來更像是一種健身操、健身功,而“導(dǎo)引的彌足珍貴之處在于它是中國傳統(tǒng)養(yǎng)生文化中最能融入現(xiàn)在文明和現(xiàn)代體育的一種思想健身體系,能夠滿足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類對健身手段的要求和需要[1]。”以保健養(yǎng)生為主的導(dǎo)引體育經(jīng)過長期的氣功養(yǎng)生實踐形成了精、氣、神三位一體的“人身整體觀”,正是在道家自然化的身體觀指導(dǎo)下即強調(diào)身體的個體超越性及健身價值而形成的用以健身強身的體育活動形式。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天人合一”這一運動思維模式強調(diào)個體自身的感受,尋求自身內(nèi)在力量的培養(yǎng)方式,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強調(diào)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倡導(dǎo)在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行強身健體的同時,要順應(yīng)自然,依時而行,這促進了體育活動的自在自為,對自然大道的追求促使中國古代走上一條趨于靜的養(yǎng)生之路,彰顯了養(yǎng)生活動的獨特魅力[1]。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由此而生的養(yǎng)生觀,從生理層面界定了身體的重要價值,提倡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生存原則建構(gòu)了獨具東方特色的經(jīng)絡(luò)論與氣化論,采用形神兼顧的養(yǎng)生策略構(gòu)成了我國古代身體觀中的實體化身體觀,通過調(diào)身、調(diào)息、調(diào)神的自我鍛煉使經(jīng)絡(luò)疏通,心血平和,從而達到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目的。其最貼近“形軀之身”的態(tài)度及對人有限生命的關(guān)懷充分體現(xiàn)道家在實在中構(gòu)建虛在的休閑理念,即強調(diào)個體的自我完善與自我實現(xiàn),追求一種自然休閑,一種個體的自適狀態(tài),注重休閑的個體性和生命體驗感。這種從個體出發(fā)的真純無為的休閑體育態(tài)度相比儒家社會層面的休閑理念顯得更為積極,更具生命關(guān)懷的終極意義,似乎更符合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休閑方式。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今天看來恰恰正是這種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與自然為友的休閑理念成為指引人類對抗現(xiàn)代高度化的機器大生產(chǎn)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指導(dǎo)下的養(yǎng)生體育可以成為今人身處嘈雜繁華的現(xiàn)代世界時進行人生選擇、生命體悟的另類路徑。它提倡避免在運動過程中的功利性,相對于當(dāng)今時代體育主流文化注以運動效率和運動技能至上的功利性追求而言未必不是一種超越。
3.4 以練兵習(xí)武、表演娛樂為主體的軍事武藝體育:強身健體,彰顯力量
軍事武藝中的田獵、騎射、摔跤一直是我國古代較為盛行休閑娛樂體育活動。夏商周時期的武舞即由軍隊操演演變而來,用于表彰軍功,以慶勝利歡樂;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彈射、斗劍、田獵、拳技、角力等項目是軍訓(xùn)與娛樂的結(jié)合,流行于統(tǒng)治階層;至秦漢三國時期開始,部分軍事化項目逐漸從軍事中分化出來朝競技、表演方向發(fā)展,如秦朝首開摔跤表演先河,唐宋將摔跤表演推到極致,促進其娛樂化;還有從娛樂性出發(fā),用于表演具有藝術(shù)美的“武術(shù)”獨立存在,有專業(yè)藝人及固定的表演套路和場所,民間休閑娛樂價值凸顯;一直到明清時期賭射、行圍射獵、詐馬等依然流行于皇宮貴族及士大夫階層,民間武術(shù)及摔跤依然盛行,特別是武術(shù)走上“武功與導(dǎo)引功法相結(jié)合的道路[4]”。由此可見,軍事武藝項目從軍隊走向舞臺,創(chuàng)新改造向民間化方向發(fā)展,其休閑娛樂性從最原始的表演歡悅發(fā)展到強身健體、修身養(yǎng)性、審美娛樂等多重價值上,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之精神的、自然的、物質(zhì)的和社會的四重屬性,彰顯了古代部分軍事武藝項目的休閑性與自娛性,其講究自我鍛煉,不提倡相互爭斗與對抗,追求對人生的體驗與磨礪,對人格的完善起到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部分項目非常適合現(xiàn)代人對休閑的需求。
4傳統(tǒng)身體觀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發(fā)展的偏頗
4.1 重自得其樂輕個性張揚的主題模式
在傳統(tǒng)身體觀認(rèn)識下,我國古代許多休閑體育活動盡管在相當(dāng)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一直帶有濃郁的農(nóng)耕社會的氣息和原始的狂歡氣氛,然而卻未能脫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性公共休閑體育活動形式,基本上還是局限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自得其樂的活動范疇,缺少個性的揮舞和冒險的激情,缺乏注重發(fā)展個體的興趣和張揚的個性。但這些現(xiàn)象也確實反應(yīng)了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某種必然性,揭示出農(nóng)耕經(jīng)濟對社會休閑體育活動的發(fā)展所產(chǎn)生的羈絆作用,進而使我國古代休閑體育活動的主題難以隨歷史演進而得到與時俱進的升華。
4.2 重靜輕動的活動形式
在傳統(tǒng)身體觀認(rèn)識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活動始終與人們德行升華的意識演進軌跡相互依存,表現(xiàn)為優(yōu)雅寧靜、沖淡平和的審美境界,持中守恒、過猶不及的感情節(jié)制以及含蓄內(nèi)斂的運動休閑選擇,以保健性、表演性為基本模式,使得中國體育表現(xiàn)出柔弱、舒緩、平和有余的性格特征,剛強、力量、競爭不足,國人的身體體質(zhì)方面受到侮辱。且崇文尚柔的運動形態(tài),“君子勤禮,小人經(jīng)力”的消極娛樂活動的基本價值觀在無形中影響人們選擇運動休閑形式的意向,對后世人們參與休閑體育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且此偏見影響頗深,使得國人在運動休閑時缺乏尋求濃烈的感官享受,缺乏通過具有極大發(fā)展張力的活動形式,充實和完善以自我為主體的人格意識。
4.3 重自然輕科學(xué)的運動健康態(tài)度
傳統(tǒng)身體觀主張順應(yīng)自然和無為而為,講究以“虛靜”為法,更進一步將人的身體運動弱化、虛化、靜化,這種思想從某種程度上遏制了對人類身體存在狀態(tài)及身體運動規(guī)律的主動探索,導(dǎo)致對人體缺乏積極主動的認(rèn)識態(tài)度。在缺乏積極探索自然的精神和重視知覺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對運動健康的奧秘未徹底探究,即使是養(yǎng)生家、醫(yī)學(xué)家也始終停留在“陰陽平衡”前,未能更進一步。且道家自然化身體觀特重自然,發(fā)展到絕對則易形成一種對身體的極端化意識與認(rèn)知。首先,在遵循自然、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對身體欲望的有意壓制和對身體形態(tài)乃至身體存在長久與否的有意忘卻,直接導(dǎo)致了中國古代休閑體育文化中缺少贊美身體、重視身體的因素,沒有對身體形象的深入追求,就未能產(chǎn)生出廣泛、普遍的形體審美觀念;其次,在道教文化中屢屢造成人的實際死亡和虛假成仙的謬知沖突,這未必不是這種極端化身體意識的結(jié)果,對身體客觀科學(xué)認(rèn)知的不足導(dǎo)致對身體的偏頗觀念和迷信思想,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古代休閑體育活動的推廣及深入發(fā)展。
4.4 重道德輕身體、重社會輕個體的價值認(rèn)識
受其影響,一方面使得古代一些休閑體育項目在禮儀色彩熏染后變得中規(guī)中矩、索然無味、了無生趣,這一傾向使許多休閑體育活動失去了休閑體育運動本應(yīng)具有的魅力,因而漸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如在隋唐時期外傳日本的蹴鞠。另一方面使得古代休閑體育表現(xiàn)出的嚴(yán)重階層差等性。首先,僅僅在少數(shù)階層中流行的項目未能流入民間,如投壺、馬球、捶丸等因缺乏群眾基礎(chǔ)而走向沒落;而民間盛行的體育項目往往又因其低俗文化特色被排斥于上層階級主流關(guān)注目光之外而不登大雅之堂,只能流于民間,如拋球、女子蹴鞠、步打球等因缺乏統(tǒng)治階級支持而衰落。其次,雖古代歷朝統(tǒng)治者在發(fā)展休閑體育活動中的作用不容小視,如歷朝政府規(guī)定了每年的傳統(tǒng)節(jié)慶活動時間并在節(jié)日期間組織一些大型的社會活動,同時還撥款建設(shè)一些休閑體育活動設(shè)施,如在每年的正月元宵節(jié)期間撥款建設(shè)可供演出的戲臺或可供觀賞的燈臺,但更多的是將體育視為實現(xiàn)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繁榮、政治進步的手段,借以顯示社會盛世太平、民眾安居樂業(yè)的繁榮景象,體現(xiàn)與民同樂的親民政策。且這些舉措往往是臨時性的,所建造的設(shè)施也通常都是應(yīng)景式的,真正作為提供人們進行社會公共娛樂活動的場所和設(shè)施并不多見,更多的是僅供皇帝和貴族享受和娛樂的體育場所,許多休閑體育項目的發(fā)展往往受到場地等因素的制約而生存舉步維艱。這些現(xiàn)象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古代休閑體育文化自身的影響范圍,從而影響了其正常走向和健康廣泛發(fā)展。
4.5 重個體輕團體、重傳承輕創(chuàng)新的項目發(fā)展
傳統(tǒng)身體觀講求法無定法、因人而異,形成了自在自為的體育文化特征,因此幾乎沒能在中國古代產(chǎn)生大規(guī)模、全民性的身體鍛煉活動,且不重視團體行為,很少發(fā)展出集體項目,即使存在也是作為實現(xiàn)政治和軍事目的手段,如唐代的拔河比賽,清朝的龍舟競渡。另外個體的相對自由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禮”的束縛,使得體育在實踐中壓抑了人的個性、主觀性與能動性,從而導(dǎo)致古代部分休閑體育項目因為缺乏內(nèi)容創(chuàng)新而失去趣味性、吸引性與競爭性,最終隨著時代的交替而沒落,如蹴鞠、捶丸等;另一方面強大統(tǒng)一的行政控制與封建君主集權(quán)制所形成的官僚制度、血脈傳承、種姓制度等對個體項目的開展影響深遠,如武術(shù)中宗派等級思想就是這種體制的變相反映,武術(shù)被視為絕技,多采用家族、族傳或宗傳方式秘不傳外人,因此武術(shù)形態(tài)上的開放性與創(chuàng)新性也就自然很難實現(xiàn),這些都對古代休閑體育的發(fā)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5結(jié)論與建議
綜上,身體觀認(rèn)識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蘊含著中華民族千年不朽的智慧,飽含著休閑體育的思想精華,其本質(zhì)更好地體現(xiàn)了不同時代人們對體育社會價值的深刻理解,更多地體現(xiàn)了休閑體育的本質(zhì),其發(fā)展受多方面影響。觀望現(xiàn)實,借古論今,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我們要在文化的夾縫中生存,就得努力地爭取“休閑體育”的正當(dāng)性,把握“休閑體育”的合理性;要想在現(xiàn)代體育發(fā)展的浪潮中乘風(fēng)破浪,就要把現(xiàn)代社會的休閑體育意識和傳統(tǒng)科學(xué)的休閑體育觀念融為一體,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方面著手,通過多種途徑將之推向社會,推向大眾,沖破禁錮我們認(rèn)同的傳統(tǒng)休閑體育生活原則的意識堡壘,使中國在邁向大眾休閑體育時代的浪潮中獨領(lǐng)風(fēng)騷。具體方法:①樹立以人為本的指導(dǎo)思想,追求休閑體育的人文性、活潑性、有效性。②守護禮制體育,將休閑體育研究更加深入,領(lǐng)域不斷拓寬,將其倫理性繼續(xù)保持,突出規(guī)范性與符號化,彰顯其科學(xué)性與獨特性。③拓展民俗體育,將休閑體育與全民健身相結(jié)合,注重內(nèi)容和方式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體現(xiàn)其層次性與多樣性。④弘揚養(yǎng)生體育,將休閑體育與構(gòu)建和諧社會相結(jié)合,趨于與自然的融合,實現(xiàn)戶外化與生態(tài)化,重視健康,體現(xiàn)自然性與時代性。⑤創(chuàng)新軍事武藝體育,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相結(jié)合,注重休閑體育的個人參與性與自發(fā)性,追求刺激與極限的感受,體現(xiàn)流行性與時尚性。
參考文獻
[1]趙岷,等.體育—身體的表演[M].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1:8,160-167.
[2]沈雪峰,等.體育文化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12:11,122-125.
[3]崔樂泉.中國古代體育文化源流[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11.
[4]畢世明.中國古代體育史[M].北京體育學(xué)院出版社,1989.
[5]陽家鵬,向春玉.休閑時代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瓶頸及應(yīng)對策略[J].南京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11,25(5).
[6]俞金英.論道家養(yǎng)生文化的內(nèi)涵及在我國休閑體育中的價值[J].吉林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11,27(5).
[7]赫雪停.儒家休閑思想對我國休閑體育文化的啟示[D].濟南:山東大學(xué),2013:12,13,25,26.
[8]劉媛媛.先秦身體觀語境下的中國古代體育文化研究及其現(xiàn)實意義[J].體育科學(xué),2012,32(1).
[9]張良.我國休閑體育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策略[D].重慶:西南大學(xué),2010.
[10]虞重干,張基振.休閑語境中的中國民間體育[J].武漢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5:39(11).
[11]陳玉忠.我國休閑體育發(fā)展的未來走向[J].上海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7:31(1).
[12]包呼和.休閑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休閑體育面臨的挑戰(zhàn)與發(fā)展[J].廣州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12:32(2).
[13]馬衛(wèi)平.體育與人—一種體育哲學(xué)[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11,81-87,98-100.
·體育史學(xué)·
摘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身體觀其內(nèi)涵是極為豐富的,可以簡括為德的身體、氣的身體、形的身體和禮的身體,即精神的、自然的、物質(zhì)的和社會的四重屬性,整一不可分割,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儒家和道家的身體觀。文章就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影響下古代體育項目中的休閑因素進行全面的梳理、研究和挖掘,分析身體認(rèn)識下我國古代休閑體育發(fā)展的必然和價值以及阻礙其發(fā)展的偏頗問題,以期為我國休閑體育的發(fā)展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模式,展望未來,提出發(fā)展之策。
關(guān)鍵詞:身體觀;中國傳統(tǒng)身體觀;休閑;休閑體育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of Ancient Chinese under the Horizon of Body View WANG Chun-yan1,2,XIAO Huang-yu2
(1.Nantong Normal College, Nantong 226006, 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The connotation of the body view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tremely rich. It can be seen as the body of moral, gas, shape and etiquette, that is spirit, natural, physic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which is as a integral whole, above them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e the body of Confucian and Taoist view. In this paper, through comprehensive carding, researching and mining the factors of ancient sports leisure whi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cal view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mod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s.
Key words:body view;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cal view; leisure; leisure sports
中圖分類號:G812.9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624(2016)01-0113-05
作者簡介:王春燕(1983-),女,江蘇南通人,講師,碩士,上海體育學(xué)院在讀博士,主要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xué).
收稿日期:201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