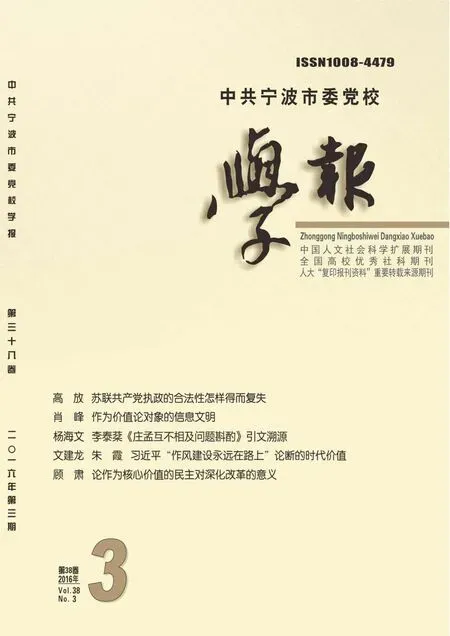儒家哲學中的認知與行動
朱承(上海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444)
?
儒家哲學中的認知與行動
朱承
(上海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444)
[摘要]關于認知與行動,儒家哲學里有著較多的討論,這就是所謂“知行之辯”。但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宋明儒家,都傾向于將認知與行動的問題歸于人的倫理實踐。從實踐出發,儒家的知行哲學最終都歸結到人的道德修養問題上,而較少思考知識本身的理論問題。近代以來,知行哲學的問題又逐漸從倫理實踐轉向政治實踐。從歷史上來看,儒家哲學中關于認知與行動的思考,即使表現形式是理論的語言,但其本質上也是具有倫理實踐色彩的“思想實驗”,而非純粹理性的問題。
[關鍵詞]認知;行動;實踐
認知和行動是人們在生活世界中展現人性能力的主要方式,在儒家哲學里,關于認知與行動的關系,有著非常豐富的思想。歷史地來看,雖然儒家思想從理論創造上高峰迭起,但從根本上儒家生活哲學仍然是一種關于如何行動的哲學,而非純粹追求知識上的創造和發現,這一點是儒家哲學的重要特點。
孔子曾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符合道德和禮儀的行動是儒家思想極力推崇的,儒家從理論上不斷為儒家道德行動的合理性做出論證。“至于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顧憲成對晚明士大夫階層的這段議論比較清晰地表達了儒家學說的實踐性特質。歷史地看,儒家向來重視實用之學,即使是關于性命的抽象辯論,其指向也主要集中在現實的倫理實踐上。儒家學說應該是指向現實生活、實際行動,而不僅僅是停留于言辭層面的玄虛討論,即使是關于性命、德義的倫理論辯,如果遠離現實行動,這樣的討論也是毫無意義的。
在以倫理為導向的儒家哲學傳統中,無論是高論天人、玄思性命,還是暢談義利、激辨知行,最終都期望貫徹到現實的倫理實踐活動中去。可以說,儒家所關注的各種問題,無論其表現為何種心性意義或者語詞意義上的討論,其實質都可以轉化為生活中的道德和倫理實踐的問題。按照現代哲學的話語講,關于理論理性的論辯內容,儒家都傾向于將其轉化為實踐理性領域的問題。關于倫理道德的討論,如果不見諸實踐意義上的行動,而僅僅流于抽象概念的思辨,始終不是儒家倫理哲學的正途。
對行動問題的警惕和憂慮,表現了儒家倫理對于道德認知、道德信念與道德行動之間關系的高度重視。關于道德認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動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傳統儒家思想中稱之為“知行”問題,眾所周知,“知”代表著道德認知、道德意識、道德信念、道德情感,而“行”則意味著道德修養、道德踐履、道德行動,我們一般傾向于把儒家思想家關于道德認知和道德踐履的討論概括為“知行之辯”。圍繞知行問題展開的論辯,也可稱之為“知行哲學”,但儒家知行哲學主要集中在倫理道德論域,也主要指向倫理實踐,而缺乏對于“知”與“行”本身的理論思辨。
一、知行哲學的倫理色彩
從文獻上來看,一般認為,儒家經典《尚書》最早意識到知、行之間的張力問題。《尚書》上提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尚書·說命中》),從邏輯上把知、行問題進行了分疏,指出人的活動可以分作認知活動與實行活動。這是有文獻記載最早的、較為明確的關于知和行的論述,孫中山曾認為《尚書》里這一“知易行難”學說“數千年來,深中于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思想的歷史也確實說明了這一點。另外,在《左傳》里也有類似的話語:“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左傳·昭公十年》)可見,早在中國思想的萌芽時期,中國的思想家們已經覺察到了知和行之間存在的內在緊張了。
《尚書》和《左傳》里提出的知行之辯,結合當時語境來看,還沒有徹底地表現出特別的倫理色彩,主要是在談現實生活中認知與踐履的關系問題。但是,到了孔子那里,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就更多的體現為道德倫理問題了。馮契先生在討論孔子思想時曾指出:“孔子的仁智統一學說,以為認識論即是倫理學,所以他的認識論命題都具有倫理學意義。”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的認知問題往往和倫理學的行動問題難以嚴格區分,兩類問題常常交織在一起。從孔子開始,中國哲人討論認知和行動關系問題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解決道德倫理中的困難,而認識論意義上理論思辨則相對弱化,缺乏從抽象層面的邏輯推演,而更多是從經驗層面予以概括和總結。
孔子沒有將知、行并言,他更多是用學與行、言與行來代替知與行的問題。孔子所謂的學,主要是學習承載了儒家倫理規范的文化典籍、禮儀制度,學習仁、義、禮、智、信的行為,而且學習的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行動。孔子曾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從孔子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學習求知的過程,是自我約束、自我修養的表現,其實就是道德行動的過程,這就使得“學”和“知”具備了濃厚的倫理意味,并不是像我們今天所言的學習科學知識的“學習”。孔子所謂的“好學”是表示道德規范的習得與實踐,并對此道德修養活動保持濃厚的興趣與堅韌的毅力。除此之外,孔子還要求在道德修養上要言行一致,他認為“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可見,孔子將言行一致看作是君子的良好道德風范,知行統一是劃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知行問題與倫理學意義上的人生修養不可分割。
從孔子的言論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倫理學意義上的知(學、言)與行,孔子主要是從道德認知和道德踐履意義上來談論知行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孔子的知行觀偏重于倫理學,而較少具有認識論的意義。自孔子之后,儒家學者所論之知行多傾向于倫理學問題,也就是我們說的道德意識、道德認知與道德踐履的問題,這是一貫的。
既然知行問題在傳統思想中更多的是一個倫理行動問題,而非純粹理性領域的問題,那么從實踐的視域來看,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來把握知行哲學呢?如所周知,傳統儒家關于知行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于知行先后、知行難易之間的辯難。也即是說,所謂知行之辯,主要是指
《中庸》里曾安排了一個從道德認知到道德行動的序列,這就是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按照朱熹的理解,學、問、思、辨、行并列的五者,實際上可以合成知與行兩個方面。朱熹認為:“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中庸》里的安排之為學工夫的序列,其實就是一個道德修養意義上的知、行次序,按照《中庸》的意圖,那就是知在行前,只有通過學、問、思、辨的認知過程,才可以真切地體認到道德知識進而樹立道德信念,從而才可以認真切實的履行,把理論德性置于實踐德性之前,但實踐本身才是目的,雖然知在行前,但是知以行為目的和歸宿。
關于知行次序的問題,在儒家倫理思想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以宋明時期的理學討論最為豐富。宋儒程頤主張知先行后,他明確提出:“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在程頤看來,道德認知之于道德行動,猶如指路明燈與行路這一活動之間的關系,明燈是為了路人更好的行走,“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程頤對知先行后的強調,也表現了對知作為行之前提和條件的重視。就道德領域而言,只有通透地體認了倫理綱常,才有可能更好地力行,道德行動是隨著道德認知自然而然形成的,正所謂“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于是,豈有不得道理?”在程頤看來,如能以“顛沛造次”的氣力和精神致力于道德認知和道德信念的培養,準備好各種前提條件,在這樣的條件下來實行踐履,自然可以證成至善的道德境界。可見,程頤不僅僅把“知”放到“行”之先,同時還相信就道德修養而言,“知”是“行”的前提。在道德修養領域圍繞知行先后次序的辯論和圍繞知行難易的辯論,也可以說是一種圍繞知行問題的“思想實驗”。
二、道德認知與道德行動
朱熹也主張將認知與行動區分開來,“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認知和行動是實現學問之事的兩條道路,一是獲得知識,一是在現實中予以踐履。二者是有著先后次序的,這個次序就是知先行后,“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但即使是知先行后,也是“行為重”,換句話來說,知的目的是行。朱熹還認為,“知與行,工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后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可見,朱熹認可知行工夫是并列的,但從邏輯上來看,“須知得方行得”,也就是說,道德倫理的教條只有理解了才能去執行,不被人深刻理解的教條將可能引導人誤入歧途。由此足見,在道德修養領域,朱熹是一位理性主義者,他希望人們獲得理性認知后才投入行動。當然,朱熹承認知先行后也并不是絕對的,就具體一事而言,可以說“知先行后”,但就長期的道德踐行而言,也必須先從小處、實處的行動開始做起,他說,“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后,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從朱熹的猶疑,我們可以看出,知行問題的先后次序只能做邏輯區分,在現實中其實難以區分。
程朱學派“知先行后”的思想與其格物致知的思想體系是一致的。“知先行后”強調“道問學”的工夫,而所謂“道問學”,就是主張在道德修養過程中重視“格物窮理”,“格物窮理”實質上就是在事物上求索道德之理,也就是我們說的道德認知。所以,程朱學派強調“道問學”同時,就意味著在知行先后的問題上主張“知先行后”,從邏輯上將理論認知作為行動的前提。
雖然在修養工夫上,程朱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的旨趣不盡相同,但在知行次序的問題上,陸九淵和程朱持大體相同的觀點,也是認為知先行后,知具有邏輯優先的意義。陸九淵論學十分重視本末次第,在知行問題上,他主張先講明后踐履,先知而后行。他認為:“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圣之事,此踐履也。……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矣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而已,是冥行者也。”《象山語錄》上還記載:“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曰: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可見,陸九淵同程朱一樣強調知先行后,強調只有理解了道德義理而后方可踐履。另外,陸九淵曾說過:“若某不識一個字,也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即使不識字,沒有知識意義上的“文化”,也仍可在道德修養意義上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這都是靠“行動”體現出來的。就陸九淵的思想體系而言,他強調發明本心,發明本心與“求知”的關涉無多。那么,知先行后的觀念與陸九淵向來重“尊德性”而輕“道問學”的基本立場是否有所沖突呢?我們認為,陸九淵所謂的“不識一個字”,主要是指不要皓首窮經鉆研冊子典籍,因為在他看來讀書并不是道德體認的必要手段,按照陸九淵的說法,堯舜之前沒有典冊,但堯舜仍然能夠成為圣賢。所以,我們有必要把道德體認與經典學習區分開來,二者之間有著不小的距離。道德體認是人在理智中把握道德原理和倫理原則,而經典學習雖然是道德體認的路徑之一,但并非唯一路徑,人還可以通過其理性本能和現實踐履體會和理解道德原則。當然,經典學習由于能較快借鑒他人反思的理論成果,因而無疑能更好地促進人們理解能力的提升。
如上所述,陸九淵在知行問題上并沒有擺脫程朱的傳統觀點,主張“知先行后”,強調知對于行的條件性意義,當然,這個“先后”并不是重要性的先后,而是在工夫次第上的先后。關于朱陸知行觀的大體相同這一事實與朱陸之爭之間的關聯問題,王陽明在與友人通信過程中涉及到,王陽明就此做了明確的回應。有人問曰:“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于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面對這樣的質疑,王陽明這樣回答,“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此處,王陽明直言象山“見得未精”,也就是說,王陽明承認他的心學前輩陸九淵在知行問題上并沒有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而他本人則在知行哲學上開創了新的境界。
王陽明的許多論點都是針對朱熹而發,在知行哲學上更是有這樣的跡象。朱熹主張“知先行后”,有割裂知行的傾向,針對知行分裂,王陽明在知行問題上主張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朱熹的問題在于將人心與天理分而論之,承認理在心外,故而主張向外求知,然后付諸行動。而在他看來,心就是理,心外無理,所以根本無須向外求理,“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既然心與理合而為一,那么本心之知本身就意味著行動,行動本身就是真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善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在王陽明看來,道德意識與道德行動本是一體,二者互為前提,知行與修養一體,無可分離,“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這就是說,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并進是不得已的事情,因為知行本體本是一個,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本來只要說一個就夠了,古人知行并說是為了糾正“冥行妄作”合“懸空思索”,是“補偏救蔽”的做法。同時,王陽明認為,人們之所以將知、行分作兩件事情去作,主要是因為程朱理學知先行后學說所造成的后果,人們誤把前提當成目的,從而造成了知行分離、虛假橫行。為了恢復知行本為一體的原始面貌,去除知先行后所造成的知行分離的惡果,王陽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王陽明認為在道德世界中本無知行之分,這似乎是說,前人區分知行、尋找知行之間的張力的理論努力都是白費了一樣。王陽明說: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這段話是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基本主張,除此之外,王陽明還曾用十分凝練的話來表達“知行合一”思想,他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粗看起來,王陽明的這句話似乎在挑戰我們的日常經驗,把主觀意念也說成是行動了。王陽明為了破除程朱理學把人們的道德認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為脫節的弊病,確實有點言過其實。但這也算是矯枉過正,是批評那些所謂滿腹道德仁義的“道學先生”們實際上并沒有領會儒家的道德精神實質,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在他看來,如果真的領會了儒家道德精神的實質,具備了完整真實的道德意識,那么道德行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一定意義上,王陽明確實打破了我們常識中知、行的界限與差別。黃宗羲在對王陽明的知行學說評述之后,贊嘆王陽明“命世人豪”:“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驚,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列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中印證過來,其為廓然圣路無疑。”就王陽明在知行學說上的洞見而言,黃宗羲的上述評價無疑是妥當的。
在統攝知行的道路上,王陽明的貢獻巨大,但不管怎么說,他將道德意識等同于道德行為,用意志、精神來代替行動,既有所見,也有所蔽。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消解了知行先后的次序問題,但在邏輯上也帶來了知與行混淆不清的理論困難。王夫之對此就曾評價說:“近世王氏之學,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入于異端也。”王夫之此說,雖對陽明良知學和知行合一學說有所偏見,但也確實指出王陽明將人們經驗中的知行兩分混淆起來了。王夫之既不同意程朱將知行分作先后來說,也不同意王陽明將知行合而為一,提出“知行相資以為用”的知行觀,他認為:“誠明相資以為體,知行相資以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為用,資于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王夫之從認知與行動的功效角度來講知行,知、行和而不同,各有其用,相互區別,同時又相互激蕩而發生功用。這表明,王夫之贊成將人的認知與行動從邏輯上做一區分,但在事實中將人在生活世界中取得的實踐效用看做是認知與行動共同發生作用的。王夫之“知行相資以為用”的觀念,與我們的日常倫理實踐中感受是相妥帖的,在日常生活行為中,人們的道德認知和道德行動很難區分先后,二者應該是相互砥礪、相互促進的。不過,王夫之也不能無視宋明理學討論火熱的知行次序問題。在知行次序的問題上,他獨異前人,提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王夫之認為,“行而后知有道”,“行焉而皆有得于心,乃可以知其中甘苦之數。”又說“故學焉而允合于道之甚難也,非力行者果不能知也。”與程朱將知作為行的前提相反,王夫之將行做為知的前提,而且認為行要高于知,他說:“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他認為,既然行得知的目的和效用,知的目的一定是為了行,但行卻不必是為了知,因此,行可以兼知,反過來則不可能,這樣,王夫之就把行提到了高于知的地位。王夫之的上述觀念,有類于后世所謂“實踐出真知”的觀念,指出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實際上是先有人們的實踐,然后才能總結歸納、抽象概括出所謂“知”,這也符合一般意義上人們的日常經驗。
關于程朱學派、王陽明、王夫之的知行哲學,張岱年先生曾經提出:“三派雖然立說不同,但是都肯定‘行’的重要。這是中國倫理學說的一個特點,即肯定倫理學說不僅是理論,更必須見之于行動。”誠如所言,宋明儒家對于知行關系的辯論,表面看上去似乎針鋒相對,在知、行次第上各有主張,但其實質都是在強調生活實踐中道德修養的重要性,都是強調“行為重”,主張生活踐履的第一位,因為無論知、行,都是關乎修養問題的道德認知與道德行動,而修養問題的實質在于人的實踐行動。歷來所批評的“假道學”,在認知方面不可謂不豐富,但如果沒有行動中的真誠落實,其豐富的認知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門面。
三、知行哲學與修養之方
在儒家哲學里,知是道德意識,行是道德行為,都不是純粹理性的問題,而是實踐領域中的事情,那么它們在生活實踐中指向哪里呢?如前所述,在中國傳統思想里,儒家最喜言知行,尤其是宋明新儒家,程朱陸王,幾乎無一例外都涉及了知行問題。我們知道,在儒家那里,道德意識、道德認知的內容無外乎發端于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仁、義、禮、智、信以及忠、孝、節、義等倫理觀念,這些倫理思想內容,在儒家看來,具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恒常色彩。在近代之前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前,儒家學者幾乎沒有什么人會質疑先圣制定的綱常倫紀,這些既定的具有知識性色彩的教條,具有神圣性。所以在儒家談論“知”的時候,分歧只是在于儒家道德知識究竟在內還是在外以及如何去認知等問題上,而對倫理道德的內容大體上沒有疑問。
儒家內部對于“知”的內容沒有什么大的分歧,雖然程朱理學有將“知”向外在知識拓展的理論取向,但其本質上還是在追求體現道德原則的“天理”。故而,從本質上說,儒家對于“知”之理解,區別主要在“如何知”的問題上。但在“行”上,也就是道德修養問題上卻有著多重維度的指向,多數有建樹的儒家學者都有一套自己頗為自得的修養之方。
《論語》中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主張在“學”和“思”中來落實修養功夫,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另外,孔子還對人的道德修養提出了“求之于己”、“躬行實踐”等等要求,即希望人們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來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在先秦儒家群體中,孟子的修養理論較為廣博深厚。孟子重視內向的心性理論,因而也格外強調人的道德修養。性善論肯定了人人可以為善,但不是說人人都已經為善,要真正做到善,還需要經過一番修養功夫。在孟子那里,修養功夫首先是要從發揮仁、義、禮、智四德。仁、義、禮、智四種德性雖然是人的內在稟賦,但如果不能時時加以自覺并將其在現實生活中予以落實,還是不能實現儒家人之為人的道德理想。孟子認為,道德修養既不能由別人代替,也不能抱怨他人。在道德修養過程中,要具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的道德自律意識。在求助自身的時候能夠“反身而誠”,通過自反使天賦的善性切切實實地體現在自己的言行思想中。只有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要求了,才能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榜樣。可以看出,孟子十分強調道德修養過程中的個人自身的責任,也即是個人的修養工夫。
宋明新儒家在孟子工夫論的基礎上又做了更多的發揮。宋明新儒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提出并實踐各種“為學工夫”,為學工夫在宋明新儒學里就是特指具體的修養方法。如,程顥主張“誠敬”,強調誠敬功夫來積極涵養德性,但程顥認為誠敬也不要過分著力把持,不要因為誠敬妨礙了和樂,破壞了內心的自然平和。程頤主張“持敬”,講究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的“主敬”,要求人從外在舉止與內在思慮情感兩方面嚴格約束自己。另外,在修養論上,二程還強調格物窮理,要求人們在事事物物上體認天理,通過遍求多識的積累涵養功夫來探求事物中蘊含的天理,并通過在人倫中踐履天理的要求,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朱熹在為學工夫上,主張發道心之微、去人心之危,堅持“存天理、滅人欲”的方針。朱熹提出“格物窮理”的工夫路徑,這就是要接觸具體事物并向極處去探究事物之理,其目的是要達到對事物的“所以然”和“所當然”的了解,也就是了解事物的普遍本質和規律以及社會的倫理原則和規范。“格物窮理”在朱熹那里,具有明顯的知識取向,但它的目的并不是只是為了探求客觀知識,而是通過窮究萬物之理的認識論途徑,最終落實到人倫實踐和性命本原上來。陸九淵在同朱熹關于為學工夫的論辯中,強調“尊德性”對于“道問學”的優先性,“尊德性”指的是心性的道德涵養,而“道問學”指的是經典的研究。陸九淵認為,為學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道德的境界,經典的學習或外物的研究都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人的本心即是道德的根源,只要擴充、完善人的良心結構,就能夠實現這個目的。正是如此,所以陸九淵反對朱熹格物窮理的“道問學”工夫,而主張直指本心的“尊德性”工夫。當然,作為一個儒家知識分子,陸九淵也不是要徹底反對讀圣人之書,他的根本意思是在強調“尊德性”為本,“道問學”是末,“道問學”要服從于“尊德性”。王陽明的道德修養論可以用“致良知”三字概括之。王陽明認為,作為本體的良知有被私欲蒙蔽的可能,因此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在王陽明的思想里,一方面是指人應擴充自己的良知,擴充到極限,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的是非善惡,在行動中實在的體現出來,從而加強為善去惡的道德實踐。另外,王陽明的修養論還具有即工夫即本體、即知即行的特點,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知行合一”。王陽明一方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要求人們在內在精神上下功夫,一方面重視道德的實踐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煉,要言行一致。
當然,縱觀儒家的修養理論,從孟子開始,主要還是一種心性鍛煉的工夫,而較少涉及具體實踐。所以在嚴格意義上還稱不上認識論意義上的“行動”。孟子以及宋明儒家主要是從心性理路上談修養的,所以儒學也往往被人們稱作“心性之學”。當然,之所以顯現出心性的特質,主要是因為我們關注的都是儒家的理論層面。實際上,在政治事務、日常生活等方面,儒家還是以行動見長的,在傳統的生活場景里,政治禮儀、禮樂教化、日常應對中都是儒家實踐其倫理信念的具體場域。
另外,心性儒學中對于修養的認識,實際上更是一種道德心理的培養。孟子開出儒家內圣的路徑并經宋明新儒家的努力,儒家的道德心理或者說道德信念培養的學說可謂是不斷發揚光大。如果從道德心理或者道德情感的角度來看傳統的知行之辨,我們會發現,所謂的知行之辨,不過是如何培養道德心理、道德信念并把這種心理或情感在道德實踐中釋放出來的問題。所謂“知先行后”,是在強調先有道德心理、道德信念而后才能有道德行為;所謂“行先知后”,是在說只有不斷進行道德踐履才能培養起合適的道德心理、道德信念;而所謂“知行合一”,就是在強調萌發道德心理的同時實際上已經在從事道德行為了,把人的情感意志或者說動機和行為等量齊觀。在這個意義上,除了認識論層面上的討論,所謂的“知行難易”、“知行輕重”的問題也可以化約為道德心理、道德情感的培養與道德行為的實施孰難孰易、孰輕孰重的問題。
故而,儒家思想中圍繞“知行”的辯論,更像是一場為了更好進行道德實踐的“思想實驗”,其目的歸根結底還是如何培養道德心理、道德情感(知)并如何適度釋放出來(行)從而實現道德理想(仁、義等)的問題,也就是說,儒家知行之辯是如何更好實現“行動”問題的具體展開,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實踐哲學。
四、倫理實踐與政治實踐
近代以來,傳統儒家圍繞知行問題展開的辯論,逐漸從道德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人們往往更容易從政治層面來反思認知與行動的關系。我們試以影響較大的孫中山的知行哲學為例,做一分析。
如前所述,《尚書》、《左傳》里都提出了知易行難的說法,孫中山稱這一說法影響中國思想幾千年,這和注重實踐理性的中國傳統文化是相契合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老格言,通過被奉為經典的《尚書》的記錄和傳播,一直為眾多讀書人所熟悉,甚至成為教條。就其本身意義而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觀念,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一方面可以激勵人們注重實際行動,反對“空知不行”的玄虛習氣;另一方面也往往會成為人們不下工夫求知、同時又畏難不敢實行的借口。針對它的消極一面,孫中山先生就曾提出過猛烈的批判。孫中山曾不無激憤地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于滿清。”在孫中山看來,“知易行難”的學說妨礙了人們去積極地接受新理論、新思想、新計劃,進而畏懼革命行動,以至于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害。
與“知易行難”說針峰相對,孫中山提出了“知難行易”的知行學說。孫中山認為,知易行難之說的危害,主要在一個“難”字上。一般人都趨易避難,因此以行為難的舊說,從心理上給人們積極采取行動設置了障礙,未行動時心已怯了。在孫中山看來,畏難而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也。除了破除“行難”給人們帶來的思想障礙,孫中山還認為“知易”一說使得人們輕視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也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所以,孫中山認為,傳統的“知易行難”學說的根本錯誤在于顛倒了“知行難易”的本來面貌,使得人們既輕視革命理論的認知,又怯于革命的行動,結果一事無成。孫中山對他自己的“知難行易”十分自信,從他將“知難行易”名之曰“孫文學說”也可以看出一二。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時代色彩相當濃厚,我們認為他是針對當時的民主革命出現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從本質上來說,孫中山畢竟更多的是以一位革命家姿態出現在中國思想歷史上的。孫中山談知、行,主要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屬于政治哲學領域的話題。他認為“知難”,是為了促使人們重視革命理論,而談“行易”,是為了鼓勵他的革命同志不要畏懼艱難而放棄革命。總體來看,孫中山用民主革命的實際經驗和近代科學知識充實了傳統儒家哲學中的知行觀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突破了自孔子以來在倫理道德意義上論辯知行的局限,而賦予了知行學說以近代認識論和政治哲學的意義,試圖突破道德修養的藩籬而談知、行,這在中國傳統知行哲學發展的歷程上是有新意的。孫中山突破知行學說上的泛倫理主義,從個人的修養領域走到公共的政治哲學領域,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問題意識轉換的一個趨勢。也就是從言必稱道德倫理轉而和西方哲學的問題范式相結合,從倫理中心主義中走出來,進而關注哲學思考的其他領域。
孫中山之前的儒家提出的各種認知與行動關系的學說,主要以倫理問題為中心,我們現在談知行學說不能脫離這樣一個思想史背景。儒家的知行是道德意義上的知行,也就是“知”意味著道德信念、道德認知,而“行”意味著道德行為、道德修養,這是傳統知行學說的基本前提。而我們當代人所說的認知與行動,是從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與實踐角度去理解的,知是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行是實踐。隨著近代革命的興起,傳統的“知行哲學”為政治浪潮所裹挾,從道德哲學演變成政治哲學的問題,但總體上看,還是和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認知與行動有所差別。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思想家所討論的“知行問題”,雖不囿于傳統道德修養領域,但依然是關乎人的現實具體行動的問題,沒有從考察人的認識能力的抽象角度思考知行問題,沒有出現類似于近代西方哲學那樣從人的認知能力角度來思考認識問題的思想,只不過是伴隨著社會關注點的轉移,從道德修養領域轉移到政治修養領域,沒有進入到純粹理性的世界。后來,毛澤東在《實踐論》里所討論的認識論問題,從根本上而言,也是一種政治哲學,這是討論近代哲學中的“知行問題”所必要考慮的。
[注釋]
責任編輯:郭美星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79(2016)03-0041-09
[收稿日期]2016-01-22
[作者簡介]朱承(1977-),哲學博士,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