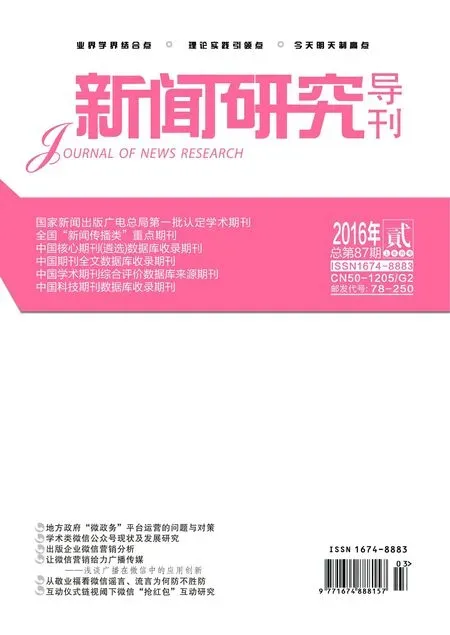淺析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謠言
伍麗美(江西師范大學 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
淺析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謠言
伍麗美
(江西師范大學 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作為一種有深厚淵源的傳播文化,謠言有其獨特的傳播規律與特點。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媒介的發展,這種規律和特點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演變。從古代的神話、傳奇到現代的假新聞,謠言改變的從來都只是形式,不變的是本質。相較于消滅謠言而言,提高公眾的文化自覺顯然更有利于阻止公眾在謠言文化中的迷失。
關鍵詞:謠言;傳播;文化現象;文化自覺
無論人們如何治理,謠言始終作為一種古老的信息傳播現象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難以根除。法國結構主義學者弗朗索瓦絲·勒莫說過:人們可以說像不存在沒有神祗的社會一樣,也不存在沒有謠言的社會。[1]謠言以其與歷史同齡的深厚資歷,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在歷史的推演與變遷中也絲毫沒有顯露出要退出歷史舞臺的意味。從文學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具有明顯意識形態屬性的謠言不僅是歷史的一部分,還是文化大傳統的組成部分。因為只有放在文化這個大背景中,才能更準確地通過謠言本身揭露歷史,從而實現與現實對話。
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謠言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謠言都是自古有之,并且從未間斷,但這種由來已久的謠言現象并未被劃入中國文化的范疇,與之相對的西方文化確是歷來重視對謠言的研究。國外關于謠言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期間,很多美國學者從個體心理學視角(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的《流言心理學》)、精神分析視角(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社會學視角(勒莫《黑寡婦:謠言的示意及傳播》)及歷史學視角(漢斯約阿希姆·諾伊鮑爾的《謠言女神》)對謠言進行了研究。諾伊鮑爾從深層大傳統動力的角度,認為“謠言的修飾變異絕不是憑空臆造的,也不完全是邪惡的化身,而是歷史的一部分,根源于民族集體無意識,并承載著歷史的呼應,喚醒的是集體記憶。謠言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文的歷史”。[2]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世界最古老的傳媒”,并明確指出“不論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哪一個領域,謠言無處不在”。[3]謠言不會消失。
國內學者對傳統媒介環境下一般性謠言傳播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等西方學者的結論,且集中在對謠言傳播的特點、規律、控制策略的研究。將謠言與文化關聯起來的研究相當少,張九海(2013)將網絡謠言視為“三俗”文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認為打擊網絡謠言是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舉措。[4]石慧敏(2011)從民間信仰、“官本位”心理、“面子”觀念和“重義輕利”心理等幾個方面,探討了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對謠言傳播中公眾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并提出規避其負面影響的相關策略。[5]劉緒義(2006)指出謠言的本質在于其傳播的過程,認為謠言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還以易傳播、傳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學科性等特點構成類似于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6]李永平(2014)從人類文化大傳統的角度對謠言敘述進行剖析,認為謠言敘述是一種以尋求意義,應對存在焦慮,進行自我療救的廣義敘述。[7]
由此可見,目前學者們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謠言本身及其應對策略上面,基本上著眼于謠言的危害性,而忽視了謠言作為一種能夠給社會帶來啟迪和反思的文化現象,已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態。而我們在探討謠言問題時,如果想擺脫此點,后果往往不堪設想。
二、謠言這一文化現象的內涵
從古至今,謠言始終伴隨歷史左右,以其帶有杜撰成分的即興或非即興創作迷惑著人類。并且,隨著媒介信息技術的更新進步與社會轉型的不斷加劇,謠言不但沒有越來越少,反而愈演愈烈,無孔不入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成為社會輿論的“常態”。
(一)謠言以神話、傳奇、故事的形式傳播
有一則名叫《咕咚來了》的童話故事,講述的是森林里的小動物們將木瓜掉進水里發出的聲音當作可怕的怪物而引發的笑話。這則簡單的故事卻蘊含著深刻的寓意,它反映出現實生活中謠言傳播的途徑以及存在的廣泛性。無論是讓人津津樂道的神話故事,還是多么荒誕離奇的市井傳奇,傳播的社會基礎都是不確定的環境變化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在我國古代,就有用神秘玄妙的語言來預測未來的“讖謠”,人們對未來的擔憂以及普遍缺乏理性的思維被反映在各類奇聞怪談里,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
(二)謠言在微博、朋友圈等人際交往平臺傳播
移動互聯網時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的出現使謠言改變了原有的傳播特性。謠言的傳播變得更加快捷簡便,只要點擊復制或者轉發,不辨真假的信息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得到廣泛傳播。相對于公開傳播的微博、論壇來說,微信傳播是由一個個的朋友圈維系起來的,這種基于“病毒式”的人際傳播關系網具有相對的私密性。固有的關系優勢為謠言明確了信源,無形中增加了謠言在微信傳播中的影響力。分析微博、微信這一類社交平臺上傳播的謠言,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類:一是假冒官方發布消息;二是裝“知識控”進行科普;三是“冷炒”多年前假新聞;四是靠恐嚇迷信騙關注;五是利用人們的善良與同情心傳謠。這些謠言往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很容易成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因此,人們需要提高警惕和信息辨識能力,以免陷入謠言傳播構建出來的社交“偽”文化之中。
(三)謠言借助大眾媒介傳播
在速度與時效成為價值標桿的今天,謠言也乘著這陣“求快”之風越走越遠——不僅流連于歷史文化與社交平臺,還轉而向新聞界進發。“假新聞”頻頻出現,引發公共媒體的深刻自省。當下自媒體泛濫,公共媒體不加甄別就隨意轉發自媒體消息似乎已成為“習慣”,這種壞習慣很容易轉發假新聞,不僅會鬧出令人尷尬的烏龍,還有損媒體的公信力。2016年伊始,受到廣泛傳播的“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男友家”的網帖引發了包括網民、自媒體以及傳統媒體在內的全
民熱議,最后卻被證實為純屬虛構。由該貼文衍生出來的話題、文章在各個媒體平臺上的點擊量多達上億次,令人無限唏噓。至此,謠言已不再是人們悉知的謠言,它化身為“新聞信息”,借助各類傳播媒介得到了光明正大的傳播。調侃世人的同時,也以文化偽裝了自己。
只有放在文化背景中,謠言才能顯出其本來面目:謠言會一直存在,也會通過網絡等新媒介得以繼續傳播。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消滅謠言本身而言,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反而是如何發揮謠言探尋真相的特性,學會與社會文化和諧共生這一核心議題。政府和媒介組織在動員社會進行強化整治時,更應該做且更能產生效用的,是使廣大公眾對新媒體時代泥沙俱下的謠言傳播有清楚的認知和正確的應對能力。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充分利用費孝通先生所講的“文化自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8]有關研究者和管理者認為,文化自覺是提高網絡傳播自律性的最根本的途徑。對于當下的網絡謠言傳播而言,雖然這種文化自覺的培養和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但卻更能發揮根本性的作用,使廣大公眾在面對突發事件時能夠更理智,不輕信謠言、不傳播謠言,進而主動辟謠。
參考文獻:
[1] 王娜.新媒體環境下謠言傳播的社會心理因素研究[J].現代視聽,2013(06):74-75.
[2] 漢斯-約阿希姆·諾伊鮑爾(德).謠言女神[M].顧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75.
[3] 讓-諾埃爾·卡普費雷(法).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M].鄭若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4] 張九海.“大V”“大謠”和網絡大治——關于網絡謠言的深度思考[J].前沿,2013(20):7-8.
[5] 石慧敏.傳統文化心理與謠言傳播中的公眾態度和行為[J].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3):111-114.
[6] 劉緒義.文化詩學視野中的謠言傳播[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2):12-16.
[7] 李永平.文學人類學視野下的謠言、流言及敘述大傳統[J].思想戰線,2014(02):23-29.
[8] 費孝通.文化的生與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8.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江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網絡傳播視域下謠言傳播者的心理研究與應對策略(項目編號:YJS2014077)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16)03-0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