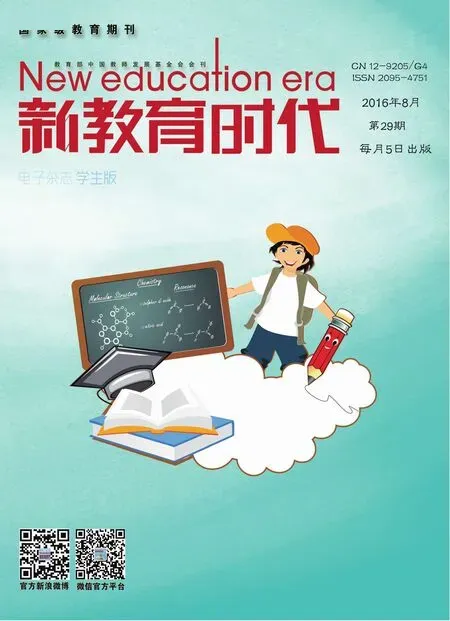飛白留課堂 思緒任翱翔
王雪川
(北京市高家園中學 北京 100000)
飛白留課堂 思緒任翱翔
王雪川
(北京市高家園中學 北京 100000)
飛白,是中國書畫藝術的一個術語,是藝術家構圖用筆時有意空出或留下的白地,目的是留給人們思考的藝術空間,是鮮明筆觸的詩化延伸。欣賞者可以由此延伸作者的思想,把自己的生活、人生感悟揉進畫意筆端,去把自己的靈性與作者的創意對接,去沿著作者布下的“圣地”做思想的自由翻飛。
語文教學作為一門藝術,與書畫藝術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將“飛白”移植到語文教學之中,不僅能豐富學生的思想,發展他們的思維,提高他們的語文素養,而且能激活語文課堂,使課堂更有生機,更加有效。
語文課堂的“飛白”,就是教師在充分了解學生的基礎上,在引導學生學習語文的過程中,藝術地去處理教材、安排課堂的一種教學方式。一篇文章,可以只講某段;一個知識,可以只作點撥提示;一篇作文,可以預設開頭和結尾;其余的都可以大膽的留給學生。這種手段,是教師為學生設置“憤”、“悱”狀態、調動情感的過程,也是抓住主要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
我們為什么要追求這種境界呢?
首先,這是向講風太盛的語文教學陋習的挑戰。傳統的語文課,或者說現實中大多數的語文課,往往是教師課前收集大量資料,精心準備,寫出十幾頁的教案,然后信心十足的到課堂里滔滔不絕的去“講”。教者從作家作品、時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題思想、寫作特點到課后練習都一點不落地去講深講透,唯恐某個知識點有遺漏,唯恐某個問題沒有講清楚。課堂上學生一個勁地聽,一個勁地記,下課后一個勁地去背。這種教學,學生成了教師傾注知識的容器,成了一個個沒有絲毫活氣的物,一個個純粹的“自然之物”。這種課堂只是教師展示知識和口才的舞臺,只是用知識構筑起來的實心的墻。講求“飛白”的課堂,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師在只作稍微的提示的前提下,作為課堂的參與者、組織者、引導者,走下講臺,深入到學生中間,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學習,去思考,去探究,去掌握該掌握的知識。
第二,運用飛白,有利于中國語言藝術靈活性的張揚。方塊為形的漢語言,表音功能之外,重要是表意,無論是一個字還是一個詞都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世界上其它文字相比,它是最具表現力的語言藝術,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智慧的結晶。“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要體味這書中的“天光云影”,需要我們調動自己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思想,揉進我們的想象。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課堂上只有把理解認識的主動權交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去品評感悟,學生才能真正進入知識瑰寶的洞天,欣賞體驗到無窮的藝術魅力,學生才能把中國語言藝術的精髓與靈性化為自己的血肉。從這個意義上講,教師大包大攬的講習方式,就是對中華民族文明的一種拋棄。
第三,運用飛白,是時代的要求,課改的需要。“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說》的出現,傳道,授業,解惑,就成了教師信奉的準則。他們認為課堂上去“傳”、“授”了,就把“道”、“業”、“惑”的問題解決了,自己的職責就完成了。這種看法在韓愈所處的農業經濟時代是合理的。而對于知識更新日趨加快、信息日益紛繁多樣的今天來說,卻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讓學生學會學習,掌握學習的本領,養成不斷求知的習慣,形成終身學習的必備的素養,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把課堂當作知識的場所,讓知識從教師一方轉移至學生一方,雖然學生也可獲得知識,但這些認知,學生難以鞏固,難以形成穩定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學生也無法透過知識的探求過程學會學習,學會主動吸收知識,更無法成為知識的創新者。學生是有著獨特個性、鮮活生命力的大寫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自己判斷是非的標準,有自己的知識體驗,有著自己的成長背景,教師所要做的不是從外部去強制地灌輸知識,讓學生原封不動地“克隆”出這些知識,而應是用自己的教學去激發他們的求知欲,由內而外地引導學生去認識知識,也就是說,教師所做的不應是為“知識”,而應是引導學生去“知”“識”。“飛白”的教學形式強調舉一反三,強調遷移啟發,強調學生主動學習探求,根本上就是為了突出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讓他們從求知中培養自己的“識”。
真正意義上的課堂的“飛白”,應該解決好三個問題。首先是教學觀念。要真正樹立起“語文課程應致力于語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致力于學生全面和終身發展的語文教學觀念,真正樹立起學生是教學的出發點和歸宿的觀念。第二是要充分相信學生、尊重學生和了解學生。相信他們的思維,相信他們的靈氣,相信他們的聰明才智。教師心中應時刻具有“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思想;要尊重學生學習過程中的獨特體驗,尊重學生的自主人格,尊重學生的生命價值;要充分了解學生,了解學生的知識結構狀況,了解學生的審美情趣,了解學生的生活體驗與感悟。第三是“飛白”的藝術化問題。應該說藝術地“飛白”,它是教師不斷探索,不斷總結,在教學中縱情揮灑的一種化境。要進入這種化境,首要條件是教師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教學智慧,具體表現在對知識了然于胸,認識視角獨特,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恰到好處;其次是對教材、對編者意圖、對全局把握的程度;再就是選取恰當的形式來布“白”的問題。學習一種知識、一篇文章的切入點是很多的,教者不同,學習對象不同,課堂的情境不同都會對布白的形式產生影響,這正如不同畫家在構思創作同一個內容的作品時,在畫面安排、用筆用墨、風格等方面會有不同一樣 。教學中,“飛白”可以是以點帶面,以管窺豹,從開頭發散結尾,從結尾溯源開頭,可以是從敘述去開發描寫議論抒情,以環境來觀照人物情節主體,可以從現實遙想古代,從古代勾勒未來,從時間躍入空間,從現實幻化虛境,等等。但有一點,這“飛白”必須是學生去“飛”,是學生在探索,是學生在動腦動手,是學生在“知”“識”。
書本只是語言符號世界,發揮教師的智慧,讓課堂煥發出生機和活力,這就是教學的藝術。語文課上只要我們大膽而藝術地去“飛白”,就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就能通過學生的動腦動手,培養他們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因此,課堂上藝術化的“飛白”,就如同阿基米德夢想的撬動地球的支點與杠桿,教學中如果真正進入這種化境,我們就能引領學生解讀蒙娜麗莎的微笑,接上維納斯的斷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