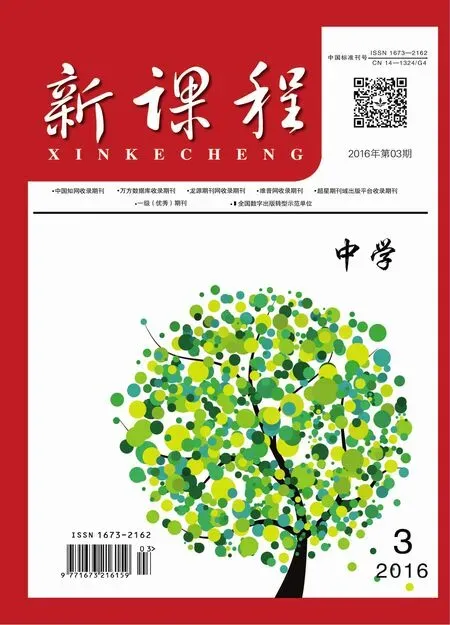新課程教學(xué)中如何提高學(xué)生的文學(xué)作品欣賞能力
閆春格(河南省靈寶市第一初級中學(xué))
新課程教學(xué)中如何提高學(xué)生的文學(xué)作品欣賞能力
閆春格
(河南省靈寶市第一初級中學(xué))
“文貴遠(yuǎn),遠(yuǎn)必含蓄。”選入初中語文新課程試驗課本的作品大都“筆墨之外有筆墨,情趣之外有情趣”。我們在教學(xué)中要注重學(xué)生文學(xué)閱讀和欣賞能力的培養(yǎng),教會學(xué)生品讀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美、意境美、結(jié)構(gòu)美、細(xì)節(jié)美和蘊藉美。
一、品讀語言觸摸意境
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所代表的意向經(jīng)巧妙結(jié)合,往往形成一種特殊的藝術(shù)境界,它似于生活圖景,又更美于生活圖景,讓人沉浸流連,顯示出了文學(xué)的美學(xué)意義。
如《荷塘月色》中的“微風(fēng)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yuǎn)處高樓上的渺茫的歌聲似的”這句話,它悠長的韻味,就在于時斷時續(xù)的“荷香”與“遠(yuǎn)處高樓上的渺茫的歌聲”這兩個藝術(shù)形象,使用了移覺手法。讓學(xué)生發(fā)現(xiàn)圖畫并去想象,與學(xué)生共同徜徉于美麗圖畫中,那么課堂的氣氛和課后效果一定倍佳。
在講授辛棄疾的《破陣子》時,我先串講各句的意思,然后讓學(xué)生想象各句所描繪的景像,一幅幅畫面扣人心弦:醉后拔佩劍,夢醒響號角,八百里連營,壯士炙肉痛飲,這是何等磅礴的氣勢!看,還有的盧飛快,弓弦震動,赤誠的呼喊,沙場上的兵陣,為“君王天下事”所有的豪情、赤誠都描繪與景物之中,讓人感動。最后“白發(fā)生”,可想詩人孤燈下,白發(fā)獨坐,壯志難酬,思國思家的了然身影,催人淚下。這首詩蒙上悲壯色彩,主題不講已明,學(xué)生的思維活躍、想象力、創(chuàng)造意識也得到發(fā)展,正適應(yīng)了語文新課程教學(xué)所要求的喧騰與熱烈。
二、感悟細(xì)節(jié)挖掘意蘊
語文教學(xué)重視積累、感悟、熏陶、閱讀。其中感悟為最高層次,它是閱讀中對情、景、理的聯(lián)想、采擷出來的一些升華的東西,它不是對淺層語言文字的理解,而是知識經(jīng)驗的升華。
《孔乙己》中,從孔乙己出場就是他“穿長衫,身材高大,臉色青白,一部亂蓬蓬的花白胡子,身上又臟又破“的外貌描寫,那么怎樣走進(jìn)咸亨酒店的呢?讓學(xué)生去想,是低頭,是昂首等等,讓學(xué)生充分發(fā)揮想象力,然后再看孔乙己是很斯文地昂首進(jìn)店,甚至不理不睬短衣幫的哄笑,便“排出九文大錢”等等,分析其性格的酸氣、迂腐,舊封建文化的糟粕毒害的靈魂,就充分展現(xiàn)在學(xué)生的面前了。
詩歌教學(xué)也是這樣。比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后兩句“正是江南好風(fēng)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寫今日相逢正是風(fēng)光秀麗的江南已到了流水落花的時節(jié),這“落花時節(jié)”包含不少內(nèi)容,既是明敘相逢的季節(jié),又暗喻了唐帝國由盛入衰的局面,作為人生的歲月,兩人又到了落花時節(jié)的暮年,這四字寫得十分深沉含蓄。而“又”字抒發(fā)了詩人撫今追昔,感時傷世之情。清朝蘅塘退士評說:“世運之治亂,年華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
三、分析技法學(xué)習(xí)結(jié)構(gòu)
在培養(yǎng)學(xué)生審美情趣的前提下,有必要在學(xué)生理解作品結(jié)構(gòu)的整個思維通道的關(guān)鍵處巧設(shè)懸念,以此為路標(biāo)誘導(dǎo)學(xué)生對謀篇布局作較深入的賞析和品位。
茹志鵑《百合花》中伏筆的運用,讓故事情節(jié)前后呼應(yīng)扣合,尤其是細(xì)節(jié)的前后照應(yīng),使得情節(jié)嚴(yán)絲合縫。如“借被子”這一情節(jié),可以說是支撐了整篇小說的情節(jié)發(fā)展,再如“小通訊員肩上撕開的一個口子”反復(fù)出現(xiàn),使情節(jié)豐富而嚴(yán)密。
在教學(xué)《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時,我設(shè)計這樣的問題:起初我們一家人為什么天天盼于勒?后來又為什么躲于勒?學(xué)生討論明確,本文按照主人公菲利普夫婦“盼于勒—贊于勒—見于勒—躲于勒”的情節(jié)構(gòu)思,波瀾起伏,設(shè)置懸念,引人入勝,運用插敘,讓故事情節(jié)巧妙真實,結(jié)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精妙的結(jié)構(gòu)展示著菲利普夫婦對于勒的態(tài)度變化純粹是金錢的力量使然。花花公子時期的于勒是菲利普家的包袱,家里容不下他,只有請他離開家鄉(xiāng)漂洋過海流浪美洲;發(fā)了財?shù)挠诶帐侨业摹案R簟保涣骼藵h的于勒是菲利普夫婦避之不及的瘟神。而菲利普夫婦見到于勒后態(tài)度變化的細(xì)節(jié)正是全文最精彩之處,多的不談,僅文中“暴怒”一詞就蘊含了豐富的內(nèi)容。“乞丐”于勒打破了對“好心的于勒”寄予太多期待的菲利普夫人全部的夢,躋身上流社會的夢想,嫁女兒的希望,未來體面的生活……一瞬間通通成為泡影,都是因為這個“賊”錯誤地出現(xiàn)在眼前,他這樣陡然地出現(xiàn)把她的一切都?xì)Я耍瑳]有任何預(yù)兆,不給她任何準(zhǔn)備,氣急敗壞、歇斯底里的菲利普夫人來不及做一丁點心理和外在的掩飾,“暴怒”是她面對殘酷現(xiàn)實脆弱的抵觸情緒瞬間的真切爆發(fā)。也只有這樣才最能夠赤裸裸地暴露菲利普夫婦的虛偽和勢利,最能充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guān)系。如果反過來于勒某一天偷偷來到菲利普家門外,遠(yuǎn)遠(yuǎn)地看一眼自己的哥嫂,那真實的菲利普夫婦讀者就永遠(yuǎn)看不到了,小說的主旨也就不能得到有力地揭示了。像這樣,教會學(xué)生發(fā)現(xiàn)謀篇之妙,安排之巧,以后他們就會思考在寫作中如何運用。
語文是對人類生命過程中一切活動描述和想象的科學(xué),文學(xué)欣賞在語文教學(xu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要帶著欣賞的目光去學(xué)語文,根據(jù)文學(xué)欣賞的規(guī)律指導(dǎo)學(xué)生欣賞作品,采用多種形式引導(dǎo)學(xué)生產(chǎn)生感受、進(jìn)行思考、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從而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學(xué)欣賞實現(xiàn)對學(xué)生德、智、美等素質(zhì)的進(jìn)一步培養(yǎng)和提高。
·編輯 楊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