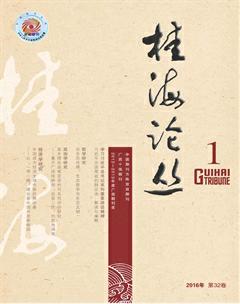論生態倫理、生態哲學與生態文明
盧風
摘 要:人類正面臨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直接根源是現代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所導致的大量排放。現代經濟、政治制度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現代性——則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提供了系統的辯護。以現代性為指導思想的現代工業文明是不可持續的。現代性是包含嚴重錯誤的。現代性的基石是獨斷理性主義,其要害則是普遍化的物質主義價值導向。當代最新科學和哲學研究表明,獨斷理性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整個現代性的體系坍塌了,則物質主義的荒謬性立顯。生態學告訴我們,地球生物圈無法承受幾十億人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建設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生態哲學將會凝練生態文明建設所必不可少的時代精神。
關鍵詞:現代性;生態危機;生態文明;生態哲學
中圖分類號:B82-0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6)01-0024-13
自19世紀的鴉片戰爭以后,現代化一直是國人的夢想。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奇跡般地加快了。如今,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各種工廠越來越多,城市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大,幾乎家家有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人人有手機,私人轎車也越來越多,……與30多年前相比,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么,我們的生活是不是越來越幸福了?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們會給出不同的回答。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國在財富急劇增長的同時,各種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在迅速加劇。自2013年以來,全國多處常常出現嚴重霧霾。在霧霾天氣里,許多人會感到心情抑郁。嚴重污染了的環境會引起多種疾病,疾病中的人們當然也不幸福。國家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說:“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1.9萬億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鋼鐵、銅等消費也占世界的40%以上。發達國家幾百年出現的資源環境問題,在我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表現出來,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氣污染非常嚴重,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環境安全的問題時有發生。我國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資源能源問題比任何國家都要突出,解決起來比任何國家都要困難。”[1]環境污染的深層根源是什么?嚴重污染與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有何關聯?主流生產生活方式與我們的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是否有內在的關聯?為建設生態文明,是否需要根本改變我們的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回答這些問題,勢必涉及倫理和哲學。并非所有的倫理學和哲學都回答這些問題,直接回答這些問題的倫理學和哲學是生態倫理學和生態哲學。
一、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的根源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逐漸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在許多國家同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如今,大部分明理人都承認,現代工業文明引起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或簡言之,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科學家和生態學家告訴我們,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直接根源是現代化生產和消費的大量排放,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例如,2013年以來我國京津冀地區的嚴重霧霾就源自許多工廠和大量汽車的排放。現代人的人均排放量或人均生態足跡比前現代人大多了,我們每天都會產生比前現代人多得多的垃圾(廣義而言,既包括汽車尾氣也包括各種商品包裝),與前現代相比,現代人口又翻了數倍,于是有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簡言之,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直接根源是巨量人口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
那么,現代人為什么采取“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呢?前現代人并不這樣。前現代的統治階級和富人中當然不乏驕奢淫逸、揮霍浪費者,但廣大勞動人民卻總是勤勞節儉的,正如孔子所教導的,謹身而節用。在一個普通勞動者家庭,鍋碗瓢盆一類的用具,破了也舍不得扔,修修補補繼續用,一件衣服破了,補好了繼續穿,破得不能再穿了,還可以改作他用。哪像我們今天?東西舊了,或不時髦了,就扔!例如,在今天的城市居民中,已沒有穿帶補丁衣服的了,更不用提大家都用許多一次性用品。人們已習慣于大量生產條件下的大量消費和隨意拋棄,如,幾乎每天都會拋棄幾個塑料袋。不僅富人如此,普通市民亦然。為什么?有多種原因。
首先,產生于18世紀歐洲的現代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了物質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人類可大量使用煤、石油、天然氣、鈾等礦物資源,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人類第一次具有了這樣的生活條件:勞動者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不僅可保障富人們過窮奢極欲的生活,而且也越來越能保障民眾滿足其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廣大勞動人民似乎也不必謹身節用了。
其次,就全球的情況看,資本主義制度要求人們(包括民眾)大量消費、大量拋棄(或大量排放)。只有這樣,企業不斷大量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賣得出去,企業家才能賺錢,GDP才能增長。如果廣大民眾皆謹身而節用,則大量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人買,企業家無法賺錢,GDP也無法增長。而現代社會把GDP增長看作社會發展的基本標志。所以,現代社會制度不僅激勵大量生產,也激勵大量消費。以現有的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必然導致大量排放。
再次,制度植根于人們的信念體系,現代人的信念體系就是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提供了相對周密的辯護。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之前,同樣追求現代化的前蘇聯及其東歐聯盟還在抵制資本主義,那么“冷戰”結束以后,資本主義已成為全球主導性的政治、經濟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意識形態就是西方現代性理論體系。其核心思想是物理主義自然觀、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反自然主義價值論、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和物質主義價值觀。根據這套理論體系,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生產生活方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就是人們在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框架(或社會秩序)中所干的天經地義的事情!多數人認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他們理直氣壯地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
可見,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直接根源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其深層根源卻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主流意識形態。
二、現代性思想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
我們也可以稱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為現代性(modernity)思想,如前所述,它包括物理主義自然觀、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科學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反自然主義價值論、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和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現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實則包含致命錯誤。不徹底駁倒現代性思想,就無法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續和極端危險,從而也無法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基礎。換言之,不根本改變現代人的信仰體系,就無從建設生態文明。以下我們將對現代性思想的各種觀點逐一進行分析。
(一)關于物理主義自然觀
物理主義自然觀的基本觀點是:大自然就是物理實在的總和,萬物皆是物理的,所謂物理的東西,就是最終可被現代物理學所說明的東西,連人的思維以及人類創造的文化也可歸結為物理的東西。物理主義如今又有了新的理論形態——計算主義,計算主義認為,萬物都只是個計算程序,連整個宇宙也只是一個巨大的計算程序。據此,大自然的奧秘是確定的,人類知識每前進一步,大自然隱藏的(即人類未知的)奧秘就減少一分。我們常說世界是可知的,就指這個意思。如果大自然就是這樣的,那么人類實在不必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我們所要做只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近三個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人們也確實是這么干的。
但當代新科學(耗散結構論、復雜性理論以及現代宇宙理論)已給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自然觀。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等科學家認為,世界萬物是不確定的。物理主義預設,世界的基本規律是與時間無關的,“從古典牛頓力學到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物理學基本定律所描述的時間都不包含過去和將來之間的任何差別。”[2]2說世界的基本規律是與時間無關的,即是說世界的基本規律是永恒不變的(據此才可說,人類知識每前進一步,則未知領域減少一分)。但普利高津認為:“自然界既包括時間可逆過程又包括時間不可逆過程,但公平地說,不可逆過程是常態,而可逆過程是例外。可逆過程對應于理想化:我們必須忽略摩擦才能使擺可逆地擺動。這樣的理想化是有問題的,因為自然界沒有絕對真空。”[2]18如果不可逆過程才是自然事物的常態,那便意味著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流變的,而且變化的并非只是現象,規律、秩序或結構也處于流變之中。
普利高津說:“我一直深信,理解耗散結構或更一般地理解復雜性的動力學起源是當代科學最引人入勝的主題之一。……這便根本改變了我們對自然的描述。在這種表述中,物理學的基本對象不再是軌道或波函數;它們是概率。”[2]73-74于是,“現在動力學規律有了新的意義。通過結合不可逆性,它們表達的不是確定性,而是可能性。”[2]126普利高津說:“大自然確實涉及對不可預測的新奇性的創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實在性更加豐富。”[2]72也就是說,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是具有創造性的,大自然隨時都會涌現新現象、新事物、新結構、新秩序,它不是固定不變的,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自然規律(不否定自然演變的穩定性,更不否認自然秩序的存在)。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可能發現什么“本原”“宇宙之磚”或“永恒不變的存在”。可見,以為人類知識每前進一步未知領域便減少一分的信念也是個錯誤的信念。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永遠都隱藏著無窮無盡的奧秘。正因為如此,人類才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二)關于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
獨斷理性主義包含這樣一些信念:理性即人類憑借語言(包括數學)去說明、預測經驗現象以至說明、理解、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人類文明的進步端賴理性的進步。理性進步就主要體現為現代科學的進步。科學知識就是理性發現或建構的知識,科學知識是客觀的、統一的,基礎科學知識(即物理學)進步的終極目標是發現關于自然的終極理論(a final theory)。終極理論就是關于自然之終極定律(the final laws of nature)的理論。把握了自然之終極定律就意味著“我們擁有了統轄星球、石頭乃至萬物的規則之書(the book of rules)。”[3]輔之以更加細致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人類就可以越來越隨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控制環境、制造物品、創造財富。
深入分析獨斷理性主義,我們可揭示其基本預設:1. 客觀知識是統一的,是在一個內在一致的邏輯體系內不斷積累的,科學知識體系能不斷地排除謬誤,積累真理,進而日趨完備(可能是個無盡頭的過程),可稱此預設為科學統一論;2. 大自然是完全可知的,即隨著科學知識的進步,大自然所隱藏的奧秘會日趨減少(這一點已包含在物理主義自然觀中),可稱此預設為完全可知論。
20世紀下半葉的科學、科學史以及科學哲學研究都表明,科學統一論和完全可知論都是站不住腳的。全面反駁科學統一論和完全可知論需要長篇大論,無法在此展開,以下僅給出簡短結論。
反駁科學統一論:1. 科學統一論設定,人類憑其理性可就“真理”或“客觀知識”的定義達成一致意見,但事實上,人類永遠不可能僅憑其理性而就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達成一致意見;2. 根據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研究,總的來講,科學知識并不是在同一個邏輯體系內不斷積累地進步的①;3. 愛因斯坦等著名科學家統一物理學的努力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4. 人類認知永遠是特定概念框架內的認知,人類知識永遠是具有主觀性的。所以,沒有什么統一的科學,只有多種多樣的科學。
反駁完全可知論:如果大自然并不只是物理實在的總和,也并不只是一個永恒不變的計算程序,如果大自然是具有創造性的,那么人類就休想憑語言和數學逐漸窮盡其奧秘,因為死數學把握不了活自然。人類的科學認知永遠只是在自然之內的對特定對象(從基本粒子到宇宙)的認知,大自然(不是科學家所研究的宇宙)本身永遠不可能成為科學認知的對象。無論科學如何進步,大自然本身永遠都隱藏著無窮的未為人知的奧秘。
結合以上對物理主義自然觀的反駁,我們必須再一次強調: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從自然,否則,會受到大自然的無情懲罰,因為大自然永遠握有懲罰人類之背道妄行的無上威力。
(三)關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包含一些“片面的真理”,其基本觀點是:每個人憑其理性而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因而擁有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如生命權、身體完整權、思想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自由、發財致富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等等。自由主義之錯不在申述了人的這些權利,而在相對忽視甚至否定了個人對不同層級共同體的依賴,過分強調了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其實,人的生存既具有個體性,又具有社會性,既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又具有脆弱性和依賴性。例如,個人有其相對獨立的個人利益,但個人只能通過參與社會的分工協作才能獲取個人利益;個人可以相對獨立于主流意識形態而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反思,但他的批判、反思能力不是天生的、自足的,而是在特定文化共同體中通過后天學習獲得的。個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存,而永遠只能作為特定社會的一個成員而生存,即他只能通過與他人交流、交換、合作、競爭甚至斗爭而生存。所以,個人在享有種種權利的同時,還負有種種不可推卸的責任,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參加工作、繳納賦稅等等責任。最關鍵的是,如果你希望他人和國家尊重你的權利,那你也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并遵守國家的法律。如今,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人的生存不僅依賴于社會,還依賴于地球生物圈,即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所說的“大地共同體”,亦即依賴于非人生物、土壤、水流、氣候等。長期以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不僅弱化了個人對人類共同體的責任,更遮蔽了人類對“大地共同體”的責任。
(四)關于反自然主義價值論
這里所說的價值論與下面將要剖析的價值觀不同。價值論指闡釋價值的來源和本質的哲學理論,而價值觀則指人們重視什么、輕視什么的思想傾向和偏好。反自然主義價值論指這樣一種價值哲學,它認定事實與價值是截然不同的,人們認知事實與體認價值的意識也是截然不同的。科學的任務是認知事實或揭示各種事實之間的必然關系,而宗教、哲學(至少其一部分,如倫理學和美學)、文學、藝術是闡明或體認價值的。事實是客觀的,而價值是主觀的,或說科學理論可以獲得客觀的檢驗,而述說價值的言說不可能獲得客觀的檢驗,簡言之,科學具有客觀性,而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沒有客觀性。所以,在倫理學中,你不能用事實判斷去支持價值“判斷”,換言之,科學與倫理學是沒有關系的,你不能用科學理論去為任何一個倫理學“命題”辯護,否則你就犯了“自然主義謬誤”。我們可把這一套價值哲學簡稱為事實—價值二分教條。
20世紀60年代以來,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著名分析哲學家對事實—價值二分教條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批判。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等生態哲學家則完全拋開了這一教條,直接用生態學、生物學、量子物理學等科學理論去為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和倫理學進行辯護。如果事實—價值二分教條是無可反駁的,則克里考特等生態哲學家的努力就是徒勞的。反駁事實—價值二分教條的論證思路如下:事實與價值是相互滲透的。凡被人所述說的東西,無論是科學的,還是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都已打上了主觀的烙印,即都已滲透了價值,沒有什么絕對客觀的對獨立于人的事實的描述,科學對事實的揭示和證明永遠都是在特定科學理論(有不可擺脫的主觀形式)框架之內的揭示和證明。換言之,沒有什么揭示了事實本身的絕對客觀的科學,科學所揭示的一切,都是科學家(共同體)從特定理論視角所揭示的東西,科學家只能在一定的理論框架內對特定判斷、定律和理論體系(也許是個公理體系)進行論證①。這樣一來,科學與倫理學在客觀性上就只有程度的區別,而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果說科學有客觀性,即科學家可給出信持特定定律的理由,那么倫理學也有客觀性,即倫理學家也可以給出必須遵守特定行為規則的理由。
事實—價值二分教條與物理主義自然觀以及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有內在的關聯。物理主義自然觀設定自然界有一些永恒不變的規律,人類理性可完全認識這些規律。可見,有一個邏輯上內在一致的絕對真理體系,科學就按這個體系的內在邏輯不斷進步,所以,其客觀性是絕對的客觀性。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學和科學史表明,人類無力建構這樣的絕對真理體系,任何科學都是滲透了價值的科學,也正因為它滲透了價值,它才有其價值,才是屬人的科學,才可能是以人為本的科學或對人類有益的科學。
正因為事實—價值二分教條是可廢除的,生態倫理學才是可論證的,能成立的。
(五)關于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
現代道德觀的基本思想是,道德關系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有人才有道德地位,一切非人事物都沒有道德地位;只有人才有內在價值,一切非人事物僅當可為人所利用、欣賞時才有價值,即它們只可能有工具價值,而不可能有內在價值。這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觀。據此立場,現代人把一切非人自然物都只當作資源或工具。對一個人,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未必應該做,例如,任何一個成年人都能殺人,但我們恰恰不應該殺人;任何一個精壯男人都能強奸幼女,但恰恰不應該強奸幼女。然而,對非人自然物,現代人認為只要你能夠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考慮道德上的應該不應該。例如,20世紀初我國就有人希望在長江三峽建大壩和電站,以便讓長江為我們發電,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們沒有能力這么做,就只好不做。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們有了這樣的能力,于是就做了。建三峽電站時人們會有種種顧慮,但絕沒有對于非人自然物(如河流、河流中的物種、未來庫區中的物種等)的道德顧慮。
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出現的動物倫理和環境倫理(包括生態倫理)對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提出了嚴正的挑戰。以湯姆·里根(Tom Regan)為代表的“動物權利論”著力論證,所有的高等動物,如馬、牛、羊、豬、狗、貓、猩猩、猴子、海豚等,都是生命主體,從而都具有主體性和內在價值,并非只有人才有內在價值。根據“動物權利論”,我們必須承認高等動物具有道德地位,它們應享用生命權、身體完整權和行動自由。以保羅·泰勒(Paul Taylor)為代表的生物中心論認為,一切生物都有其固有價值(inherent worth),都有其自身的福利(well-being),且它們的福利應該被理解為獨立于人類福利的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4]。由利奧波德提出的且經克里考特所周密論證的大地倫理(Land Ethics)則著力論證,人與大地(即地球生物圈)之間的關系是倫理關系,大地是由非人生物(包括一切動物、植物、微生物)、人、土壤、水體、氣候等構成的一個共同體,人是這個共同體中的普通一員,人有責任維護大地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的論證表明,在人類與非人物種之間沒有人類中心主義者所說的那種天壤之別,如前者有理性,而后者沒有;前者有內在價值,而后者沒有,等等。但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自身有一些難以克服的理論困難和實踐困難。在下一節,我們將較詳細地論證,只有大地倫理才是既具有理論徹底性又具有實踐可行性的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
(六)關于物質主義價值觀
現代社會貌似一個價值多元化、信仰多樣化的社會,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信仰伊斯蘭教,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無神論或唯物主義,等等。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信仰自由。但能堅持純正信仰的人很少,很多信徒都受到了金錢的腐蝕。有些宗教,或某種宗教中的某些教派(如佛教中的少林寺),也開始走商業化的道路。而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則公開宣稱,創造財富就是榮耀上帝,于是它認可了物質主義。哲學原本可以指引人們追求精神超越,但今日之哲學,或已淪為物質主義哲學,或已成為與現實生活隔絕的所謂純粹學術(極少數人玩的“象牙塔”中的語言游戲)。在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市場經濟過分擴張的國家,“萬物皆商品化”(華勒斯坦語),金錢的魔力被過分凸顯。于是,價值多元化和信仰多樣化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各種信仰都對一種信仰——物質主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協,各種信徒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物質主義。換言之,最有影響力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是物質主義②。
今天,多數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幸福就在于創造物質財富、擁有物質財富、消費物質財富,即人生的意義、價值和幸福就在于參加創造物質財富的各種工作,例如能加入馬云或王石的團隊;就在于個人收入的穩步增長,從而能由騎自行車換為開車,由開QQ換為開“豐田”,等等;就在于物質消費品味和檔次的不斷提高。這就是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與這種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相應的社會發展觀就是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或GDP至上觀念。經濟主義認為,經濟增長就是唯一的可切實追求的公共的善(common good),即多數人都愿意為之奮斗的公共目標;經濟增長能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包括科技進步、教育普及和提高、社會穩定、文化繁榮等;提高人們“幸福指數”的最現實、最有效的途徑就是不斷改變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如建越來越多的工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地鐵,建設越來越便捷的通訊系統,生產越來越多的家用電器和汽車,等等。
物質主義的盛行不僅與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萬物皆商品化”的社會潮流有關,而且與物理主義自然觀和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密切相關。根據任何一種激勵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學都可以發現物質主義的淺薄和荒謬。但在以物理主義和獨斷理性主義為根本信念的現代性思想體系內,物質主義就不但不顯得淺薄、荒謬,而且顯得天經地義地正確。
既然萬物都是物理的,那么也可以說萬物都是物質的。人和人的思維以及人所創造的文化都可以歸結為物質。只有物質才是真實的,非物質的一切都是虛幻的,充其量也只是隨附的。不僅鬼神是虛幻的,純粹的愛情,崇高的精神和審美的崇高,儒家、道家和佛學所講的極高人生境界也都是虛幻的。所以,只有像比爾·蓋茨、喬布斯、王石、馬云等為人類做出的貢獻才是真實的、可嘉的,因為他們為創造物質財富做出了巨大貢獻,那是真實的貢獻。而像顏回、大衛·梭羅一類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為他們沒有為人類做出真實的貢獻。
獨斷理性主義則告訴人們,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質財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義、價值和幸福是最切實可行的,即最為確定,最具有現實性。何謂崇高?何謂神圣?不同的宗教和哲學對崇高、神圣的理解是不同的,而儒家、道家和佛學所講的極高人生境界則是語焉不詳、虛無縹緲的。只有物質主義所定義的幸福才是可以客觀衡量的,才是人人都能夠追求的。人們可以通過合作與競爭而追求共同但有程度差別的幸福,即通過各自的努力——如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廣告創新——而共同促進經濟增長(即財富增長),從而共享經濟增長的果實和財富增長的盛宴。當生態主義者說,物質主義和資本主義所激勵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導致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時,獨斷理性主義者會說,你們不要危言聳聽,所謂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只不過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暫時困難,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困難都將被克服。于是,獨斷理性主義總是鼓勵人們:不要懷疑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不要懷疑“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不要懷疑人類征服自然的偉大力量,按照現代性的藍圖不斷地進行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人類將越來越自由、自主、幸福。
物理主義自然觀和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是現代性思想的基石,而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是現代性思想的要害,前者為后者提供了“周密”的辯護。
如果物理主義自然觀和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都是荒謬的,我們就不僅該質疑資本主義制度,更應該質疑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如果現代性思想大廈坍塌了,則物質主義的淺薄和荒謬立顯。如前所述,物理主義自然觀和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都是站不住腳的,可見,現代性思想大廈不是建立在堅固的巖石上,而是建立在現代迷信的沙灘上。
突破了現代性思想的藩籬,理解了生態學的基本法則,我們就能立即明白,“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激勵人們“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現代工業文明是不可持續的。
巴里·康芒納(Barry Commoner)在《封閉的循環——自然、人和技術》一書中概括了生態學的四法則。第一條法則是,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相關。第二條法則是,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第三條法則是,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條法則是:沒有免費的午餐[5]25-37。
記住第一條法則,我們就明白,人類對生態系統某個部分的過分干預,即超過生態系統之承載限度的干預,會導致生態系統的崩潰。人在生態系統之中,而不在生態系統之外,更不在生態系統之上,人類生存是依賴于生態系統的健康的,是依賴于各種非人生物的生存的。如果整個地球生物圈崩潰了,人類便將陷入滅頂之災。
第二條法則不過就是物理學中物質不滅定律的另一種表述形式。謹記此法則,就能明白,我們每天拋棄的垃圾,燒掉的汽油、煤等,都并非徹底湮滅了,而是積儲在某個地方。例如,我們正沉溺其中的私家車消費就對2013年以來的“霧霾”天氣有所“貢獻”。如今,我們只好一邊享受駕車的舒適,一邊忍受“霧霾”的傷害。
康芒納自己也明白,他所提出的第三條法則會遭到很多人的反駁。事實上,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否認這一法則。這一法則認為,“任何在自然系統中主要是因人為而引起的變化,對那個系統都可能是有害的(中譯本加的是著重號)。”康芒納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他所提出的這一法則:你有一塊精致的手表,如果你打開手表機芯,而在部件緊密處硬插進一截鉛筆芯,那么十有八九你會毀了這塊手表。對于手表來講,我們可以說,“手表匠懂得的是最好的。”對于大自然,我們則須謹記:大自然所懂得的是最好的[5]32-33。謹記此法則,我們在改造環境、制造物品、干預自然過程時就會小心謹慎。我們不要認為,人類有了科技就無所不能,而忘了普利高津的告誡:大自然是具有創造性的。令人擔憂的是,至今仍有許多人拒不承認大自然是具有創造性的,從而仍主張用征服性的科技去征服自然。
第四條法則告訴我們,我們的每一次獲得都必須付出代價。現代性指出的一個追求幸福的基本方向就是,不斷通過征服性科技的創新,制造越來越多的機器,以把人們從笨重、艱苦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如今,機器不僅免除了早期礦工們艱苦、危險的勞作,免除了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而且免除了我們用兩腿走路的麻煩。但這一切是有代價的,我們在享受機器的代勞和服務的同時,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礦物能源,從而每天都在污染著環境,破壞著生態健康。
根據生態學四法則,我們很容易明白,“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是徹頭徹尾的“背道妄行”。激勵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的現代工業文明是不可持續的,超越現代工業文明,建設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
清理了現代性思想的根本錯誤,分析了現代性思想對人類價值追求的致命誤導③,我們才有可能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
三、生態倫理和生態哲學
直接思考環境問題的哲學通常被稱之為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如美國著名環境哲學家哈格羅夫(Eugene Hargrove)所說的,環境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被命名錯了,它更為恰當的名字是環境哲學,因為“它包含了哲學領域中的大多數傳統學科的內容,包括美學、形而上學、認識論、科學哲學以及社會與政治哲學的內容。”[6]
如今,環境哲學流派繁多。其中有些流派并不訴諸生態學,它們甚至有意識地與生態學保持距離,有些流派則自覺地訴諸生態學。我們可稱后一類,即自覺訴諸生態學的環境哲學,為生態哲學。我們認為,整體主義、自然主義的生態哲學是既具有理論深刻性,又具有實踐可行性的生態哲學,是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礎(或理論依據)。其基本觀點如下:
(一)生成論自然觀
在20世紀80年代,普利高津說:“本世紀初,物理學似乎接近于把物質的基本結構歸結為幾種穩定的‘基本粒子,例如電子和質子。可是現在,我們卻和這種簡單描述大相徑庭。無論理論物理學的未來是怎樣的,‘基本粒子看來是如此之復雜,以至關于‘微觀世界簡單性的格言再也不能適用了。”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天體物理學中同樣得到了印證。“盡管西方天文學的奠基者強調天體運動的規則性和永恒性,但如今這種界定至多只適用于行星運動一類的極少數情況。無論我們往哪兒看,我們所發現的都是多樣性和不斷增加的復雜性,而不是穩定性與和諧性。”[7]1-2
在人類認知歷程中,總有一種以簡馭繁或以不變應萬變的追求,總有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家,希望發現可說明甚至預測一切紛繁復雜現象(多或雜)的永恒不變的規律(一或簡)。在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強有力的傳統,該傳統認定,世界的存在(being)或本質是永恒不變的,變動不居的只是為人類感官所接受的現象。只有永恒不變的存在才是真實的、重要的,是哲學和科學所該著力把握的東西,而變動不居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次要的,是需要用永恒不變的東西(真理或規律)去整理和統御的。普利高津稱這種世界觀為“靜止的世界觀”(static view of the world)[7]Preface,P.vi,并通過自己畢生的科學研究和哲學思考,對這一思想傳統提出嚴正挑戰。
普利高津認為,20世紀的科學仍然在堅持著靜止的世界觀,這就體現為物理學對不變性的極端重視,具有不變性的規律是與時間無關的,例如,無論是在經典力學中,還是在量子力學中,力學方程對于時間反演t→-t是不變的。按照這種觀點,將來和過去沒有什么區別,構成我們宇宙的原子或粒子所依循的世界線(the world lines),即軌道,是一致地通達過去和未來的[7]Preface,P.vi。也就是說,世界的終極定律(溫伯格的概念)是永恒不變的。將來就包含在過去之中,于是,現在的仔細研究能夠揭開未來的面紗。即科學能準確地預測未來。這就是“經典科學的神話”[7]Preface,P.124。但普利高津認為,時間是世界萬物乃至世界本身的一個內在維度,可逆過程只是世界中的某些特殊過程,更多的自然過程是不可逆過程。換言之,萬物都處于不斷的生成(becoming)之中,萬物皆隨時間而變化,或說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這就要求我們擯棄決定論,承認“將來并沒有包括在過去之中。即便在物理學中,我們也只能像社會學那樣對各種可能‘事態進行預測。”[7]Preface,P.x vii因為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現實性更加豐富。
(二)謙遜理性主義知識論
理性就是用語言,特別是書寫語言(包括數學),進行思維的能力。迄今為止,地球上只有人類這一物種具有這種能力。也正因為人具有這種能力,他才創造了文化或文明。但我們須對人類理性有個恰當的認識。獨斷理性主義的致命錯誤就在過分夸大了人類理性的力量,認為人類理性可確保真理在一個內在一致的體系內不斷積累、擴展,以至可達到或無限逼近對自然奧秘(永恒真理或存在本身)的完全把握。在上一節我們已大致反駁了獨斷理性主義。這里須對可知論問題做一簡要論述。
長期以來,正統哲學(涵蓋獨斷理性主義)堅決拒斥不可知論,堅持世界可知論。但完全可知論只是現代人的獨斷信念而已。
如今,我們認為,理性就典型地體現為科學理性,即科學方法的運用。科學方法典型地體現為假說—演繹法(抑或“最佳說明推理”)。科學方法設定,來自觀察和實驗的數據或證據是最可靠的,一切科學定理(假說)都必須獲得來自觀察和實驗的數據或證據的支持。但科學定理是一般的或普遍的,而觀察或實驗數據是個別的或具體的。從邏輯的角度看,由個別推出一般的推理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可見,即使觀察或實驗數據絕對可靠,也無法保證科學定理的絕對可靠,況且觀察和實驗是依賴于理論的,即“觀察滲透理論”。這就決定了科學定律只能是猜想性的,而不可能是絕對真的。
經典科學方法論設定,科學家對研究對象的觀察和干預活動(包括用復雜實驗裝置對物質的處理)不會影響觀察或實驗數據的客觀性和精確性。但量子物理學告訴我們,測量過程是有局限的,因為測量過程不能撇開觀察(測量)者的作用。普利高津說,在量子力學中觀察者的作用(即對被觀察者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無論將來如何,這種作用都是實質性的。所以,經典物理學中的那種天真的實在論,即設定物質屬性獨立于實驗裝置而存在的觀點必須被糾正[7]215。這說明我們永遠只能在自然過程之中認知自然過程,那種設定主體可完全站在客體之外而絕對客觀地認知客體的觀點只是一種理想的假設。認為作為存在之大全或萬物之根源的自然(抑或永恒不變的存在)也是科學認知的對象(客體),并認為科學認知的最終目標就是窮盡自然的一切奧秘,更是獨斷理性主義的僭妄。
科學之應用的有效性,特別是長期應用的有效性,使人們誤以為科學定律都是客觀真理,甚至誤以為科學正日益逼近對自然奧秘的完全把握。如果能清醒地認識到科學理性的局限性,并體認普利高津所說的大自然的創造性,我們就容易明白,無論科學如何進步,科學之所知相對于大自然所隱藏的奧秘都只是滄海一粟。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如果科學進步正日益逼近對自然奧秘(即終極定律或永恒不變的規律)的完全把握,我們就根本沒有必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這是不是意味著墮入了不可知論?回答這個問題,要看我們追求什么樣的認知目標。若認為人類的認知目標就是古代西方哲學和經典科學的認知目標——世界之永恒不變的存在(Being)或規律,那么人類理性就根本沒有能力達到這一目標,因為世界或許根本就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東西。如果我們追求的認知目標是服務于人類價值追求的知識,那么就可以明確回答,人類理性可以發現確保人類生活幸福的知識,于是我們就不會墮入不可知論。古人已發現了很多服務于人類追求幸福的知識,這類知識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如天文、地理和醫藥),也包括如何修身的知識。如果我們認為,人類認知的本分在于獲得必須的物質生活資料和無限追求精神豐富或無限提升人生境界的知識,則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知識。如果你認為,人類認知的終極目標就是獲得絕對客觀的真理和囊括一切世界奧秘的真理大全,則答案只能是: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認為人類理性只能發現用以指導有意義的人生的真理以及用以指導有節制地改造環境、制造物品、創造財富的知識,而不能發現無限逼近自然之全部奧秘的真理大全,這就是謙遜理性主義。謙遜理性主義傾向于把科學看作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對話,更確切地說,把科學看作人類傾聽自然之“言說”的一種方式。在20世紀末普利高津說:“經典物理學的宇宙是個給定的、封閉的宇宙,而新物理學的宇宙是個對漲落和創新開放的宇宙。對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經典物理學的奠基者們來講,科學力圖超越表象世界而達到至高理性的超時間的(即永恒不變的)世界。但實在的形式(form of reality)可能更微妙,既涉及定律,也涉及博弈(games);既涉及時間,也涉及永恒。我們這個世紀是個探究的世紀:即藝術、音樂、文學和科學都出現了新形式的世紀。如今已到了世紀末,至今我們仍不知道人類歷史的新篇章將走向何方,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它會產生人與自然的新的對話。”[7]215這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改變哲學層面的信仰體系,而且需要改變科學層面的知識體系。
謙遜理性主義知識論既鼓勵人們培養自己的謙遜美德,也要求人類集體(作為一個類或物種)保持其謙遜態度。個人需要謙遜美德,就因為任何一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便你是最聰明、最卓越的人,你也不可能是全智全能的。故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但人又很容易自高自大,一旦自高自大就容易犯錯誤。所以,個人需要謙遜美德。人類需要保持謙遜的態度,就因為70億個有限的個人無論以何種方式組織(國家、跨國公司、國際聯盟、國際科學家聯盟)起來,仍然是有限的存在形式,而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
(三)共同體主義政治哲學
人的生存既具有個體性,也具有社會性。共同體是由個人構成的,但個人又只能是共同體中的個人。正因為人的生存具有不可消解的個體性,所以個人利益難以與社會利益徹底地協調起來。也正因為如此,永遠都會有人對他人施暴行騙,也永遠都無法排除某些人打著維護社會利益的旗號剝削、壓迫多數人的可能。所以,不能忽視人權保護,不能徹底廢除財產所有權和市場經濟制度,不能再回到計劃經濟時期。但個人又永遠是共同體中的個人,個人在行使自己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和社會公共規則。就保護環境、節能減排和建設生態文明而言,我們既要訴諸污染權交易等手段去激勵人們(特別是企業家)以追求私利的方式保護環境、節能減排,也要訴諸政治和道德,以喚醒人們維護環境正義乃至生態正義④的良知。
在政治、經濟建設方面,生態文明必須繼承現代工業文明的積極成果——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的合理方面。但生態文明的市場經濟必須受生態規律的約束,而不是一任“資本邏輯”的制導,生態文明的民主法治必須通過公民價值觀的深刻轉變而有力促進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且明確規定,節能減排、保護環境是每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四)自然主義價值論
人在自然之中,人既不可能游離于自然之外,也不可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人類所追求、珍惜、重視的一切都可被稱之為價值。價值源自主體的評價、追求、使用等主體性活動。但人的主體性也就是一種自然存在者的主體性。如今,我們已不能認為只有人才有主體性,如湯姆·里根所著力論證的,非人動物也有主體性。當代西方哲學家已不太使用“主體”(subject)和“主體性”(subjectivity),而較多地使用“能動者”(agent)和“能動性”(agency)。不同的事物,如不同的動物,具有不同水平的能動性。在地球生物圈諸物種中,人類的能動性水平無疑是最高的。價值源自能動者的能動性,源自能動者的傾向性活動。人類追求的價值則源自人的意向性活動(包括向往、思戀、評價、欣賞、使用等)。我們向往桂林山水,桂林山水就對我們有價值;我們思戀故鄉,故鄉就對我們有價值;我們評價《紅樓夢》的藝術水平和審美境界,《紅樓夢》就對我們有價值;我們欣賞玉石的潤澤質感,玉石就對我們有價值;我們使用石油,石油就對我們有價值。
在現代性的概念框架中或文化氛圍中,我們還把價值區分為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和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一個事物因其所是而具有的價值就是它的內在價值,一個事物相對于其使用者而具有的有用性就是它對于使用者的工具價值。我們認為每個人僅因為是人就具有價值(因此每個人都應受到他人的起碼的尊重),這就是人的內在價值;而石油的有用性就是它對于人的工具價值。現代性理論認為,只有人才有內在價值,而非人事物的價值都是人所賦予的。這種觀點已受到多方質疑和挑戰。
在特定語境中,價值與事實是有區別的,評價與描述也是有區別的。如,“2014年x月x日北京地區的天氣是重度霧霾天氣”這句話是對一個事實的描述,而“霧霾天氣真是太糟糕了!”這句話就是對霧霾天氣的評價。但我們不能認為,價值與事實是沒有關系的,不能認為,用事實判斷去支持價值判斷是注定無效的,也不能認為倫理學與科學是沒有關系的。普特南、克里考特等著名哲學家已充分闡述了事實與價值、科學與倫理學的內在關聯[8],在此不贅。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科學所追求的真理總是滲透價值的,追求“終極理論”的科學也恰恰體現了一種價值追求——試圖掌握“統轄星球、石頭乃至萬物的規則之書”,從而追求人類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換言之,人所追求的真理永遠是屬人的真理。如果人類理性根本掌握不了“統轄星球、石頭乃至萬物的規則之書”,如果人類不可能按所謂科學之內在邏輯無限逼近對自然奧秘的完全把握,那么人類就該有對科學之價值追求和價值導向的明確反省。試圖掌握“統轄星球、石頭乃至萬物的規則之書”的科學似乎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科學,而是服務于政治霸權、軍事霸權和億萬富翁們健康長壽甚至長生不老奢望的科學。真正以人為本的科學應是盡力維護地球生態健康、保障人類安全(包括食品安全、醫藥安全和生態安全)的科學。
現代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物質主義價值導向,但它卻打著科學的旗號,掩飾了它的價值導向。“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原本只是對多數人行為傾向的統計性描述,卻被現代經濟學設定為不可改變的事實或永恒不變的真理(公理)。而現代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又深受經濟學的影響,于是現代工業文明激勵人們永無休止的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如萬本太所言:“工業文明的核心價值是功利和自我,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9]正因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被認為是一條關于人性的真理,所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地正確的。可見,現代多數人信仰物質主義與經濟學(一種科學)的價值導向密切相關。人生追求本有多種可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傾向并不是人的不變的本性,而是可以通過修身、學習和社會實踐而加以克服的傾向。人生的意義和幸福恰在于克服這種“氣質之性”而凸顯人的“天命之性”,即克服其自私性而居仁由義,進而不斷提高自己的境界。
總之,在價值論上認識到事實與價值的相互滲透,厘清科學(包括經濟學)的價值導向,對于生態哲學的體系建構至關重要。
(五)非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
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都對現代主流道德觀——人類中心主義——進行了有力批判。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都表明,人與非人動植物之間的區別沒有人類中心主義所設定的那么大。例如,非人高等動物也有意識,也能使用簡單的工具,也能改造環境(如,鳥兒能壘窩,老鼠能打洞,等等)。簡言之,非人高等動物也具有能動性,盡管其能動性遠不及人類的能動性。
但能不能像動物權利論說的那樣,認為具有特定能動性水平的非人動物也和人一樣具有生命權、身體完整權和行動自由權呢?如果我們決定像尊重人的權利一樣尊重一切非人動物(包括所有家畜、家禽)的權利,那就意味著我們不但不能利用家畜、家禽,而且必須照顧它們(保障它們的生命權、身體完整權),讓它們自由活動。它們不能對人類履行道德義務,但享受人類對它們的道德保護。在老齡化社會人們尚且擔心青壯年擔負不起對眾多老人的照顧,那么人類有能力對幾百億個動物個體履行其單向的道德義務嗎?道德上的“應該”蘊含行動上的“能夠”。對于人類實際上做不到的事情說“應該”是沒有意義的。人類無法在無回報的條件下履行對幾百億個動物個體的道德義務。所以,動物權利論不具有可行性。個體主義的生物中心論面臨同樣的困境。
真正具有理論徹底性和實踐可行性的生態倫理是源自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且經克里考特等哲學家精心論證的自然主義、整體主義生態倫理。說這種生態倫理是自然主義的,就因為它擯棄了事實-價值二分教條,自覺地謀求倫理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而力圖把生態倫理奠定在自然科學(包括現代物理學、生物學和生態學)成果的基礎上。其基本觀點如下:
1. 生態系統乃至地球生物圈是一個共同體,人類在這個共同體之中,而不在這個共同體之外,更不在這個共同體之上。人類的生存和繁榮依賴于非人生物的生存和繁茂,依賴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具有生物多樣性)。人應該學會“像山一樣思考”,即學會用生態學的方法看待人與非人事物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僅根據是否對人類有用判定非人自然物之有用(有害)或無用(無害)[10]。
2. 人在地球生物圈中享有比其他生物更高的權利,但同時負有更高的責任。不必像動物權利論者所要求的那樣,絕對廢除對非人動物的利用,尊重每一個動物的權利,但人類必須擔負保護生態健康的特殊責任(保護物種,而不是保護個體)。人類不能一任其物質貪欲的膨脹,肆無忌憚地干預自然過程。只有在正常時空閾限內的對生態共同體的干預才是正當的,否則是錯的(克里考特),或說在地球生物圈承載限度內的干預才是正當的,超過地球生物圈承載限度的干預就是不正當的。用利奧波德的話說就是:一件事如果有利于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和美麗就是正當的,反之是不正當的。
無論是個人行動還是集體行動,都應該遵循生態倫理的基本規則。遵循生態倫理的基本規則就是遵循生態學的基本法則(如前所述,當然還可以細化)。個人行動遵循生態倫理的基本規則,就意味著恪守綠色消費原則: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健康的消費才是正當的,反之是不正當的。就此而言,生態倫理要求人人都保持物質消費的節儉和自律,既反對大量排放的奢侈消費,又反對不顧生態良知的獵奇性消費,如以吃珍稀動物為榮。集體行動遵循生態倫理的基本規則,就意味著我們的生產和建設嚴格遵循生態學法則,如所有工廠的生產都要使用清潔能源,采用清潔生產技術,盡可能節能減排,并盡可能循環利用各種資源。當然,完全做到這些還需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就是生態文明的建設目標。
(六)超越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
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文化動物,是追求無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必須穿衣、吃飯才能活著,但活著并非僅為了穿衣、吃飯;人必須消費才能活著,但活著并非僅為了消費;人必須創造物質財富才能活著,但活著并非僅為了創造物質財富。人活著是為了創造價值和文化,但不可把價值僅理解為商品價值,也不可把文化僅理解為現代物質主義文化。人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有意義或價值,這里的“意義”,抑或“價值”,只能是在特定文化氛圍中被人們所承認和體認的意義或價值。一個人若覺得自己活得沒有意義或價值,他極有可能去自殺。
一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與其認定的最高人生目標或終極關懷密切相關,與其信仰密切相關。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終極關懷是對上帝的信仰和對自己靈魂的拯救;一個佛教徒的終極關懷是成佛(最高的覺悟);一個真正的儒者的終極關懷是成為圣人(達到天人合一境界);一個道教徒的終極關懷是成仙;一個拜金主義者的終極關懷就是擁有盡可能多的金錢;一個物質主義者的終極關懷就是創造物質財富、擁有物質財富、消費物質財富,……每個人對自己所認定的最高目標(價值)的追求都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說人是追求無限的有限存在者,就是這個意思。對無限的追求就是對人生意義、價值和幸福的追求。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拯救靈魂的努力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真正的儒者對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物質主義者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同樣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換言之,不同的信仰指引(決定)著不同的意義追求(或無限追求)。信仰基督教的人們無限追求“上帝之城”,信仰儒學的人們無限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即圣人境界),信仰佛學的人們無限追求根本的覺悟(即成佛),而信仰物質主義的人們無限追求物質財富。
從任何一種激勵精神超越的哲學和宗教的視角看,物質主義都是一種粗俗、荒謬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在現代性的框架內它卻被凸顯為唯一具有真理性的信仰體系,使眾多人誤認為人生的意義、價值和幸福就在創造、擁有、消費物質財富。這是對人類無限追求的致命誤導。
西方啟蒙學者力圖證明,基督教蒙騙了那些未經啟蒙的人們。如今,生態學和生態哲學則表明,現代性致命地誤導了經過“啟蒙”的人們。如果說某些宗教所提供的信仰是錯誤的,那么現代性所提供的信仰——物質主義——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因為它激勵了多數人的物質貪婪,把原該指向精神領域的無限(意義)追求誤導于物質領域。事實上,人只能在思想或精神領域體認無限,而不可能在物質上達到無限。近3個世紀以來,由于人們貪得無厭地追求物質財富,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生態學表明:大自然允許人類以無限追求精神價值的方式追求無限,但不允許以無限貪求物質財富的方式追求無限。
我們也可以把人生追求歸結為對人生幸福的追求。幸福是在生存安全前提下的主觀感受和生存體驗。擁有必需的物質生活資料是一個人生活幸福的客觀條件,而心態和境界則是一個人生活幸福的主觀條件或主體條件。一個人必需的物質財富是有限的⑤,而改善主體條件是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現代工業文明的根本弊端就是誤導人類以無限追求物質財富的方式追求幸福生活,而忽視了最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徑:不斷調適個人心態并不斷提高人生境界。換言之,現代工業文明一味鼓勵人們“向外用力”,而基本不鼓勵人們“向內用力”(梁漱溟語)。
向內用力就是改善自己的心態,養成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境界,增強自己的智慧。簡言之,改變自我,進而通過改善自我而改善社會,重在改善自我。向內用力的根本途徑和基本工夫是修身。而向外用力就是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和物質生活條件,如掙更多的錢,買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車,建越來越好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建越來越好的能源系統、通訊系統等。簡言之,改變外部生活條件,改變世界,征服自然。向外用力的根本途徑和基本要求是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廣告創新等等。也可以說,向內用力是追求自我完善,而向外用力是追求身外之物。一個人只有心態平和且有較高境界時才能常有幸福感,反之,一個人若貪婪、好爭,則很難有什么幸福感。所以,智慧的人生是向內用力為主、向外用力為輔的人生。可持續的文明更激勵人們向內用力,而一味激勵人們向外用力的文明,必然是不可持續的。現代工業文明正是一味激勵人們向外用力以無限追求身外之物的文明。它一味激勵人們進行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廣告創新等等,但根本不鼓勵人們修身。它過分倚重于貪婪、好爭的人們,而傾向于把心態平和且追求人生境界的人們(如顏回、大衛·梭羅)擠在社會的邊緣。它激勵人們永無休止地為創造財富、占有財富而激烈競爭,從而只能在生態危機中越陷越深。
為了建設生態文明,我們必須建構超越物質主義的生態文化。生態文化即蘊含生態價值觀的哲學、宗教、科學、文學和藝術。生態文化將呼吁人們適度追求物質財富,將激勵人們無限追求非物質價值,即以無限追求德行和境界的方式追求無限,將只要求人們適度地向外用力,而更鼓勵人們向內用力。
如果說現代性理論為現代工業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周密”的辯護,那么生態哲學可以為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進行周密的論證。有了生成論自然觀和謙遜理性主義知識論,我們才能明白,為什么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有了共同體主義政治哲學、自然主義價值論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我們才能明白,人類社會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經濟系統是地球生態系統的子系統,人類經濟活動所伴有的排放量必須限制在生態系統的承載限度內,人類是“大地共同體”(即地球生物圈)的一個成員,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依賴于大地共同體的整體健康,依賴于非人生物的生存與繁茂,人類文明必須與地球生物圈協同共生。有了超越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我們會發現,人類幸福根本不依賴于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卻依賴于人的德行養成和境界提升,我們會明白,物質財富不增長了,人類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甚至可以比物質財富增長時生活得更幸福。
四、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
由以上闡述的生態哲學,加上生態學和環境科學,我們可得出結論:現代工業文明是不可持續的,建設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態文明是繼承了以往文明(包括原始文明、農牧文明和工業文明)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的更高級的文明,其大致愿景如下:
清潔能源逐漸取代了如今的礦物能源,清潔生產技術、低碳技術和生態技術得到了充分發展,低碳企業和生態企業越來越多,物質生產逐漸走向清潔化、生態化的穩態。非物質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如信息產業、文化產業、旅游業等得到了充分發展。人們的消費也逐漸理性化、生態化、綠化,即人們不在物質消費上互相攀比,而盡力降低個人生活的排放量,人們更傾向于非物質消費,如較多地消費信息產品、文化產品等等。
清潔生產技術、生態技術、低碳技術、環保技術大發展,直至成為主導性技術。
碳交易和污染權交易等市場良性發育,企業能自覺地擔負其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循環經濟漸成規模,唯GDP至上觀念淡出,政界不再以DGP論英雄,相反,保護環境成了各級地方官員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信仰科技萬能論和物質主義的人們趨于減少,生態學知識日漸普及,相信生態學和生態哲學的人們趨于增加,以至成為多數。
思想觀念的改變是根本。僅當多數人相信生態學和生態哲學且擯棄了科技萬能論和物質主義時,清潔生產技術、生態技術、低碳技術、環保技術才能充分發展進而成為主導性技術,物質生產才會走向生態化的穩態,非物質經濟才能大發展,綠色消費和非物質消費才會蔚然成風,唯GDP至上觀念才會淡出政治舞臺。
當生態文明漸成大勢時,我們才能一邊享受文化豐富的幸福,一邊享受碧水藍天。
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事做起。對于每個個人來講,超越物質主義且擯棄科技萬能論是思想起點。不能超越物質主義,就不可能割舍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迷戀。迷戀“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人不可能誠心建設生態文明。認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與建設生態文明不矛盾的人們必然信持科技萬能論,即相信進一步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將使我們能一如既往地“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而不會再有“大量排放”。然而,科技萬能論只是現代工業文明長期灌輸給人們的神話。節約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度電,隨手關燈,隨手關水龍頭,盡可能少用一次性用品,盡可能綠色出行,是建設生態文明的行動起點。人人行動起來,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就能成為現實。
注釋:
①參見庫恩著《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或有人說,物質主義不是信仰,只有堅信超越的終極實在(如上帝)之存在的信念才屬于信仰。但我們認為,這是對信仰的過于狹窄的界定。人們堅定不移地用以指導其人生的信念體系就是其信仰。
③筆者無意于說現代性全是錯誤,它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當然只能是歷史性的成果,言其成果的文獻已汗牛充棟,無須在此贅述。
④“環境正義”與“生態正義”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只考慮環保責任和環境資源(如清潔水、清潔空氣等)的人際(包括代際)公平分配,而后者還考慮維護非人物種的利益。
⑤一個人只能吃那么多東西,只能穿那么多衣服,只能住那么大面積。如果一個人以吃到最珍貴、稀有的食物(如熊掌、魚翅、果子貍、穿山甲、刀魚等)為榮,以穿戴最珍貴、稀有的服飾(如用藏羚羊絨織的披肩)為榮,那么她/他就不僅是粗鄙的,而且是嚴重破壞生態的。
參考文獻:
[1]美麗中國不是夢——中國生態文明論壇(杭州)主題對話(節選)[J].中國生態文明,2014,1(2):23.
[2]Ilya Prigogine,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M].The Free Press,1997.
[3]Steven Weinberg,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M].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New York,1993:242.
[4]Paul W.Taylor,The Ethics of Respect for Nature,in David Schmidtz and Elizabeth Willott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What really Matters,What really Work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83-84.
[5]巴里·康芒納.封閉的循環——自然、人和技術[M].侯文蕙,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尤金·哈格羅夫.環境倫理學基礎[M].楊通進,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2-3.
[7]ILYA PRIGOGINE,FROM BEING TO BECOMING: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M].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80.
[8]J.Baird Callicott,Thinking Like a Planet:The Land Ethic and the Earth Ethic[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9]萬本太.新型文明時代的呼喚——生態文明斷想[J].中國生態文明,2014,3(2):14.
[10]阿爾多·李奧帕德.沙郡年記[M].李真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154-159.
責任編輯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