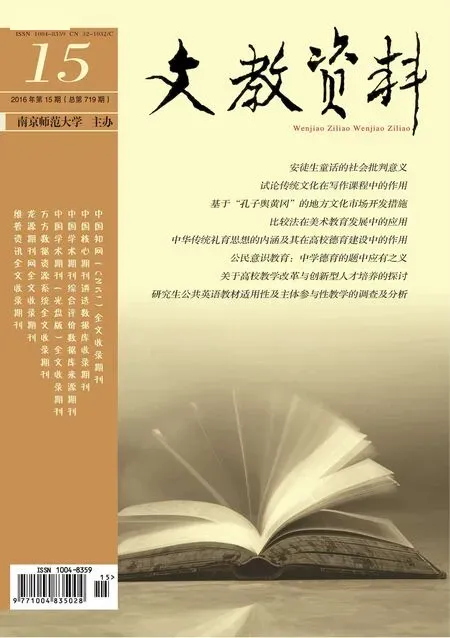試論傳統文化在寫作課程中的作用
吳丹鳳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試論傳統文化在寫作課程中的作用
吳丹鳳
(肇慶學院文學院,廣東肇慶526061)
自啟蒙運動以來,高校課程設置日趨功利,將傳統文化的理念引入寫作課程中綜合思考對課程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人”的完善是寫作課程的出發點和終點,認為教師應以“格物致知”的眼光引導學生認識世界,以“物我兩忘”的觀點提高學生的寫作思維與技巧,以“有教無類”的信念打破學生的既定思維,探討完善寫作課程的可能性。
傳統文化寫作課程作用
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一直指導著高校課程教育的展開。然而不幸的是,“那個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從神話鐐銬下解放出來的啟蒙運動,由于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而走到了它的反面,成為新的神話。啟蒙運動走向自殺的道路,而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著巨大的不幸”[1]。寫作課程毫無例外地被理性拖著走向了它的反面,著重強調它的工具性。所以,想要重新審視寫作課程時,必須先明確的是人在寫作課程中的位置。那就是設置寫作課程到底是為了人的完善,還是為了提高人對寫作這一技能的控制。這是一個“體”與“用”的根本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將傳統文化的理念引入寫作課程中綜合思考。
一、在傳統文化中重新明確寫作課程的初衷
《尚書·舜典·堯典》言:“詩言志,歌永言。”[2]寫作是人有所感或有表達的需要,而將所想語言符號化的過程。所以,寫作無論是作為一種行為還是一門課程都是為了使生命的呈現更自如,幫助人們更好地表達自己、完成自己、審視自己作為人的自覺歷程。單純從寫作課程出現的初衷來看,啟蒙是首要的,工具性是次要的。孟子曾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意思是,學問之道沒有別的什么,不過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來罷了。寫作所為人表達自我的重要方式,正需要幫助寫作者思考及與世界互動,促進人的自我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寫作是能動的,既是人大腦智力的表現又促進人的能力圓滿。寫作課程中人的存在與寫作這一行為應融為一體。明確了寫作課程展開的初衷后,我們把人的完善作為寫作課程開展的出發點和最終的目的,摒棄“追逐、適應、認識、掌握這個世界”這種課程功利理念,追求“適應、認識、掌握、發展這個世界”的漸進理念[4]。
二、以“格物致知”的眼光引導學生重新認識世界
古人常說“格物致知”,物必須是真實的萬物,而不是被扭曲與概念化了的萬物。因此,教師不能用已經固定化的概念命令學生接受世界。首先要求學生親近世界。也就是要求學生親近自我、了解自我,親近萬物、了解萬物。教師引導學生體會萬物,感受萬物迎面到來,最終擁抱萬物學習知識。這就要求教師上課多用形象的例子、具體的視頻、課外的實踐,而不是只灌輸僵化的概念。其次,要求學生學習態度端正。要求學生把寫作看成是自身的需要而不僅僅是一種技能,從而通過寫作把人性中最好的部分找尋回來,完善自我。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學習的目的是從個人到國家乃至全天下的一種逐步完善,應該是一種內在的逐步契合而非外在的過度強求。一旦教師對寫作課程的認識由追逐抽象概念開始,以掌握僵化技能結束,則是還沒有走向萬物,已定下了規范及目的,最終可能引導學生將萬物視為異于自身的隔閡物,將寫作視為工具,最終學生也處于被物化的危險中。學者李澤厚曾說:“昨日花開今日殘,是在時間中的歷史敘述,今日殘花昨日開,是時間性的歷史感傷,感傷的是對在時間中的歷史審視,這就是對有限人生的審美超越。”[5]同樣的文字符號,在不同意識觀照下排列,產生了意蘊完全不同的理解可能。這正是不同的自我覺醒層次在寫作中的呈現。過于強調寫作的工具性訓練并不會導向更高層次的文字表現,只會產生流水線般的沒有美感和差別的劣質文字,這在現今網絡上的文字狂歡中已有所體現。寫作課程要求寫作者有源自內心的對人和對萬物的親與敬。寫作者的人品即建立在此,人品即文品。寫作課程如做人一樣首先立意要高。教師應引導學生不拘泥于術的追求,跳出寫作,融入世界萬物中觀看自我與寫作。
三、以“物我兩忘”的觀點提高學生的寫作思維與技巧
寫作課程要求學生做到“格物致知”,這就對學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要求學生在了解外界之前必須先了解自我。學生必須由自我開始探討,對當下的我進行體認。教師必須以每個學生個體為出發點,將生命體驗作為課程設置的一部分。美國當代課程理論家派納(W.F.Pinar)2002年8月在東北師范大學接受訪問時,曾闡述了對課程的理解:“課程是提供知覺、情感和思考的生命經驗,而不是一種模仿或機械性的活動。也就是說,課程必須通過自身生命體驗與自覺的生命歷程,此經驗的學習不是被事先預定好的,而是個人在周遭世界中所感、所思的具體行動。因此,我的課程理論不是將焦點置于外在的活動,而是關注于內在與外在世界的交互活動,以及自我、他人及課程之間的磋商。”[6]這種課程是自我生命經驗的建構理論,強調學生對個體的認識和對課程的參與。當學生將寫作課程作為一種生命體驗與歷程時,寫作課程即成為一種活潑生動的構筑。當學生能在寫作課程進行時創造和具體化自我,寫作課程就成了一種關注和理解自我的生命體驗與歷程。
教師在引導學生進行課程體驗與建構時,可運用傳統文化中“物我兩忘”的觀點引導學生感受世界與尋求自我認同,最后主客體共在一天地間,物我皆在而物我皆忘,從而進入寫作的忘我境界。西方存在主義認為他人即地獄,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通過逐步認同把個人與社會他者的悖謬與沖突化為社會共生體。“物我兩忘”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將寫作主體的此在融入社會的此在中,達到一種共相式的自我認同。教師在具體的課堂操作中要力求動態呈現人與世界的交接,鏡像觀照社會,讓學生在回歸自我與觀照世界中掌握寫作技能,既以我觀物,又以物觀我,通過寫作提升寫作主體的存在感。只有這樣,寫作課程才能以學生的寫作技能成就學生的發展,從而走向真正的應用。至此,我們重新回到寫作的初衷,把寫作看做我與世界的互動前進,寫作完全成為人的一部分。一方面,人在寫作課程中得到更好的自我觀照,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成長,另一方面,寫作技能作為人的動態結構的一部分,也會隨之發展,得到更好的舒展。
四、以“有教無類”的信念打破學生的既定思維
正如伽達默爾所言:“理解過程發生在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是人類全部世界經驗的源泉,理解能力是人的一項基本限定,有了它,人才能與他人一起生活。”[7]37寫作就是這樣一種能促進人們相互理解與相互親近的才能。寫作作為一種個性化的才能,冷冰冰的命令式教學顯然并不能產生更好的作品。因此,寫作課程需要教師以“有教無類”的信念引導學生打破既定思維,展示個人風格。
寫作課程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學生最終寫出來的文本并不一定精彩。因為學生通常容易將事關自身的經驗美化,在文本中肆意擴大某部分經驗的分量而排除他者可能有興趣和想了解的部分,寫作主體的寫作意識最終讓文字轉化成乏味無力的文章。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學生存在過度親近自我,愛憐自我而受制于個體狹隘心理的可能,另一方面,學生因知識和經驗水平不夠深廣,可能出現個體意識受意識形態鉗制而不自知的情況。總之,學生個體若無法突破既有的思維框架,那么我們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寫作動態課程設置,最終只會是學生狹隘意識的原地打轉,無法提高學生對自身的認識和對世界萬物的認知,課程只能最終僵化,并成為一門終將被拋棄的課程。所以,寫作課程的能動參與,既是基于學生自身生活的存在式體驗,又是超越學生自身生活的眼界超越。在這里,學生與課程的互動,必須是在老師引導下的,超越自身生活認知的互動。教師要引導學生親近自身并把自身融為世界萬物的一部分,同時密切關注學生在參與課程建構過程中出現的自身意識偏差,反對學生螺絲釘式的自我狹隘定位。教師還要調整學生的狀態,增強學生的自我存在感,引導學生在眼界開闊的基礎上提高寫作能力。
總而言之,寫作課程應該是由傳統文化理念引導的學生充分參與的動態課程。學生的寫作與世界的關系是“我”與“你”的雙向親密互動關系,既是開放式的又是帶有私人情感的互動。教師以“有教無類”的信念引導學生帶著親近與敬意確定生活中美的有價值的東西,做到“格物致知”與“物我兩忘”。課程以“人”的完善作為最初出發點和最終的皈依,不是從文字的概念層面了解生活,而是“從精神生命的既定感性表現中,認識這種生命本身的過程”[7]33。課程價值在于,學生把主觀世界重新又變回客觀世界的一部分,通過反思,把生活的瑣碎條理化,通過訓練觀察能力、思維能力、記憶能力和想象能力,不再是以螺絲釘的自我觀照層次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以有意識的能動的世界觀照者的身份層次重新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寫作課程作為一門重要而獨特的課程,將獲得嶄新的意義。
[1][德]馬克斯·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哲學片段[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26.
[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Z].北京:中華書局,1980:131.
[3]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告子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67.
[4]魯潔.實然與應然兩重性:教育學的一種人性假設[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8:(4).
[5]鄧德隆,楊斌,編選.李澤厚話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5.
[6]許芳懿.William Pinar課程理解典范之探究[D].臺灣:“國立”高雄師范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5:10.
[7]金生竑.理解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