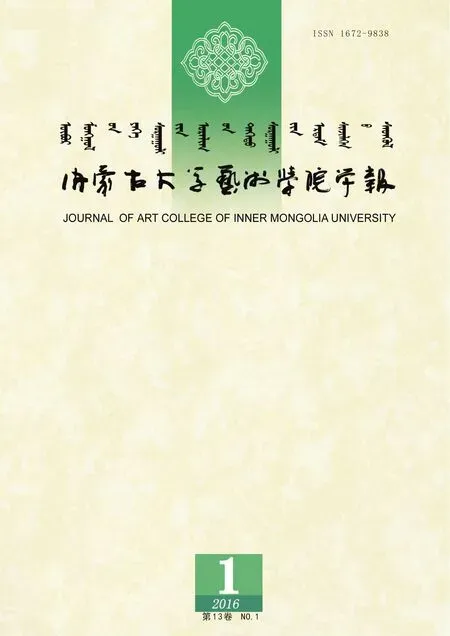廟會功能的演變與傳統文化現代性轉變的關系研究
——以江蘇省的三個城市為例
亢寧梅
(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 江蘇 淮安 223001)
廟會功能的演變與傳統文化現代性轉變的關系研究
——以江蘇省的三個城市為例
亢寧梅
(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蘇淮安223001)
廟會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處于守勢。在中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部門的行為對廟會的生存有相當大的影響。本文以江蘇省的三個城市為例,分析了廟會生存的現狀,認為以政府為代表的實踐理性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應當保持合理的“度”,現代旅游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應當保持一定的張力,不同領域的文化才能合理有序地發展。
廟會;政府;傳統文化;現代性
一、皂河安瀾龍王廟會考察
皂河鎮坐落于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湖濱新城,北臨駱馬湖,南瀕古黃河,是一座具有近400年歷史的文化古鎮、水鄉古鎮。全鎮總面積266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就占了219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實的水鎮。皂河發源于山東郯城墨河,南入京杭大運河,因水底土色發黑,故名皂河。明孝帝弘治八年(1495年),黃河泛濫,從蘭封縣銅瓦鄉流向東南經徐州、宿遷,因為皂河鎮地勢低洼,在此匯入運河,從此皂河地區洪災頻發,百姓常年遭受侵擾。為了祈求神靈護佑,消除水患,當地百姓在皂河鎮南首建了一座“大王老爺廟”。從那以后,每逢正月初九這個“陽”到極致的日子,人們都到大王廟敬香祭神,以此來壓住水的“陰”,祈求風調雨順。康熙十九年(1681),總督靳輔在舊皂河開建皂河碼頭,皂河鎮從此成為大運河南北漕運要道,商賈行船不絕,逐漸發展成宿遷西北部經濟貿易中心和水陸交通樞紐。
清朝初期,康熙六次南巡,途經皂河,發現水患依然嚴重。為了保地方安瀾、造福百姓,康熙帝宣旨,在皂河鎮南首敕建安瀾龍王廟,代替了原來民間的“大王老爺廟”。乾隆年間,乾隆南巡途經皂河,五次把龍王廟作為行宮,并且親自祭祀,焚香敬佛,祭拜龍王神,以此告誡百姓,只有誠心敬奉龍王,才能保佑地方安居樂業,永遠平安。由于這種官方背景,祭祀活動的民間色彩和官方色彩逐漸合一,影響力擴大。原先單純的祭祀活動逐漸加入了商品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內容,規模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最終形成了廟會這一具有節慶和祭祀功能的民俗活動。并且由皂河向周圍擴展,流傳于宿遷市及緊鄰的安徽、山東、河南三省毗鄰縣市。如今的皂河鎮保留有大量文物古跡、遺址、遺存、傳說,如安瀾龍王廟乾隆行宮、陳家大院、合善堂、奶奶廟等明清建筑,還有廟會、柳琴戲等活態文化遺存。1983年,安瀾龍王廟暨乾隆行宮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6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皂河古鎮安瀾龍王廟會也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統的皂河安瀾龍王廟會從正月初八開始,延續三天。以儀式“乾隆鑾駕巡游”打頭,廟會正式開場。“乾隆鑾駕巡游”還原了當時皂河安瀾龍王廟執仗人員恭迎皇帝以及巡游、祭祀時的盛況,涉及很多風俗、禮節,演員必須經過嚴格訓練。以往表演主體是龍王廟行宮柳琴戲劇團,有近百人參加。最近幾年情況略有變化,主要由民間組織“皂河古廟會夕陽紅民間藝術團”表演。藝術團目前有20多人,平均年齡在60歲左右,主要是喜愛民間藝術的老人。表演儀式需要近百人,其余都是熱愛這一民俗活動的市民自發加入的。他們還表演舞獅、舞龍、旱船、大頭娃娃、吉祥物等傳統民俗節目。百姓到龍王廟觀看儀式,同時進香祈福。龍王廟行宮建筑群布局嚴整,規模宏大,軸線分明,氣勢磅礴,雙重圍墻,保存完好,有著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的特點。整個建筑群分六大部分,最南端為古戲樓,額枋上懸掛 “奏平成”鎏金匾一塊,上下門懸有“陽春”、“白雪”金匾各一塊。廟會期間,古戲樓通常上演的劇目是:柳琴戲《小姑賢》《馬古驢換妻》,分別演繹家庭和睦、換妻成家大團圓的故事,有著節慶戲團圓、喜慶、輕喜劇的特點。柳琴戲屬于秧歌小戲系統中的拉魂腔,流布于山東、安徽等鄰近地區,以當地方言表演,高亢,粗獷,悲而不傷,通常綴著“光明”的結尾,體現了民間善惡相應的價值觀。
出了龍王廟行宮,還有兩處必去的地方。一是合善堂,建于清光緒二十年,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里有前后兩進院落,占地面積1500平方米。正堂中供奉觀世音菩薩,后堂供奉釋迦牟尼,是慈悲的象征。二是財神廟,是一座保存較好的清代廟宇,雖然不大,但香火很旺,因為有一只能“吸金”的“神龜”。“神龜”為石質,位于院中的水池里,傳說只要用錢幣砸中龜,就有財運,因此新年伊始,人們都要試試手氣,同時上香、敬奉財神、祀求降福、賜財。
以上這些活動貫穿著百姓對幸福、團圓、財富的向往,還有對禮、義、天、地的信仰,屬于民間價值系統,是廟會活動的核心。廟會作為民俗行為,除了精神信仰活動,實際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游、玩、吃、看,娛樂、熱鬧,還有情感交流和商品買賣。從前,年輕男女愛趁趕廟會的時候見面,廟會也是走親戚、聯絡感情的好時候。今天,在擁擠熱鬧的人流中欣賞地方傳統民間手工藝,有草編、米粒刻字、根雕、糖人等,地方傳統美食有銀魚、青蝦、紅心鴨蛋、乾隆貢酥等,還有現在的各種生活用品、服裝、玩具、花木、小寵物、藥材、煎餅等。鄰近的山東、河南、安徽的民間藝人展示了精彩的技藝:“木刀木劍紅纓槍、桃猴玉兔青竹蟒、剪紙雕刻撥浪鼓、糖人泥哨小花棒”。 廟會上傳統經典的小吃有蒸米糕、麥芽糖、冰糖葫蘆、臭豆腐、梅花糕等,時興的有韓國炒年糕,西藏青稞餅,清蒸梭子蟹,鹵肉卷,現熬椰奶、內蒙古烤肉、臺灣一口蟹、印度飛餅、韓國醬汁鐵板豆腐、大連鐵板魷魚,這些也是與時俱進、全球一體化的表現吧。
延續三天的皂河安瀾龍王廟會,正月初九是“正日子”,這幾年據地方相關部門統計,每年參與人數都在60萬人左右。接下來還有正月十五元宵節廟會,情況也差不多。到這個時候,熱鬧的春節才算是依依不舍地結束了。
二、南京、南通的廟會被政府部門取消
“正月過年,二月趕會,三月種田。”民間自發形成的廟會民俗,通常是春節的延續,也是以自然節氣的規律性變化為取向,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的天人之情在民間的生動表現,所以廟會才被稱為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小年”過后的二月,正是廟會最集中的時段。民間認為整個正月都是春節,雖然時令到了二月,春意融融,但是農忙還沒有開始,人們還想把春節的歡樂延續下去,各地的廟會絡繹不絕,比如著名的溫州 “攔街福”,北京懷柔的“斂巧飯”。
然而據2015年3月18日《新華日報》報道,南京市棲霞區相關部門發布通告,取消龍潭、棲霞、西崗三街鎮的八場廟會。與此同時,玄武、江寧、浦口三個區也取消廟會,也就是說加上江寧的南京七個區,除了著名的夫子廟燈會,廟會幾乎絕跡了。
細細追蹤起來,這些廟會的起源不外乎是祭祀祈福。位于棲霞區燕子磯的關帝廟,位于龍潭區的娘娘觀,位于浦口的兜率寺,都在長江邊,都與祭祀龍王有關。在年節祭祀的同時祈福,也游玩熱鬧,這正符合廟會的特征。在交通不便、生活閉塞的時代,各個地方長期以來形成了一些富于特征的民俗活動,如棲霞山的攝山觀龍燈、龍王山的元宵祭拜,最早可以溯源到明代,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屬于典型的地方性知識傳統。
對于廟會被取消,政府管理部門解釋為:廟會是農耕社會的產物,與城市化進程不相匹配。農民拆遷后住進了小區,不再有傳統的廟會場地,如果轉到集貿市場和主干道,又容易造成交通擁堵。從前的廟會活動,大宗農資、生產資料交易是重頭戲,如今農民的身份變了,這些就不再需要了。并且廟會上的小商品和食品以假冒偽劣產品為主,處于工商管理的盲區。來自安徽、河南、山東的流動廟會行會組織,根據各地的黃歷趕廟會,造成大量交管、衛生、城管、治安問題。草臺班子也不再表演民俗,而是表演山寨、色情節目。一旦造成后果,政府部門難辭其咎,干脆就把廟會禁止了。
無獨有偶, 據2015年5月13日人民網報道,今天是農歷三月二十五,按多年的習俗,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興仁鎮廟會應該在這一天熱熱鬧鬧開幕。但是5月初,興仁鎮人民政府宣布“永久性取消” 興仁鎮廟會,原因是“受條件限制,人多擁擠存在交通和安全隱患”。
查詢相關資料,興仁鎮始建于唐朝,已經有上千年歷史,興仁廟會起源于清朝。興仁鎮北有一座東岳廟,廟碑記載,東岳廟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建成于嘉慶三年(1798)。廟中供奉一尊“元帥”塑像,是一位民間傳說中的地方神,每年農歷三月二十五日出會。如此看來,廟會已有二百余年的歷史。東岳廟會有一套完整的儀式:“元帥”出巡,有龐大的隊伍為前導:頭牌鑼、龍鳳彩旗隊、鑼鼓隊、高蹺隊、跳判隊、馬叉隊、蚌殼精、花籃隊、肉香隊、大鑼大鼓隊、傘蓋隊、如意香隊、絲竹樂隊、龍燈隊等等。然后是神船隊和轎隊。神船里是“元帥”和“太太”的小行身,在旗牌和大鑼的引導下,“元帥”的八人綠呢大轎隆重登場。一路上有地方士紳鄉董跪獻祭菜,最多的時候達到十八張宴桌。廟會既有隆重的祭祀活動,又是熱鬧的集市,還有各個雜耍戲班的表演。這個儀式既有對天地、神靈崇敬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又充滿了世俗的氣氛,可謂是地方民間文化小傳統的一部分。三月廟會正值南方四夏大忙即將來臨之際,是農民緊張忙碌前的放松,難得的閑暇。六月二十九日的興仁城隍廟會是巫公盛會,又稱“孝神盛會”,起源于紀念一位巫姓孝子。巫子經歷了逆子變孝子的過程,成為民間道德訓誡的范例,類似于《除三害》里的周處。清乾隆二年(1737),興仁城隍廟擴建,在新大殿上設了巫公祠,從此興仁城隍廟會流傳不絕。興仁城隍廟會儀式具有強烈的內省和道德教化功能,能夠引發民眾自省,叩問天地良心。這正是它作為傳統文化遺產最可寶貴的“本真性”,也是它作為儀式的高峰體驗的價值所在。隨著時代的演變,廟會的形式、內涵也有所改變。新中國成立后,廟會逐步去除了迷信色彩(去除了儀式的同時,也去除了神圣性,也去除了祈福禳災、敬畏自然、道德訓誡等等最重要的功能。)主要變為農副產品交易,并且一度更名為物資交流會,政府在工具理性主導下完全以實際功利性取代了神性。隨著現代交通條件的便利,兩個廟會的影響地域也逐漸擴大,是目前南通市規模最大的民俗活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府也沒有明文禁止廟會。隨著意識形態的松弛,民間社會逐步擴大,近年來的廟會集祭神、娛樂、商品交易于一體,每次大約有10多萬群眾參加。廟會聚集地段主要在洋興公路和興中路,綿延約4公里。
興仁鎮政府宣布取消興仁廟會,造成了民間的強烈反應,網上輿論發酵,甚至有嚴厲的措辭指責政府“懶政怠政”。興仁鎮相關負責人接受了人民網采訪,認為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看,取消廟會是吸取上海新年踩踏事件的教訓,出于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考慮,應當得到理解擁護。具體到興仁廟會的情況,主要原因大體上還是假冒偽劣商品多、交通管理困難、擾亂了正常生活生產秩序,有安全隱患,衛生、治安壓力大,綠化破壞嚴重,表演低俗等等。并且以興仁鎮兩屆人大委員已經做了充分調研為依據,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看戲祭神的廟會演變成了趕大集,只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在商品買賣非常方便的今天,廟會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鎮政府在4月份組織了人大代表、教師、公務員和“部分群眾”召開座談會,最終做出取消廟會的決定。同時也通過張貼公告、分發通知等形式進行了廣泛告知。政府部門認為自己已經盡到了責任,做足了功課,有理有據,是為群眾的安全考慮。但是群眾不認可政府的決定,感情上對廟會不能割舍,認為自己“被代表”了,廟會具有強烈的南通地域認同性,是南通人的共同回憶。一紙通告過于草率,完全是政府單方面的行為,傷害了民眾的感情。認為政府“無視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砸了傳統手藝人的飯碗”。
作為民俗重要表現形式的廟會,在江蘇省的不同地區,生存現狀迥然有別。在信息產業高速發展、科學昌盛的現代社會,廟會到底還有沒有存在的空間和必要?政府應當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措施?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三、廟會的現代演變和政府的作用
從上述三個城市的廟會現狀看,宿遷的皂河廟會是保護發展比較好的,政府的定位和采取的措施也相對比較合理。
首先,皂河廟會所在地的宿遷市宿城區區長作為最高行政領導直接負責廟會的相關各項工作,這在中國的行政運行管理體制中是有效的。雖然目前正在由“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過度,但是政府的組織、管理還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政府一是把皂河廟會定位為群眾自發性廟會活動,政府的功能是組織、引導、管理。把廟會功能定位為:展示深厚的地方歷史文化,打造宿城文化名片,提高宿城知名度和美譽度。“更祥和、更繁榮、更平安、更文明”是總要求。二是把握關鍵,詳細制定各項工作預案,提前安排統籌廟會聚集點,營造宣傳氛圍,確保廟會活動安全有序進行,適應城市發展新變化,“保障人民群眾廟會安全”。這里撇開行政套話口號,對政府部門的實際工作有明確的要求,也符合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總方向和地方政府發展經濟、追求政績的行政訴求。
其次,圍繞皂河廟會的生存和發展,地方政府也做足了功課,不過這個功課與前述的南通市通州區興仁鎮政府正好相反。為了保證廟會活動的安全有序進行,區政府精心規劃,做好宣傳造勢工作。相關信息在中國江蘇網、宿遷網、《宿遷日報》等媒體上反復傳播。各個相關部門做了充分預案,如道路布點、安全保衛、車輛分流等,對相關路段進行交通管制,提前反復通告,臨時抽調上千警力全程監控,保證安全。切合現代城市商業發展形勢,把廟會會址設在原來就很熱鬧的馬陵路商圈,增加了人氣,同時對臨時商業區域進行規范劃分,各種商品分類匯聚,既方便了游客,也便于管理。
最關鍵的是,政府部門根據現代旅游經濟的發展,調整思路,借著皂河古鎮安瀾龍王廟會晉身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風,把這個民間自發形成的民俗活動悄悄地向由政府主導的、有組織的、有序的特色旅游活動轉變。這個轉變又分為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從2013年開始,皂河龍王廟會就“擴容”成了文化旅游周,提前到初五,延續六天。原來的“鑾駕巡游”儀式只有初八到初十共三次,現在則調整為初一到十五每天都舉行一次。現代理性去除了儀式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大眾社會又把它變成了一項純粹的娛樂活動。在“紫氣東來降祥瑞,金羊報喜迎春來”的氛圍里,柳琴戲表演、祭財神、“乾隆出行”(由“鑾駕巡游”演變而來)、花燈展等形式多樣的表演性的民俗活動成為廟會的看點。同時根據歷史記載新建了“下江南大觀園”和安瀾橋。新“發現”、“挖掘”、修繕了“古跡”陳家大院,這個建筑群始建于清朝嘉慶年間,是宿遷目前最大的古民居。陳家大院占地6畝,北方回廊式建筑結構,共有房屋66間,建筑面積1500平方米,有著從清朝到民國到新中國的復雜演變史,還有民眾最樂于想象的豪門恩怨。“整舊如舊”了通圣街。這條街貫穿南北,一直是皂河的商業中心,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紀80年代,磚瓦結構的平房,最高的建筑是三層的影劇院。街上的店鋪大都有20年以上歷史,很多店主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有老舊的“鏡店”、“大眾浴池”、“大眾電器修理”等招牌,老人們慢悠悠地做著生意,也展示著手藝。在似乎靜止的時光里,保留了“活態”的舊生活空間,滿足了快速發展的社會里人們的懷舊心理。這些地方文化遺產一旦變成旅游資源,就具有了經濟價值和展示意義。
以上的轉變還僅僅是近期目標,旨在提升廟會的文化內涵、品味、知名度和影響力,打造全新的皂河鎮旅游文化品牌。應該說這個目標正在實現中。長遠目標在政府的規劃下正在進行。2013年5月14日,由攜程集團和古鎮網在上海聯合舉辦的“文化古鎮、智慧論壇”上,皂河鎮榮獲“2012年最純凈生態古鎮”稱號。有了這塊招牌,鎮政府制定了“借勢文化優勢,規避自身不足,把握歷史機遇,轉化外部挑戰”的發展策略,以大運河文化遺產長廊構建和蘇北旅游新三角的崛起為契機,迎合古鎮旅游和湖泊旅游的開發熱潮,通過差異性、創新性旅游大項目的開發,轉換外部挑戰,力爭把皂河古鎮構筑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品牌。鎮政府把古鎮開發旅游項目向全國招標,北京的達沃斯巔峰旅游規劃設計院拔了頭籌,做了《宿遷皂河古鎮旅游區總體規劃》。在這個科學規劃里,以乾隆行宮為代表的皇家文化、以皂河廟會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駱馬湖、古黃河、古今大運河歷史人文為代表的水文化,被有機地結合起來,打造為駱馬湖文化制高點。核心理念是:立足于區域旅游發展格局中的古鎮與兩河一湖,由“皂河古鎮”轉變為“龍運皂河、皇家水鎮”,實現皂河古鎮旅游開發經濟效應和文化效應的雙贏,力爭將皂河龍王廟會逐步打造成華東地區乃至全國范圍內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重大的民俗節慶活動。
這里我們發現,傳統的民俗文化悄悄地變成了當代旅游節慶文化,政府是這個轉變的推手。傳統民俗作為符號,內涵被置換了,現代理性對儀式的神圣性進行了祛魅,包裝成了一個娛樂形式,也去除了民俗的本真性。現代旅游熱、節慶熱、古鎮文化熱等等因素以及政府的政績訴求共同促成了這一轉變,類似的例子在全國還有很多。傳統民間文化變成了現代娛樂文化,也許在政府主導的、快速劇烈的城市化進程中,民間文化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存在。[1](249-259)
反觀南京的一系列廟會和南通的興仁廟會被取消,無論從經濟效應還是文化效應上看政府的舉措都是不合適的。南京的相關區政府把廟會定位為“色情、低俗、低檔”, 興仁鎮政府認為“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要敢于揚棄,時間會證明一切的。”從性質和功能上把民間文化與“先進”的時代主流文化對立起來。其實,廟會作為民間文化傳統,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可以說就是草野的、葷味的、狂放的,是眾聲喧嘩的釋放和熱鬧。按照張法先生對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的劃分,傳統審美形態分為四類:朝廷、士人、民間、市民。中國最廣大的是鄉村,但民間美學沒有形成獨立的形態,它為朝廷、士人、市民美學提供基礎,同時又依附于這三者,并且通過它們表現出來。[2](292)民間文化作為母體,與處于高位的朝廷文化、士人文化不但不是矛盾對立的,恰恰是相互補充、循環良性發展的。劉錫誠先生認為民俗文化“其實并非一個很小的傳統,反倒是一個很大的傳統”,西方文化人類學者認為的精英文化是大傳統的觀點不一定適合于研究中國文化。民俗文化與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手工業生產方式相適應,與幾千年形成的中國家族社會和人倫社會結構相適應,并且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逐漸融匯和附會了許多文化涵義,帶上了農耕生產方式和家族人倫制度的特點。所以中國的民俗文化精神是生生不息、自強不息、天人合一。[3]可以說民俗文化的世俗性、神秘性、神圣性與主流文化是完全一致的,主流價值觀在民俗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傳播,民俗文化具有對傳統認同的重要功能,這也是民俗文化的最大價值,與今天的和諧社會理論也是一致的。西方文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托尼·班尼特在《文化 歷史 習性》一文中認為習俗有強大的治理功能,對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而我們的政府部門卻把民間文化與主流文化對立起來,認識不到它重要的娛樂和教化功能,這是很可惜的。民俗作為強大的傳統,有傳承性和心理暗示性,公序良俗起著強大的道德倫理“軟”作用,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世俗社會里。民眾的文化記憶是長久的,珍貴的,需要好好加以保護,才能使文化傳統延續下去。網友們的吐槽:“興仁廟會是我童年的記憶和永遠的懷念,取消了,太傷我對故鄉的情懷了。”“這么多年的活動就這么沒了,心里也覺得空蕩蕩的。”都表達了這樣的心理。
其實如果仔細考量政府部門的理由和舉措,就會發現民眾對政府“懶政怠政”“無視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指責有相當的合理性。現代社會城市交通安全問題日益復雜,政府不愿意承擔組織管理、安全責任,干脆一禁了之。至于鎮政府以兩屆人大委員的調研為依據,組織人大代表、教師、公務員和“部分群眾”舉行座談會,可以說更是一個無視民意的行為。這些“群眾”是體制內的成員,他們所在的“單位”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組成部分,而作為廟會參與者主體的廣大民眾是草野的,民間的,沒有“單位”的,只有他們才能決定廟會的舉辦取舍。再說僅僅二十余人的座談會能代表十萬民眾嗎?
政府部門從主流文化的立場,批評廟會上的山寨、色情表演。無非是以大眾文化的末流代替了民間文化中“葷”的部分,其實功能是相同的,因為沒有了民歌、民間小戲表演,大眾文化就占據了民間文化的空間。傳統的民間文化領域,“葷”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與大眾文化的欲望表達殊途同歸。而民間從來就是一個眾聲喧嘩的領域,無需過分地凈化,更不用把這些現象看作洪水猛獸。無論是交通安全,還是民俗表演,都可以通過規范、引導加以管理,當然需要政府踏踏實實的調研和巨大的投入。
四、余論
與此同時,同樣是在南京,著名的“慢城”高淳,從正月開始,舉辦了多場廟會,各種民間藝術如古戲臺、黃梅戲、大馬燈、跳五猖等上演了三百多場。當地政府部門認為,民俗文化是一個重要的空間,應當用好這個空間,才能避免淪為行商和草臺班子的領地。他們也對傳統民間藝術進行了“去粗存精”式的整理,予以去“葷”化、精致化、雅化,但是相對還是保存了大部分的“原汁原味”。雖然他們對民間藝術的理解也是功利性的,但在實踐中對民間文化顯然采取了包容的心態,對民眾的心理、民間立場有比較好的理解,使民眾感覺到這個舞臺還是他們的舞臺。
2015年6月16日,針對興仁鎮廟會被“永久性取消”事件,人民網發表評論文章,批評鎮政府“因噎廢食”、行政不作為。隨后,鎮政府進行了反思,表示:可在適當的時候恢復興仁鎮廟會活動。
其實,興仁鎮周邊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資源,如香光寺景區、中國乒乓球通州訓練基地,等等。如果結合興仁鎮廟會活動進行認真策劃,應當是很有價值的旅游資源。
我們認為,文化從來不能分為精華與糟粕,對文化進行功利主義的理解是現代性的失誤,導致現代社會的發展付出了巨大代價。早在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在《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以政府為代表的實踐理性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應當保持合理的“度”,現代旅游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應當保持一定的張力,不同領域的文化才能合理有序地發展。
[1]周星.古村鎮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再發現”[A].鄉土生活的邏輯[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張法.中國美學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3]劉錫誠.民俗文化是一條滔滔巨流[DB/OL].中國藝術人類學網.
【責任編輯徐英】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Temple fair's Function and the Modern Change of Traditional Culture——Taking Three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Kang Ningmei
(College of LiberalArts,HuaiyinNormalUniversity,Huaian,Jiangsu,223001)
Temple fair as a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n the defensive in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In China's curren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the behavior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survival of the temple fai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mple fair survival status in charge of three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t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maintain a reasonable "degree", while the modern tourism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keep a certain tension ,thus culture in different areas can be in 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
Temple fair, Govern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ty
G122
A
1672-9838(2016)01-034-06
2015-11-01
本文為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項目,江蘇省品牌專業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亢寧梅(1969-),女,江蘇省南京市人,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