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音樂研究百年(七)
博特樂圖 郭晶晶
(1.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 2.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
蒙古族音樂研究百年(七)
博特樂圖1郭晶晶2
(1.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2.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
蒙古族多聲音樂研究(上)
蒙古族多聲音樂,可用“潮爾”(?oor)一詞概括。“潮爾”為蒙古語,意為“和音”、“共鳴”。蒙古族“潮爾”音樂既有獨立體裁的,亦有附著形態的;有人聲的、器聲的以及人器聲混合的。其中,人聲演唱的潮爾,有一個人演唱的浩林·潮爾和多人演唱的潮爾道兩種;樂器演奏的潮爾有弓弦樂器潮爾和托布舒爾;冒頓·潮爾和薩木·潮爾是人聲與器聲的結合形式。這些“潮爾”系列體裁,有一個高度程式化的模式,便是在一個持續低音聲部的基礎上,唱或奏出高音旋律聲部,從而形成二聲部結構。這種形式可以由一個人單獨表演(如,浩林·潮爾、冒頓潮爾),也可以是多人表演(如,潮爾道)。它有人聲演唱的形式,也有器樂形式,又有人聲與器聲結合的形式。如,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弓弦樂器潮爾,是一種樂器形式,演奏時用弓子同時擦奏內外兩根弦,在外弦高音弦上按奏出旋律聲部,內弦低音弦則保持空弦持續低音。新疆阿勒泰地區的冒頓·潮爾,是一種聲樂與器樂相結合的形式,演唱時表演者唱出持續低音聲部,同時用笳管吹出旋律聲部。因此,蒙古族多聲音樂的研究,主要圍繞呼麥、潮爾及“潮爾”系列音樂體裁的概念術語、本質特征、歷史源流、文化屬性、區域分布、音樂形態、唱奏特征、多聲機理、表現形式以及潮爾體系音樂的共性與個性等方面進行研究,研究成果豐碩,是目前蒙古族音樂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
一、關于蒙古族多聲音樂的概念及其分類
(一)關于“潮爾”的概念及種類
在內蒙古東部科爾沁——東土默特地區,“潮爾”一詞指一種類似馬頭琴的二弦馬尾弓弦樂器。莫爾吉胡先生的早期論文《“潮兒”大師——色拉西》一文中首次介紹潮爾琴及其多聲現象。關于其形制,介紹說琴弦是由馬尾縷成,高音弦大致由五十余根馬尾,低音弦是九十余根馬尾縷成,兩根琴弦相距四度。[1]烏蘭杰在《蒙古族音樂史》中介紹到,拉弦樂器抄兀兒,乃是蒙古人所創造的一件具有草原特色的樂器。其樂器形制是:倒梯形的琴箱上蒙之以羊皮,約三尺余長的琴桿貫穿其上。兩根弦均以一縷馬尾為之,弓子則是以食指般粗細的柳條彎制而成。唐、宋以來,從蒙古族彈撥樂器中演變出來一種新的拉弦樂器,蒙古語稱之為“奇奇里”,也譯作“也克勒”。奇奇里是兩弦拉奏樂器,琴弦以馬尾為之,被認為是馬頭琴的前身。奇奇里善奏雙弦和音,保持著胡笳時代人聲與胡笳同時共鳴而形成雙音的特點。蒙古人取其共鳴之意,稱之為“抄兀兒”。[2](105)
在內蒙古中部的錫林郭勒地區,該詞表示民間多聲部合唱“潮林道”的持續低音聲部。莫爾吉胡認為,即由著名歌手高腔演唱婉轉動聽的長調旋律,另有數名歌手用渾厚的低音,在其下方構成主音持續低音的獨特二重結構的演唱,人們也稱其為“潮兒”。[3](10)他還認為,這是自古流傳下來并帶有禮儀性的祭祀歌曲,也是蒙古人所無限崇尚的音樂形式。其演唱形式:上聲部華彩旋律由一二位著名歌手領唱,在其下聲部是固定的低音持續音自始至終相襯。這樣,兩個聲部構成具有獨特音響的合唱:時而是八度(十五度)、五度(十二度)或四度(十一度)關系,整個合唱洋溢古樸、渾厚、敦實的雄健氣勢......[4](1)烏蘭杰在《蒙古族音樂史》中對潮爾合唱這樣定義:潮爾,蒙古語為“共鳴”之意,是蒙古族所特有的合唱形式,一般由藝人領唱,另有一二人擔任“潮爾”,從而形成多聲部音樂形態。[2]

圖1 ①《追尋胡笳的蹤跡——蒙古音樂考察紀實文集》書影
在新疆阿勒泰地區,“潮爾”音樂有浩林·潮爾和冒頓·潮爾兩種形式。上個世紀80年代,著名學者莫爾吉胡在新疆阿勒泰地區進行考察,寫出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文。在《追尋胡笳的蹤跡》[3](166)和《“浩林·潮兒”之謎》[5]兩篇論文中,他根據對新疆阿勒泰地區罕達嘎圖蒙古族自治鄉塔本泰、瑪尼達爾和布林巴雅爾等藝人的調查,首次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冒頓·潮爾和浩林·潮爾。《追尋胡笳的蹤跡》一文中寫于1985年,莫爾吉胡將把阿勒泰蒙古人當中流傳的冒頓·潮爾與中國古代著名的胡笳進行比較,得出冒頓·潮爾便是失傳已久的胡笳的結論。論文把自己對胡笳(冒頓·潮爾)的追尋和相關問題的理論思考,放置在自己在阿勒泰地區所進行的田野考察的記述當中,再現了阿勒泰地區蒙古人當中流傳的冒頓·潮爾,并從“樂器—樂人—樂曲”三維角度,進行了富有創見的探討。論文通過實地考察,對新疆阿勒泰蒙古人當中的胡笳(冒頓·潮爾)的形制及演奏法進行詳細描述的同時,記錄并介紹了《葉敏河的流水》(瑪尼達爾奏)、《棗紅馬》(瑪尼達爾奏)、《阿勒泰的贊頌》(瑪尼達爾奏)、《沖鋒的呼喊》(瑪尼達爾奏)、《奔跑的黑熊》(瑪尼達爾奏)、《丟失腰帶的姑娘》(瑪尼達爾奏)、《哈巴河水的波浪》(瑪尼達爾奏)、《深谷中的回聲》(瑪尼達爾奏)、《上了馬絆的黃走馬》(塔本泰奏)、《黑舌頭的牛》(塔本泰奏)、《報春的鳥》(塔本泰奏)等11首樂曲,并總結出“獨特的二重結構”、“自然五聲調式”、“音樂內容的單一性”、“音樂的標題性”等特征,并運用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將《阿勒泰的贊頌》與漢代從西域傳入中國的著名樂曲《摩訶兜勒》進行比較,認為“摩訶兜勒”一詞便是蒙古語“贊頌”的意思,故《阿勒泰的贊頌》便是《阿勒泰的摩訶兜勒》的觀點。他進而指出,胡笳是蒙古族古代樂器,張騫將其從西域引入中原,而《摩訶兜勒》不是一首笳曲,而是笳曲的整體。笳曲就是“摩訶兜勒”曲,就是胡人(蒙古人)對大自然、故鄉、阿勒泰贊美頌揚的由笳管吹奏的樂曲。論文中還列舉了“潮爾”的多種表現形式。本文詳細介紹了阿勒泰潮爾的兩種形式——浩林·潮爾和冒頓·潮爾,認為阿勒泰的潮爾與蒙古潮爾屬于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而浩林·潮爾是內蒙古兩種潮兒的源,其中浩林·潮爾更是較早的古音樂文化范疇的音樂現象。在《“浩林·潮兒”之謎》一文中,莫爾吉胡介紹了流傳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的另一種潮爾音樂體裁——浩林·潮爾。他根據阿勒泰罕達嘎圖蒙古自治鄉塔本泰和布林巴雅爾兩位藝人的談話內容,介紹了浩林·潮爾的表演形式。他將浩林·潮爾的唱法總結為:先發出主音上的持續低音,接著便同時在其上方(相差三個八度)發出一個音色透明的大調性旋律,最后結束在主音上。同胡笳曲一樣,全曲是單樂句構成的樂段。是一口氣完成的。他認為,吟是持續的低音,一直延續到全曲結束,而在其相差三個八度的上方,疊置出現一個優美完整的旋律線條(音色近似長笛高音區)。樂曲極為簡單,全部是一口氣一段的大調性曲調,無題無詞。有時低音的吟是四度跳進到主音。泛音旋律線與持續低音的有趣結合,構成了奇妙的二重結構的音樂(原始多聲部音樂),其音響多彩,令人感到空曠而神奇。[5]趙·道爾加拉、周吉兩位學者合編的《托布秀爾和楚吾爾曲選》一書的文字介紹部分,對阿勒泰蒙古人的冒頓·潮爾進行了詳細介紹,并介紹了當時兩位重要傳承人塔木泰和瑪尼達爾,是冒頓·潮爾研究的早期重要文論。[6](99-115)莫爾吉胡認為,在內蒙古西部或新疆蒙古族地區的“潮兒”音變為“粗兒”。有的是地方音變為“蕎兒”。無論是“粗兒”或“蕎兒”在這西部蒙古族地區不再是指馬頭琴,更不是民間傳統合唱,而是指蒙古族古老吹管樂器——胡笳,他將這種現象稱其為“潮兒現象”。[4](3)呼格吉勒圖認為,具有深刻影響的潮爾現象發展為“抄爾系統”。“抄爾”(潮爾——筆者注)不僅反映著器樂抄爾歌曲或抄爾樂器的存在,還反映著“抄爾”一詞已概括了蒙古人特有的關于多聲音樂的含義。他還認為,抄爾一詞來自古代蒙古人的音樂審美觀,它也是古代蒙古人關于多聲部音樂概念的初步認識的表現。[7](454-455)
李世相認為,按“潮爾共鳴說”來看,“潮爾”是指物理學、音響學的一種“共振”現象(指基音與泛音的關系),但共振或共鳴又必須依靠一定的物體震動才能實現。蒙古族民間所謂的“潮爾”,實際上是對某一具體音響共振現象的俗稱或泛指。[8](64-65)博特樂圖認為,蒙古人關于多聲——“潮爾”的概念,是在一個持續低音聲部與一個旋律聲部的對比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們在世間萬物的“動”與“靜”或“變”與“不變”的自然法則中總結出了一種獨特的聽覺美,于是用音樂把它表現出來。持續的低音以“靜”或“恒”的形式出現,象征亙古不變的大地;以“動”或“變”的模式出現的旋律聲部猶如大地的河流、綠草、鮮花、鳥獸、人畜等世間萬物,生機盎然,自由奔放、變化無窮、輕輕飄逸在持續低音之上。從民間合唱潮林道到一人獨唱的浩林·潮爾,再到人聲與器聲組合的冒頓·潮爾、薩木·潮爾,以及弓弦樂器烏塔森·潮爾等,都屬于這一特定的審美表達范疇。[9](17)李·柯沁夫認為,潮爾,蒙古語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聲音同時鳴響之意;后將凡帶有持續低音的多種形式的潮爾音樂,“統稱為“潮爾”;有時亦指多種蒙古族復音音樂(即潮爾音樂)中的持續低音(哈日嘿拉);在科爾沁草原民間,“潮爾”則是烏塔森潮爾的簡稱。[10](26)代興安從“潮爾”一詞的語言學特征以及潮爾的聲音、形制特征出發,對其本質進行闡述,并從神話學的角度,對其來源和所體現出來的蒙古人獨特的音樂認知方式進行探索,進而認為,潮爾是人類音樂的原生形式——人體樂器,亦是蒙古族音樂的原初形態。潮爾來源于大自然,體現了蒙古人與大自然間相處的關系,它表現了蒙古人對大自然的種種認知和情感,是蒙古人對待自然的文化心理的生動體現,而“潮爾”一詞恰恰體現了這一基本的認識論。[11](331)
博特樂圖在厘清潮爾概念與雙聲系統間音樂體裁的關系時,將“潮爾”一詞作了不同角度的梳理,認為蒙古語“潮爾”一詞有兩種用法:一是作為單詞時,具有“個指”的意義,表示具體的音樂事象。如,弓弦樂器潮爾以及潮爾道中的潮爾聲部;二是,該詞作為后綴詞或前綴詞使用時,具有“類指”的意義,如,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浩林·潮爾”和“冒頓·潮爾”,錫林郭勒地區的“潮爾道等。他認為,無論是“個指”的,還是“類指”的,這些不同體裁在“潮爾”這一層面上是統一的——二重聲部結構式它們共同的特點。[9](16)他認為,可以總結出“潮爾”一詞不同的所指:一是,指樂器,如弓弦樂器潮爾、吹奏樂器潮爾。二是,指潮爾系列音樂中的低聲部而言,如潮爾道持續低音聲部。三是,指一種由一個旋律聲部和低音聲部構成的多聲音樂體裁。四是作為前綴詞或后綴詞使用時,“潮爾”一詞具有“類指”的意義,指“高——低”兩個聲部以及與其相對應的“旋律——持續低音”二元關系模式而言,從而與前后詞共同構成了一個名詞,表示某一特定體裁。[9](16)徐欣認為,“潮爾”的核心意義之所以說法不一,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語音的影響。[12](37)她在《草原回音:內蒙古雙聲音樂“潮爾”的聲音民族志》中就“潮爾”在“對象層”的多種所指進行梳理,繼而也嘗試跨越其表層所指,圍繞“語音和語義”這一對關系來探討“潮爾”一詞的原意,她認為,潮爾一詞有兩種性質,其作為名詞,代表了各種體裁(對象),而作為形容詞,則代表了一種聲音的核心結構(意義)。在她對于潮爾作為形容詞的語義從不同讀音與語義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后,傾向于將“潮爾”一詞認為第五元音,其詞根源自“楚日亞”,即“回聲”“共鳴”之意,而第四元音只是民間音變或者地方方言。[12](48)
關于“潮爾”一詞,曾有“潮爾”、“潮兒”、“抄兒”、“抄爾”、“楚吾”、“紹爾”等不同寫法。關于規范“潮爾”的漢語音譯問題,柯沁夫提出六條音譯原則,(1)尊重傳統;(2)適應現代;(3)考慮約定俗稱之因素;(4)在接近準確音譯的前提下,不必完全拘泥于蒙古語原發音。如(漢譯的)馬頭琴、蒙古語是“莫林胡爾”,只有馬頭琴的意思;(5)在多個詞的比較選擇中,盡量取舍含有善意、美意之詞,回避可能造成貶義、歧義的音譯;(6)簡潔明了。他建議以“潮爾”這兩個字來記寫,以統一標準,避免混淆。[13](73)布林在《潮爾釋辨》一文中指出,近年來,隨著對蒙古族傳統潮爾音樂即多聲部音樂的熱議日趨升溫,對潮爾一詞的語音及其語義的研究探討也愈加熱烈而深入。他認為,潮爾是蒙古語的漢語音譯詞。因為是音譯,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書籍中有“抄爾”、“抄兀爾”、“綽爾”、“珠爾”、“潮兀爾”等多種技法。潮爾則是現代人們普遍已習慣和接受了的記法。現在常見的傳統的潮爾音樂形式除其源頭的兩項而外,至少還有潮林哆、冒頓潮爾、托布秀爾、胡仁烏力格爾四種形式是無可非議的。[14](94-97)
(二)關于潮爾音樂的分類
可以適當增加豬只的飼養密度,利用豬體自身的散熱來取暖,例如可放15頭豬的圈舍,可增加到20頭,等飼養4周后,再把生長緩慢的5頭仔豬調出重新組圈。
莫爾吉胡的《“浩林·潮兒”之謎》一文中介紹到,塔本泰老人將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潮爾分為兩種。一種是“冒頓·潮爾”(即胡笳),一種是“浩林·潮爾”。“冒頓·潮兒”是用一種木管和人聲演奏的。“浩林·潮兒”完全是一個人唱出來的。[5](22)在此基礎上,莫爾吉胡又將稱為“潮兒”的事物進行分類,他將流傳在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潮爾琴和流傳在錫林郭勒察哈爾地區的民間潮爾合唱統稱為“蒙古潮兒”,一是樂器的“潮兒”,一是演唱方法上的“潮兒”;而將流傳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潮爾稱為“阿勒泰潮兒”,即分為浩林·潮兒和冒頓·潮爾。[3](9-10)而在他隨后的研究中,又將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潮爾音樂分為浩林·潮兒、冒頓、潮兒、托克·潮兒、葉克爾·潮兒四種形態。[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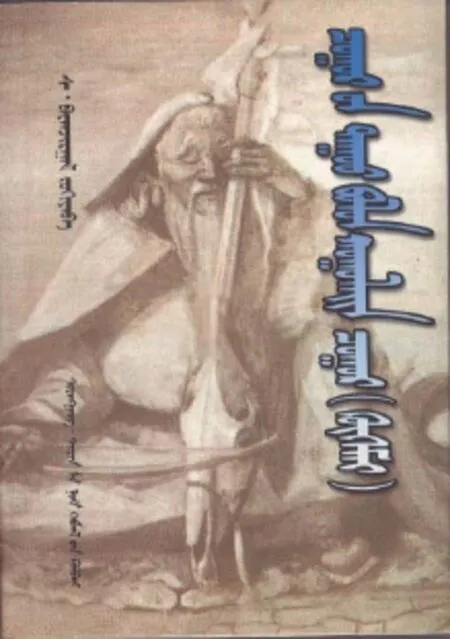
圖2 《潮爾歌及浩林潮爾(呼麥)》 書影
烏力吉昌首次對潮爾音樂進行系統分類研究。他把流傳在蒙古族民間的潮爾分為“烏他順潮爾”(一種類似馬頭琴的弓弦樂器)、“冒頓潮爾”(胡笳)、“浩林潮爾”(呼麥)、“潮爾音道”(潮爾合唱)等四類。其中,他把“潮爾音道”又分為察哈爾潮爾、科爾沁潮爾、阿勒泰潮爾三種。[15](21-28)上世紀九十年代,達·桑寶 著文對蒙古族潮爾音樂進行分類,指出“潮爾”是蒙古族多聲音樂的統稱,包括了呼麥·潮爾、冒頓·潮爾、潮爾(琴)、潮爾道四種體裁。
李世相提出,因歷史上北方草原多民族共存融合之故,對其語義產生了不同理解,因而有“潮爾樂器說”、“潮爾低音說”、“潮爾合唱說”、“潮爾和音說”、“潮爾共鳴說”諸種詮釋。前三種說法是針對事物的現象而言,后兩種說法是對事物本質的提示,尤其是最后一種“潮爾共鳴說”更為科學。他還根據民間的稱謂,認為,“潮爾”借助發音體的不同,有“吟、唱、吹、彈、拉”五種代表性的形式。包括浩林·潮爾、冒頓·潮爾、托布秀爾· 潮爾、烏他順·潮爾。[8](64)
博特樂圖將潮爾音樂分為包含人聲的和器聲的以及人聲與器聲相結合的等三種形式。其中,人聲演唱的潮爾,有一個人演唱的浩林·潮爾和多人合唱的潮林道兩種;樂器演奏的潮爾有弓弦樂器潮爾和托布舒爾;冒頓·潮爾和薩木·潮爾是人聲與器聲的結合形式。他認為,潮爾是一個體裁系列,這些體裁共同構成一個特定的多聲音樂模式,并表現在聲樂、器樂等領域,表現為單人演唱和多人合唱等表演形式。[9](17)瑟·巴音吉日嘎拉將潮爾音樂分為“潮爾”的“聲三種”和“潮爾”的“器三種”,其中,“潮爾”的“聲三種”分為,浩林·潮爾、呼麥、潮爾歌;“潮爾”的“器三種”分為冒頓·潮爾、托普·潮爾、葉克勒·潮爾。[16](119-120)李·柯沁夫將潮爾音樂分為:聲樂潮爾、器樂潮爾、跨界潮爾三大類。聲樂潮爾包括浩林·潮爾(呼麥)和潮林道;器樂潮爾包括弓弦潮爾——烏塔森·潮爾(又稱葉克勒)、撥弦潮爾——托布秀兒(又稱托普·潮爾);跨界潮爾,包括帶有人聲持續低音的管樂潮爾——冒頓·潮爾(胡笳)、帶有人聲和器樂雙重持續低音的火木思·潮爾(口簧,俗名阿門·潮爾)等。[10](27-34)
(三)關于潮爾音樂的產生及文化內涵
莫爾吉胡在《“潮兒”音樂之我見——試論阿勒泰蒙古音樂文化圈》[4]一文,詳細介紹了流傳在內蒙古地區的弓弦樂器潮爾和民間合唱潮爾同流傳新疆阿勒泰地區的四種潮爾形式的音樂形態、音樂內涵、特征與價值。根據他對蒙古古代音樂文化現象的考察、探索和研究,他將流傳在內蒙古地區以及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潮爾音樂視為“古代文明的殘存物”。他認為,大量的資料以及考察過程中反復接觸的事實說明“多納茨”現象肯定是存在的。他還認為,阿勒泰“潮兒音樂”是東方古代音樂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內涵豐富,特色鮮明,應該說,具有著區別于任何地區的古音樂文化特色,也是在整個音樂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雖影響很大而我們對其知之甚少或研究很少。”[17](4)關于潮爾音樂的淵源及產生問題,莫爾吉胡認為,阿勒泰的兩種“潮兒”到內蒙古科爾沁及錫林郭勒流傳的兩種“潮兒”,首先是源與流的關系......就是阿勒泰的兩種“潮兒”,從其演奏方法、音樂風格以及內容等等方面,都是內蒙古的兩種“潮兒”(不僅是“潮兒”,而且是今天的蒙古民間民族音樂)的源。其中,“浩林·潮兒”更是較早的古音樂文化范疇的音樂現象。其次,是古與今的關系。不能將阿勒泰“潮兒”與蒙古“潮兒”并列起來,盡管都存在于當今的社會條件(歷史時期)之下。從音樂內容、演奏(唱)手段,以及使用的樂器結構的不同,都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聯系,而他們事實上又有著質的差異,都屬于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3](10)
莫爾吉胡認為,“浩林·潮兒”應歸屬于人類早期的音樂文化范疇。比胡笳可能更早、更遠古一些。[18](22)莫爾吉胡在論文《“嘯”的話題》一文中介紹了有關“嘯”的史料,他認為,“浩林· 潮兒”有可能就是古代“嘯”的遺存物。他從史料中記載的“嘯”的藝術特征予以論證,“嘯”的結構式是由丹唇發出的“妙聲”同皓齒激出的“哀音”同時發出;其次,雙聲之間又有著和協的音程關系。即宮音與角音相協(三度關系),商音羽音狹雜徵音(五度、四度)關系;第三,二聲部結構的音樂自始至終運作在同宮系統之內(即自然大調式)。另外,他認為,“嘯”的另一個話題,也是不可忽略的話題,是否漢字在拼寫不同民族語言時存在著偏頗或錯誤。通過以上兩點問題,莫爾吉胡提出了質疑,“浩林·潮爾”和“嘯”是否是同一事物?[19](136-145)在隨后的研究中,針對這一問題不同的學者闡釋了不同的觀點。
烏力吉昌對潮爾音樂各體裁的起源進行了逐一討論。他通過文獻考證以及與古老英雄史詩中關于潮爾琴的描述,認為潮爾琴在元代之前便已產生。而通過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關于胡笳與冒頓·潮爾的比較與考證,認為胡笳就是冒頓·潮爾,早在公元195年前便已產生,它不僅在北方草原民族主義中有影響,而且由張騫從西域帶回中原后,在漢族當中也得以應用和傳布。關于潮爾道的產生,認為大約是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汗國的時候,而它的鼎盛時期是在明末清初。[20](21-23)達·桑寶著文對潮爾和呼麥的關系進行探討,認為潮爾的基礎是呼麥,而呼麥是潮爾音樂的一類。他認為,呼麥潮爾是潮爾多聲音樂,最早的形態;冒頓潮爾是在呼麥的基礎上,人聲與器聲結合的形式,屬于潮爾音樂發展第二個階段的產物;潮爾琴和潮爾道是潮爾音樂發展第三階段的產物,它們都以呼麥為其基礎。[21](197-203)
達·布和朝魯根據民間傳說以及蒙古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呼麥產生于深阿勒泰山,是早期蒙古人對自然界風聲、水流聲、山谷回聲的模仿模擬,在特殊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的民族,以她獨特的狩獵、游牧生產生活方式,使呼麥從自然界走入人類的生活并發展為人和自然界和諧共生的情感之聲。[22](77)新疆學者照·道爾加拉認為,蒙古人在夏日的炎熱時,往往用吹口哨來“招來涼風”,便是“齒哨”(?idün isgere),后為了與招喚遠處的人,吹更有力量、更具穿透力的“唇哨”(urulin isgere)。浩林·潮爾來自于“哨”,而冒頓·潮爾則來自于浩林·潮爾。[23](193-194)蒙古國呼麥藝術大師敖都蘇榮著文指出,呼麥與蒙古人的生產生活有關。早先,蒙古人打獵時候,用呼麥模仿各種動物的聲音進行誘捕,游牧時代卻用呼麥為母畜勸奶。擠壓音、哈日嘎呼麥、潮萊呼麥,同時也是蒙古薩滿神歌演唱經常使用的方法。成吉思汗時期,黑蘇勒德、白蘇勒德出陣時,都要以呼麥形式唱頌特定的歌曲。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后,哈日嘎·呼麥用于佛教誦經。但認為,伊斯若·呼麥卻被認為聲音使“心性不穩”,故不用于誦經。1980年之后,呼麥在蒙古國大面積流傳開來。[24](192-193)蒙古國學者、馬頭琴演奏家桑達格扎布支持了呼麥是阿勒泰蒙古人對自然聲音的感受和模仿當中產生的觀點,并與薩滿、英雄史詩、烏力格爾進行比較,指出呼麥同時也是這些體裁中經常運用的演唱技法。[25](39-61)
唐代學者孫廣(生卒年不詳)在公元八世紀后半葉撰寫的《嘯旨》是我國唯一的一部關于長嘯藝術的專書。范子燁的《論<嘯旨>——中國古代呼麥藝術的教科書——嘯史鉤沉之一》[26](66-93)一文,便是對這部篇幅短小的著作也是以往文化界和學術界未能破解的“天書”之一的《嘯旨》進行的解讀和引申研究。他首先對《嘯旨》的作者孫廣及《嘯旨》編撰的文化背景進行探索,認為《嘯旨》的文化淵源是道藏,即孫廣以前的道教文獻,孫廣是相關文獻的編纂者和整理者,而非純粹的原創者。繼而認為“長嘯”與“學道”是相輔相成的,因為長嘯本身就是道教徒的一種修身養氣之術,從根源上說,嘯脫胎于大自然的音響。他還認為,《嘯旨》的編纂是建立在道教文化的背景之上的。長嘯與呼麥的兩個契合點,即道教的聲音法術與原始的薩滿巫術,中土道士的呼吸吐納與游牧民族的呼麥藝術之密合無間。進而認為這是我們確認“長嘯即呼麥”這一事實的第一個文化視角。接著,他從“一聲能歌兩曲”這一基本視角來談,《嘯旨》中的長嘯與呼麥在音樂形態上的同一性。他認為,在音樂形態上長嘯與呼麥的吻合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五聲音階的調式特征,一口氣旋律與拖腔的吟唱特征以及二重音樂織體的結構特征。二者在以上三個方面是相同的,從而進一步論證了長嘯與呼麥等同的觀點。他還認為,長嘯的發聲方法與呼麥的發聲方法是完全相同、完全一致的,這主要表現在“縮喉”與“反舌”是長嘯與呼麥共同的發聲方法原理。
趙磊通過浩林·潮爾與人類歌唱史中“嘯”的比較,認為,浩林·潮爾這種演唱形式在文化人類學中具有特殊意義。它是人類幼年時在人聲呼號中引發出的泛音旋律,以抒發內心情感的一種自娛性“歌唱”,應屬于人猿揖別之際。[27]格日勒圖認為,呼麥的歷史甚至比蒙古族本身的歷史還要長,早在兩漢、三國、魏晉時期,便有漢族文人學唱北方民族呼麥藝術——稱曰“嘯”。[28](66)李·柯沁夫認為,被中外音樂學界誤認為嘯樂的“口哨”、“葉嘯”和“指嘯”,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浩林·潮爾(嘯樂)“帶有持續低音的復音音樂”這一特征,因此,不屬于潮爾音樂體系范疇,或是潮爾音樂的一種變異。[10](35)
范子燁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1月23日)上發表的《呼麥藝術的鼻祖:對興隆溝紅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樂學解讀》一文中,根據自己所熟悉的史料以及對蒙古民族音樂藝術傳統的了解,對5300多年前興隆溝出土的一尊陶像的動作表情進行解讀,認為陶像并非是在用力呼喊的狀態,而是正在縱聲高歌的狀態,而且,這不是普通的歌唱,而是至今仍然在蒙古高原上流傳的呼麥藝術。[29]他還認為,呼麥大致與“豹齒,虎尾而善嘯”的西王母處在同一時代。這位“呼麥鼻祖”重現于蒙古高原,很自然地將我們關于蒙古民族起源的歷史視野拉到遙遠的史前時代。[30]他從音樂史層面來看,認為,人類文化可能有一個呼麥的時代,早于人類所有的音樂形式,因為呼麥發聲自然,屬于“自然純正律”,是我國古代三分損益律和西方十二平均律的原型。從呼麥與古代文獻中“嘯”的關系和呼麥的歷史等來看,這尊史前陶人的文化價值并不僅僅局限于美術史和宗教史層面,更在于音樂史層面。[29]莫爾吉胡的《呼麥終端探源之佳作——評談<呼麥藝術的鼻祖>》是這篇論文的解讀和引申。他認為,范子燁對陶像動作表情的正確解讀,證明了呼麥在久遠的人類童年時期便已存在。進而他再次強調古文化研究領域內多納茨觀點、多納茨方法的重要性,提出文化爆炸現象所造成的古文化的裂變特質,使人種、種族或具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以及操不同語言的族群之間的融合現象。多納茨現象告訴我們,民族古代文明與文化并非永遠只遺存在本民族中,而在遙遠的他國他民族中,常常遺存另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這就要求我們跨地域的限制去發現。[31](1-2)
關于呼麥(浩林·潮爾)的產生問題,除了前面談到的“浩林·潮爾就是古代嘯的遺存物”這一觀點外,學界還持有不同的觀點。一是與藝術起源說的關系,一是體現在與原始薩滿教之間的關系。達·桑寶認為,起源于阿勒泰山的額和爾河,在流過一山間時發出一種奇特美妙的聲音,古人就模仿其聲音創造出了“浩麥”。[8](65)呼格吉勒圖認為,這一傳說表明了古代蒙古人由模仿大自然聲音而發展為移情化的一種藝術發展觀;也反映了浩林·潮爾這一古代蒙古音樂形式在古代蒙古人思想意識中已有了多聲音樂的概念這一事實。[7](454)烏蘭杰認為,從呼麥產生的傳說,以及曲目的題材內容來看,“喉音”這一演唱形式,當時蒙古山林狩獵文化時期的產物。[2](173)他還認為,其產生發展和成熟與原始薩滿教有密切關系......呼麥藝術的歷史十分悠久,早在東湖、匈奴時期,即已在蒙古高原上廣泛流傳。由此可知,根據海岸條石共鳴而創造呼麥藝術的古代民族,無疑是東胡、匈奴......薩滿教巫師便刻意用嗓音加以模擬,遂創造出呼麥藝術......薩滿教音樂中的多聲部音樂形式——呼麥,其產生的歷史要比單聲部音樂早得多。[32](4-6)范子燁[29]持有相同觀點。李·柯沁夫認為,不論何種傳說解釋,均反映了浩林潮爾是遠古山民模仿大自然聲響而創造的神奇的喉音藝術。他還認為,潮爾藝術是原始人類音樂文明的活化石,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性,而且以其高度的歷史學、民族文化學、文化人類學價值,從而成為無比珍貴且具有無限潛力的人類文化藝術遺產。[10](27)
然而,在潮爾藝術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地區的潮爾體裁形式有著怎樣的聯系?莫爾吉胡認為,從內蒙古流傳的“潮兒”合唱、嘯兒、奚琴、馬頭琴追溯到新疆阿勒泰山中,至今保留的四種形態的潮兒音樂,使我們清晰地感知到:它們之間不但有著橫向的聯系,更是有著縱向的源與流的脈絡關系。阿勒泰潮兒音樂,無論是樂器形制,音樂所表述的情趣,音樂語言構成的特色以及調式思維的古老形態,都證明了所應歸屬的年代是極為遙遠的年代。[17](1)他還認為,由于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災害,或者是戰亂所帶來的顛沛流離,使得古代傳統文化藝術(包括“潮兒”音樂),隨同解體的民族流散到四處,甚至會發生這樣有趣的現象:某些藝術、文化在此處早已失傳甚至銷聲匿跡,然而在遙遠的他處卻至今保留著。這種現象,在古代文化研究中所無法回避的Doughnuts現象?!大量的資料以及考察過程中反復接觸到的事實說明“多納茨”現象肯定是存在的。[4](3)因此他提出,可將內蒙古地區以及新疆阿勒泰地區的潮爾音樂視為“古代文明的殘存物”,[4](3)而阿勒泰的潮爾與蒙古潮爾屬于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而浩林·潮爾是內蒙古兩種潮兒的源,其中浩林·潮爾更是較早的古音樂文化范疇的音樂現象。[3](10)
呼格吉樂圖認為,浩林·潮爾的產生比冒頓·潮爾更為古老。可為我們提供如下線索:首先,浩林·潮爾呼嘯的持續低音的上方所構成的泛音音列樂風的結構,為了解并研究蒙古族古代音律及人類早期調式理論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第二,從這一珍貴的呼嘯音響可以了解到古代奇妙的聲源;第三,可以推測,人類發現泛音的歷史是很早的;第四,除了已被證實的人類早期音樂起源說——粗狂的、集體娛樂性質的或祭祀性的集體藝術(如哼嗨式的勞動號子、擊石發聲及百獸率舞)之外,浩林·潮爾也是研究和了解原始音樂的不可忽視的藝術形式。從浩林·潮爾的原始性和自然性可以看出,該音樂形態早已有之。
李世相認為,“浩林·潮爾”至“冒頓·潮爾”的演變,可謂是人類對自然規律認知過程的次“質”變,蒙古祖先已懂得了利用精巧的工具——樂器,來表達人聲難以達到的藝術境界。從“冒頓·潮爾”的人聲吟鳴與管上取音的表現方式來看,此時的共振體是人聲與器樂的混沌狀態,雖然在后續發展中已有了“聲”、“器”分離取向,但仍缺少器樂獨立性(指發聲方式)。從吹奏樂器“冒頓·潮爾”至“火不思”彈撥樂器出現,是蒙古族祖先在利用工具(樂器)表達情懷方面的又一次飛躍。繼彈撥樂器之后,弓奏樂器的出現與發展,更使“潮爾”的二重結構影響實現變得方便而有效。浩林·潮爾——潮林道——烏日汀道(長調)三者間有著非常近的血緣關系,而浩林· 潮爾中的“潮爾”觀念則是具有遺傳基因意義的因素。而它又對蒙古族調式觀念的形成與確立,有著深刻的影響。[8](65-68)
烏蘭杰通過對浩林·潮爾與口簧、浩林·潮爾、抄兒琴(潮爾琴——筆者注)英雄史詩、浩林·潮爾與潮爾·道和浩林·潮爾與胡仁·烏力格爾以及浩林·潮爾等一系列體裁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辨析,找出之間的親緣關系、依附關系、從屬關系等,進而將此與漢族傳統音樂進行比較研究,從而論述了原生態浩林·潮爾藝術的廣泛輻射作用。他認為,作為古老的音樂形式,呼麥對蒙古族的其他傳統音樂形式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另外,氐羌、匈奴、鮮卑、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將呼麥帶入了中原漢族地區,從中國傳統音樂的情況來看,至今可以看到呼麥影響的明顯痕跡。[32](3-14)
巴音吉日嘎拉認為,先是發現了“潮爾”,然后才發展了它的聲、器樂藝術系列。蒙古族“潮爾”系列藝術“發音”的先后順序應該是聲樂類在前,器樂類隨后。[16](119)喬玉光認為,原始形態的呼麥(浩林·潮爾),主要的社會功用有二:一是作用于生產領域——吸引獵物、捕捉獵物、勸奶等與狩獵經濟和游牧經濟相關的實踐,這種遺留在內蒙古的山林和草原民族中,至今依然可尋;二是引用于宗教領域——在宗教儀式中,用呼麥(浩林·潮爾)強調宗教氣氛,并將之作為人與自然宇宙溝通的媒介與手段。古代蒙古族信奉薩滿教,呼麥是薩滿教儀式的組成部分;在崇信喇嘛教后,呼麥(浩林·潮爾)成為喇嘛誦經的重要方法,這一誦經方法被稱之為“堪布潮爾”,至今內蒙古的喇嘛寺廟中仍可聽到。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呼麥(浩林·潮爾)的進一步成熟,呼麥(浩林潮爾)更多地弱化或脫離了原始的功用,或者說進入了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成為蒙古民族的主要的代表性藝術形式。[33](76-77)博特樂圖認為,我們很難說明作為體裁的“潮爾——呼麥”在先,還是作為附著形態的“潮爾——呼麥”唱法在先,然而大量的事實證明,作為一種體系化的演唱技法,“潮爾——呼麥”唱法著實廣泛存在于民間,成為一個體系,完整、流傳廣泛的技藝系統。在中國,“潮爾——呼麥”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民間傳承。它不僅表現出統一的模式化類型特征,也因地域、部落、時代而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個性特征。[9](19)關于呼麥藝術的發源地,烏蘭杰認為,呼麥藝術的歷史十分悠久,早在東湖、匈奴時期,既已在蒙古高原上廣泛流傳。由此可知,根據海岸條石共鳴而創造呼麥藝術的古代民族,無疑是東胡、匈奴。他認為呼麥藝術的發源地,并不是阿勒泰山鄂畢河峽谷,而是南古力斯克島海岸山崖西伯利亞地區的廣闊空間。[32](5)
關于呼麥藝術的分布的歷史與現狀問題,烏蘭杰認為,綜觀蒙古高原地形圖,東部的大興安嶺,西部的阿勒泰山,以及北部的薩彥嶺,三面包圍著蒙古高原中心地帶,形成一條巨大的馬蹄形,構成“浩林·潮爾”分布的中心地域。從歷史上看,屬于“林木中百姓”的幾個蒙古部落,諸如不里牙惕人(布里亞特)、斡赤剌惕人(衛拉特)、禿馬惕人(圖瓦),他們長期保持著薩滿教信仰,以及“浩林·潮爾”的古老音樂傳統,看來不是偶然的。自13世紀以來,斡亦剌惕(衛拉特)、烏梁海部落已經離開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向西遷徙至阿勒泰山一帶游牧。但依舊保持著祖先的“浩林·潮爾”的音樂傳統。至于歷史上的圖瓦部落,生活區域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故保留“浩林·潮爾”的音樂遺產最為豐富,形成新的“呼麥”藝術中心地區。[32](7)
注釋:
①本文圖片來源于作者本人收藏,吳·斯日古冷拍攝。
[1]莫爾吉胡.“潮兒”大師——色拉西[J].草原,1962(5).
[2]烏蘭杰.蒙古族音樂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莫爾吉胡.追尋胡笳的蹤跡——蒙古音樂考察紀實二[J].音樂藝術,1986(1).
[4]莫爾吉胡.“潮兒”音樂之我見——試論阿勒泰蒙古古音樂文化圈(上)[J].音樂藝術,1998(1).
[5]莫爾吉胡.“浩林·潮兒”之謎[J].音樂藝術,1987(2).
[6]趙·道爾加拉、周吉.托布秀爾和楚吾爾曲選[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7]呼格吉勒圖.蒙古族音樂史[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
[8]李世相.“潮爾”現象對蒙古族音樂風格的影響[J].中國音樂學,2003(3).
[9]博特樂圖.“潮爾——呼麥”體系的基本模式及其表現形式[J].中國音樂學,2012(2).
[10]李·柯沁夫.蒙古族潮爾藝術及其世界意義[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11]代興安.大自然與人體樂器——關于潮爾名稱的來源[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12]徐欣.草原回音:內蒙古雙聲音樂“潮爾”的聲音民族志[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4.
[13]柯沁夫.“潮爾”漢語音譯的規范問題[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09(2).
[14]布林.潮爾釋辨[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15]烏力吉昌.潮爾初探[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1989(2).
[16]瑟·巴音吉日嘎拉.“浩林·潮爾”與“和聲學”之比較研究[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17]莫爾吉胡.“潮兒”音樂之我見——試論阿勒泰蒙古古文化圈(下)[J].音樂藝術,1998(2).
[18]莫爾吉胡.“浩林·潮兒” [J].音樂藝術,1987.
[19]莫爾吉胡.“嘯”的話題[a].追尋胡笳的蹤跡——蒙古音樂考察紀實文集[C],2007.
[20]烏力吉昌.潮爾初探[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1989年2期,21—23頁。
[21]達·桑寶.關于“潮爾”[A].(蒙文),C·巴音吉日嘎拉.潮爾歌及浩林·潮爾[C].(蒙文),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
[22]達·布和朝魯.喉音藝術——呼麥初探[J].內蒙古藝術學院學報,1992(1).
[23]道爾加拉.論阿勒泰烏梁海之“浩林·潮爾” [A].(蒙文),莫爾吉夫等.蒙古音樂研究[C].(蒙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24](蒙古)巴·敖都蘇榮.呼麥起源初探[A].(蒙文),C·巴音吉日嘎拉.潮爾歌及浩林·潮爾[C].(蒙文),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
[25](蒙古)瓦·桑達格扎布.蒙古呼麥藝術——歷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基礎[M].(蒙文),烏蘭巴托市,2010.
[26]范子燁.論<嘯旨>—中國古代呼麥藝術的教科書——嘯史鉤沉之一[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A]. (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27]趙磊.嘯與浩林潮爾[J].草原藝壇,1996(1)
[28]格日勒圖.呼麥藝術初探[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07(2).
[29]范子燁.呼麥藝術的鼻祖:對興隆溝紅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樂學解讀[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11/23,B04.
[30]范子燁.蒙古呼麥的藝術傳統與蒙古史前史重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8/20, B02.
[31]莫爾吉胡.呼麥終端探源之佳作——評談《呼麥藝術的鼻祖》[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32]烏蘭杰.關于“浩林·潮爾”——蒙古族嗓音藝術的幾點感悟[A].中國呼麥暨蒙古族多聲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會議文集內部資料),2013.
[33]喬玉光.“呼麥”與“浩林·潮爾”:同一藝術形式的不同稱謂與表達——兼論呼麥(浩林·潮爾)在內蒙古的歷史承傳與演化[J].內蒙古藝術,2005(2).
【責任編輯徐英】
Centuries Research on Mongolian Music (PartⅦ)
Boteletu1, GUO Jing-jing2
(1.Art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2.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J609.2
A
1672-9838(2016)01-121-09
2016-01-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蒙古族傳統音樂的保護與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3JJD760001)階段性研究成果。
博特樂圖(1973-),男,蒙古族,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庫倫旗人,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內蒙
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郭晶晶(1982-),女,達斡爾族,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族自治旗人,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