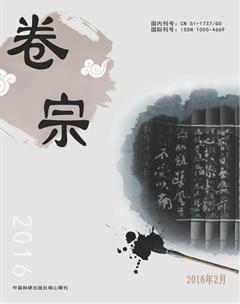從企業商標戰略看“微信”商標案
摘 要:2013年5月,創博亞太科技以騰訊微信涉嫌侵權發明專利為由,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將騰訊公司告上法庭,但卻因為違反“微信”商標注冊法而最終敗訴。該案件也引起了社會企業界、商標界以及法律學術界的一片嘩然,更因其受眾面廣泛而牽動了眾多社會公眾的視線與神經。如何看待這場創博亞太與騰訊的知識產權之爭,本文將從企業商標戰略與法律角度來著重審視分析。
關鍵詞:微信商標;知識產權糾紛;企業戰略;法律案件;騰訊;創博亞太
2011年10月,創博亞太有限公司率先對“微信”文字商標進行了注冊,而且該公司稱已經在微信業務中加入了包括“附近的人”、“微信公眾賬號”等功能,相對完整的為用戶提供包括黃頁電話簿和用戶位置信息的全部技術特征。但在兩年后創博亞太對騰訊公司的商標搶注侵權訴訟卻以“專利復審無效宣告”而敗訴。更讓創博亞太心寒的是,騰訊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改變專利權有效這一決定并被予以認可。最后,法院判定撤銷專利復審委員會的維持專利權有效決定,對微信商標進行重新審查決定。2015年2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創博亞太上訴請求,判定微信商標權歸騰訊所有。
1 基于企業商標戰略的案件探究
近年來,我國社會企業開始實施“自愿注冊原則”,未經注冊商標允許在商品或服務中直接使用。但企業必須首先明確一點,雖然可以使用商標權限,但在未注冊狀態下使用商標是存在巨大隱患的。創博亞太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它引起了社會公眾及法律界的思考。
雖然騰訊公司在微信商標案中勝出,但實際上騰訊自身也曾經受到過同樣的遭遇,早在1997年,騰訊公司就開發了符合中國用戶習慣的及時通訊軟件OICQ,這也是我國第一個在功能方面比較全面的即時通訊軟件,實現了信息收發、網絡呼叫、傳輸文件等功能,但在2001年被奇瑞公司起訴,在隨后長達11年之久的QQ汽車商標爭奪戰中以失敗收場。所以這一次,騰訊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過來人”,對微信商標的注冊本應該提前謀劃布局,但實際上騰訊卻再一次被一塊石頭絆倒,沒能為這一“備用商標”提前注冊,也沒有與公司字號“騰訊”綁定,騰訊對商標監查的嚴重失位也就導致了這一次法律爭端的出現。從企業商標戰略角度講,騰訊既沒有按照辦理注冊人名義來進行商標的有償轉讓,也沒有對商標實施更換或重新注冊,更不曾對商標公告后提出異議。因此這樣看來,創博亞太是沒有任何過錯的,他們先于騰訊一步注冊申請微信商標也沒有任何異議,反而是騰訊在企業戰略上一錯再錯,那為什么最后為商標知識產權爭端買單的依然還是創博亞太?應該考慮從企業商標戰略的法律層面來審視這一事件[1]。
2 基于企業商標戰略法律層面的微信商標案糾紛分析
(一)關于“絕對禁用條款”與微信商標
在《商標法》的第十條第一款中就規定了某些標志是不得用于商標使用的,因為它們都是商標禁止使用的內容,也是商標審查的基本標準。具體來說,對“絕對禁用條款”的解讀可以總結以下三點。
首先,所謂被審查的“標志”,其本身是否有予以禁止作為商標的具體理由;其次,如果具有此類理由,那么該“標志”是否具備任何人都不得將其作為商標使用的權限,更不能將其作為“注冊商標”使用;最后,在《商標法》中給出了“但書”這一概念,例如該法律條例中的第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中就明確指出“同外國的國家名稱、國旗、國徽等等相同或相似的“標志”也不能被作為商標,除非得到國家政府的同意。”
(二)“微信”商標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依據《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規定中指出“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志不得作為商標使用。”這一條例就可以被應用于騰訊與創博亞太的“微信”異議爭端案件中。而最終的終審判決也表明,創博亞太的“微信”商標使用對社會、對騰訊是存在“不良影響”的。
關于“不良影響”在法律上還被稱為“兜底條款”,此類條款一般都是較為抽象的,它并沒有具體的判定標準,而是完全基于社會生活發展的復雜特性來給出標準的。所以說,此商標案件的不良影響不能用“窮舉法”來解釋,因為它無法安全給出所有不良影響所造成的所有情況。不過利用“兜底條款”依然可以對某些法律屬性劃出相關界限,并判斷該條款是否可以被適用于騰訊與創博亞太的這起“微信”商標案中[2]。
(三)“微信”商標案涉及“特定用戶群體”
在本案件中,“微信“的使用涉及大量消費者群體,它的糾紛就在于混淆了廣大消費者群體或干擾了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其并非是與騰訊公司的企業利益相抵觸,所以說該案件所涉及的是公益而并非私益,它也是適用于不良影響這一條件的前提。
具體來講,企業在市場上使用任何商標都應該針對于不同的特定用戶群體和企業用戶,這里就形成了一個以商標為紐帶橋梁的“利益共同體”,它促成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行為,所以客觀來講,“特定用戶群”與“利益共同體”之間是不存在本質區別的,只是在數量方面存在差異。可以說,關于此次“微信”的商標糾紛,確實觸及了創博亞太和騰訊這兩個“利益共同體”,它不是針對某個個體企業利益的單純性抵觸,其呈現的應該是商標糾紛案件中所慣有的常態。但在本案中,它卻被認定是屬于公益而非私益的,這也是創博亞太感覺不服的地方,因為它既沒有任何官方的法律認定標準,也沒有確切的法律依據。
(四)從企業專利意識層面看“微信”商標爭議
對創博亞太和騰訊兩家企業而言,他們在創業初期都經歷了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他們的創始人侯萬春和馬化騰都是以專利發明起家的,對早期專利申請具有豐富的操作經驗,對通信技術領域具有很深刻的了解與認識。雖然在專利申請上,侯萬春的77件遠遠高于馬化騰的11件,但是在此次“微信”商標爭奪中,侯萬春和他的創博亞太卻甘拜下風,這不由讓人質疑,是否是小公司縱使有再大的夢想,在遇到騰訊這樣的大企業后都要成為炮灰?因為在終審判定中也提到,由于改名而造成廣大用戶混淆認識的創博亞太在與騰訊后期推出的“微信”品牌相互混淆,從而對廣大用戶造成了較為消極與負面的嚴重影響,所以為了保護廣大用戶切身利益,不能將“微信”商標裁定給創博亞太。因此從企業商標戰略和社會影響角度來看,本案的判決結果是有待商榷的。原本在《商標法》中的絕對禁用條款卻成為了鼓勵騰訊使用未注冊商標的積極條款。對創博亞太而言,看到騰訊在使用未注冊商標所存在的風險而積極搶注,待注冊成功后再使用“微信”商標,這種思路不但無可厚非,還非常值得推崇,但是由于在市場銷售與企業商標戰略層面的失誤,卻讓他們錯失了“微信”這樣一個金字招牌,甚至連商標異議提出的機會也不復存在。所以綜合來看,該案的判決顯然偏離了《商標法》立法的本質內涵[3]。
3 總結
總而言之,創博亞太在“微信”商標方面的企業策略實施是有待考量的,而騰訊雖然贏了這一戰,但他們冒風險使用未注冊商標,第二次犯錯的行為也不值得提倡。更重要的是,該案的最終判決卻以改變商標立法初衷為判定條件,這種判決結果是不利于國家及企業制定和實施企業商標戰略的。所以可以見得,我國《商標法》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還有待完善,避免這種“不良影響”的再次出現,而使用未注冊商標被搶注的教訓也足以敲響業界警鐘,更加重視未來的企業商標專利發展戰略部署。
參考文獻
[1] 付丹.淺議“微信”商標紛爭背后的反思[J].法制博覽,2015(15):285-285.
[2] 姚泓冰.“微信”商標紛爭背后的反思[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5):87-89.
[3] 王好.未注冊商標“搶用”問題的規范分析——以指導案例30號為例[J].政治與法律,2015(4):78-89.
作者簡介
錢繼善(1980-),男,漢族,湖北赤壁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商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