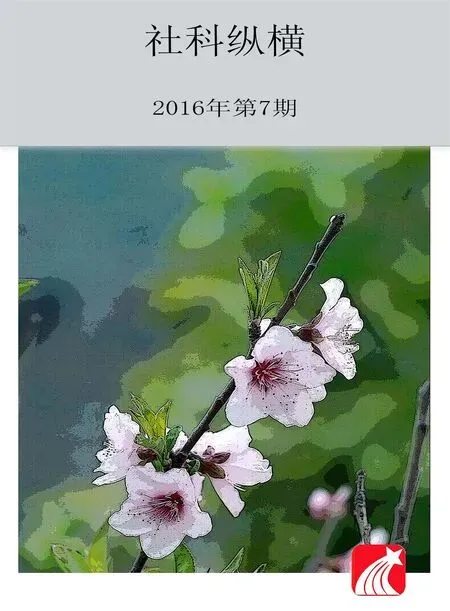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影響研究綜述
藍英
(川北醫學院管理學院 四川 南充 637007)
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影響研究綜述
藍英
(川北醫學院管理學院四川南充637007)
區域經濟(產業)發展決定著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又反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級階段演進。國外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結構(經濟)研究結論主要有工資勞動簡化法、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丹尼森的經濟增長多因素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實踐上主要注重教育結構的改革完善,強調向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傾斜。而國內大部分研究仍集中于對高等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研究,定量研究上表現為借鑒國外成熟的一些定量分析模型和方法,缺乏對模型進行創新。現有文獻對高等教育結構的分類一般有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類別結構、層次結構、布局結構和體制結構。只分析某一種或幾種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關系研究成果較多,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關聯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少。
高等教育結構產業結構人力資本經濟增長
一、引言
區域產業結構是指在一定經濟空間內的產業構成和諸產業間質的聯系及量的比例關系,區域經濟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演進。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庫茨涅茨的理論揭示了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基本發展趨勢是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等非農業部門轉移。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也表明,產業結構的調整會帶來勞動力結構和技術結構的變化,進而引起勞動力就業產生新組合,這必然會對需求的人才帶來數量與結構上的新要求。高等教育是國家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搖籃,其社會職能決定了其必須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供給。也就是,區域經濟(產業)發展決定著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又反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級階段演進。
二、國外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影響研究現狀
國外研究產業結構與教育主要圍繞著兩條主線展開:其一,論述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他們主要研究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采用的模型和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一是1924年前蘇聯經濟學家斯特魯米林提出的“工資勞動簡化法”,該法認為要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需要把教育所形成的復雜勞動按一定標準或尺度折合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二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1959)在《人力投資——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文中闡述的人的素質對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教育投資收益率的估算方法。三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丹尼森(1960)根據歷史統計資料,運用獨特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法對經濟增長水平進行實證分析,從而創立了“經濟增長多因素分析法”,該方法也被認為是計算教育經濟收益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四是20世紀末,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和數學家柯布在研究美國1899年—1922年制造業領域勞動和資本對生產的影響時,得出的生產函數即Y=AKαLβ該函數目前仍然是計量教育對經濟發展貢獻方面較為主要和權威的方法。后來羅伯特·盧卡斯(1988)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索洛的技術進步概念和羅默的知識積累結合起來,具體化為“專業化的人力資本”。
其二,研究明確了教育對個體而言的持續性,側重于教育結構的改革完善,加強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比重,強調終身教育的重要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指出:“終生教育只不過是成人教育的一種新術語,這種教育思想己逐步應用于職業教育。”日本學者天野郁夫(1986)分析了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公民辦教育滿足國家和社會不同類型的人才需求。Geoffery·Tabbron(1997)在《發達國家中技術職業教育培訓與經濟發展的關聯》一文中指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必須重視職業教育,主動將職業教育與產業調整結合起來。在實踐層面,日本二戰后采取的“互補型”辦學模式和德國的“雙元制”等都是一些比較成功的職教實踐模式。
三、國內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影響研究現狀
國內研究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影響作用始于改革開放,盛行于21世紀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特別是近十年來,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關注度與日俱增,大量文獻發表見諸報端。通過在中國期刊網2005—2014年公開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檢索發現,國內學者從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現為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關于高等教育結構分類維度上,有只研究某個或幾個維度與產業結構調整影響關系,也有研究多個維度與產業結構調整影響關系。
(一)理論角度研究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影響
丁繼勇(2006)以我國1952—2003年三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教育結構的數據試圖驗證配第—克拉克定理。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與教育結構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系,并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在前工業化時期,受教育的人數和層次都處于較低水平;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完成中等教育的人數增長速度與二三次產業的增長速度保持同步”。朱宏飛等(2007)指出“高校完善的學科建設要以產業發展為導向,學科建設需與產業結構的發展保持動態平衡”。谷建春等(2008)以湖南省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為例研究認為,“區域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具有相關性,因此培養人才的高等教育必須根據產業結構調整趨勢進行自身結構上的優化”。楊曉明(2008)分析認為“當前我國農業高等教育存在著結構趨同、盲目擴張和學科專業設置不合理等問題,在學科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為促進農業高校類型結構合理,并走出一條創新之路,應構建農業高等教育多層次、立體化結構,塑造農業高等教育特色科類結構,發展多樣形式結構的農業高等教育”。劉瀑(2010)以河南為例研究了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與高等教育發展的相互影響,并認為“高等教育是以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為支點,優化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高等教育發展格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及人才培養模式,以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縱觀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都承認產業結構決定高等教育的專業和學科結構。同時,高等教育結構的優化必須服務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且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及學科建設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二)實證角度研究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影響
近十年來,國內大量的定量實證研究集中在區域經濟與教育互動關系的領域,研究方法表現為借鑒國外既有的一些模型方法如工資勞動簡化法、丹尼森因素法、柯布-道格拉斯函數模型,利用ADF、協整分析和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法驗證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邏輯關系,研究結論可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對人力資本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和優化產業結構理論的實證研究。這方面研究結論非常豐富。
解呈(2005)借鑒了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和教育類似于出口的思想,分析面板數據得出我國高等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0.13%的結論。胡劍鋒等(2007)選取了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e)、農業機械總動力(M勞動投入)、農村實有耕地面積(S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F資本投入)幾個投入量,以農業總產值為產出量,考慮到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與農業總產值之間并非線性關系,將其以指數形式進入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即Y=AertMaSbFc,并分析了浙江省農村教育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結果表明:“農業機械總動力、化肥使用量對浙江省農業總產值的影響不大,農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實有耕地面積和勞動力文化程度,基于耕地為不可再生資源”,得出“加強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是促進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的結論。趙鎮(2008)借鑒崔玉平博士的勞動簡化系數,用丹尼森因素法測算了1997—2006年間我國某省高等教育對經濟的影響,繼而與國外數據比較分析得出“某省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較低”的結論,并提出了“必須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促進高等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性建議”。
孫敬水等(2008)建立人力資本評價體系,通過建立模型,論證了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得出結論:“浙江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其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資資本的產出彈性,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要大于物質資本,簡單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為負值,簡單勞動力已經處于過剩或飽和狀態”。張曉秋、冉茂盛等(2009)首先估算出中國1997—2005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根據中介效應模型理論認為:“教育投資、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之間存在類似的中介效應關系”。最后得出“成人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直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改善,還通過提升人力資本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改善”。張芳玲(2011)利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和綜合評價法就重慶市2002—2007年間教育對經濟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重慶市教育對其他部門的影響雖然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但其影響呈遞增趨勢,也就是教育對經濟影響越來越大”。何菊蓮等(2013)運用我國2000—2009年的面板數據,構建了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測評的指標體系,對我國高等教育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狀況進行測度后得出結論:“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不同學者選取的樣本不同,研究方法各異,但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教育投資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第二,教育(高等)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的適應性研究。
姚益龍等(2005)以中低收入的中國、中高收入的巴西、高收入的美國等國家為例,證實了“各國教育對經濟的積極影響,教育與產出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且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正的非線性相關”。龐資勝(2006)從1978—2002年我國教育投入和經濟增長數據入手探討了我國教育規模效應對經濟的影響,再以江蘇和江西為代表論述了教育的結構效應對經濟的影響,強調“不同層次的教育應該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條件相適應”。王萍等(2007)通過SPSS軟件,采用主成分和回歸分析方法研究了四川省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認為“四川省高等教育各學科基本適應四川省經濟發展”。高耀等(2013)通過2000和2010年我國十大城市群相關經濟和教育指標體系,運用因素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度后得出結論:“整體而言,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非常顯著,但貢獻度隨時間推移有所下降。長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為‘雙領先型'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為‘雙落后型'城市群”。
這些學者的研究都得到結論: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大小與一國(區域)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關。特別是龐資勝和高耀他們的研究,印證了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大小與區域經濟發展階段成正相關,區域經濟越是發展,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越大。長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經濟較我國其他城市群經濟發達,處于較高的發展階段,教育對該城市群貢獻率也大些。
第三,將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大小作各省市或者中外對比研究,或者將各層次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進行對比研究。
劉睿(2006)則將重慶1990—2000年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與其他省市進行對比發現,四川和重慶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低于同期的北京、上海和天津,提出“要提高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還需創新人才留住機制”,這正是重慶和四川教育對經濟貢獻率較低的重要原因,“人才吸引機制低效,本地培養的高層次人才流失加劇”,外出求學畢業的學生不愿回到本地工作。李雯(2006)等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基礎上構造教育投入的勞動增長型生產函數,實證分析發現“1990—2000年中國教育對GDP貢獻率為5.69%,其中高等教育對GDP的貢獻率為2.035%,相當于美國1950—1973年的水平”。同樣,張立新等(2008)運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測算出東北“黑、吉、遼三省1990—2005年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分別為1.4%、1.25%和1.55%,均處于較低的水平”。武凌(2010)將四川省1996—2008年間研究生、普通本科生和普通專科畢業生人數與三次產業發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四川省研究生對第二產業發展貢獻最大,普通專科畢業生對第三產業發展貢獻最大,而普通本科畢業生對三次產業發展貢獻并不明顯”。陳晉玲(2013)首先從教育的層次結構和布局結構入手研究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作用發現,“第一,全國中等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最為顯著,高等教育次之,初等教育最小。第二,各層次教育對經濟影響作用大小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一是東中部地區各層次教育對經濟增長明顯,而西部最弱;二是東部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影響最大,中等教育次之,初等教育最小;西部地區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大,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小。看來,東中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對高學歷人才的吸引力很大,所以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最大。西部地區則相反,長期輸出人才,對高學歷人才的吸引力很弱”。
總之,不同學者選取不同年份跨度數據,實證研究了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增長之關系。絕大多數研究結論認為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基本吻合,對經濟增長也起到了相應的促進作用。但也有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論。如陳晉玲(2012)以J省為例,利用1985—2009年時間序列數據對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J省高等教育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作用機制,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了J省的經濟增長;但J省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不相適應,一是J省高等教育層次結構不盡合理,二是按產業結構主動調整專業設置的有效機制尚未形成”。
(三)從高等教育結構分類及指標選擇角度研究結果總結
從現有文獻看,學者們對高等教育結構的分類一般有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類別結構、層次結構、布局結構和體制結構。多數學者只分析了某一種或幾種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關系,如楊曉明(2008)從學科結構角度研究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業高等教育結構之間的關系,張根文等(2006)、葉苗苗等(2011)都從學科結構角度研究安徽省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適應關系,李東航(2013)從學科結構角度研究廣西高等教育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適應性。劉瀑(2010)主要從高等教育學科專業、區域布局、層次結構角度探討了河南高等教育發展與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的耦合關系。吳會詠等(2012)從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出發,選取2001—2010年遼寧省高等教育的經管、人文、理工、農業、醫學和教育學各專業招生人數分別與一、二、三次產業產值作回歸分析發現,“三次產業產值對經管、理工和醫學類專業學生需求成正相關,對人文、農學和教育學專業學生需求成負相關,其中第二產業對經管類和醫學類學生需求最高;三次產業發展對人文類專業學生需求都很低”。
近兩年,一些學者對高等教育布局結構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如崔玉平等(2013)研究認為,“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客觀上受到行政邊界壁壘制約,要求在空間鄰近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一體化進程中探索高等教育行政區劃改革與重構”。姜巍等(2013)研究認為,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張,“高校在校生規模絕對差異不斷增大,相對省際間的差異,高等教育規模在省域內差異更為嚴重,高校集中于省會的現象十分突出,其主要原因并非區域經濟水平和交通狀況,而是師資條件和人口規模”。
少數學者如谷建春(2008)等、武凌(2010)則全面分析了現有高等教育五類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之動態關系。李帥英等(2011)研究了保定市2003年—2008年農業高等教育的類型結構、布局結構、層次結構和學科結構后認為,“保定市農業高等教育能促進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人才結構的發展”。本文作者認為,谷建春、武凌及李帥英他們的研究全面一些。
現有文獻反映出學者們對高等教育和產業結構衡量指標選擇差異,多數學者都采用單一或少數幾個指標來衡量高等教育和產業結構的發展狀態,少數學者采用較全面的指標體系開展研究。孫敬水等(2008)首先采用人力資本質量和人力資本積累能力兩個一級指標、再分別設置了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每萬人大專以上人數等9個人力資本質量和包括人均教育經費、政府教育經費占GDP比重等9個人力資本積累能力的二級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來衡量人力資本,然后研究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何菊蓮等(2013)選取包括高等教育事業費占GDP的比例、高等教育經費占全國教育經費的比例、普通高等學校生均教育經費支出、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和畢業生人數等共7個指標構成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指標體系,選取包括一二三產值及其占GDP比例、全要素生產率、萬元GDP能耗、專利發明申請受理數等共16個指標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指標體系來研究二者影響關系。本文作者認為,相對于其他研究,采用指標體系而非單一指標來衡量產業結構和教育人力資本的研究方法更全面深刻得多。
四、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影響研究總結
總之,國內外的學者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經濟產業(結構)兩者關聯的理論研究已做了較為全面深入的解析,對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都予以了充分肯定,闡明了高等教育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國外的研究中,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如他們在研究政府對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的撥款問題時,經常會涉及到高等教育(結構)與某區域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均采用了較多模型和方法,對(高等)教育各結構要素和經濟(產業)結構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工資勞動簡化法,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法,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函數,內生增長模型,回歸分析,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等方法。由于采用的樣本空間和時間跨度不盡相同,各模型也有其相對局限性,得出的結論差異較大。相對于國外研究,國內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這將是未來該領域研究亟需完善的環節。
第一,國外尤其在該領域的定量研究方面遠甚于國內,國內研究基本延續國外既有的一些計量模型和方法,極少有對模型有所改進和創新。在這一方面,國外研究起步較早,現階段也仍走在前面,與國內的差距明顯。
第二,大部分研究仍集中于對高等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研究,將高等教育結構展開為五個甚至更多維度分別與產業結構進行互動研究的較少,或是僅就高等教育的某一結構內容與產業結構進行專項分析。
第三,各實證研究中由于使用模型和數據區間樣本的不同,致使相關結論不盡相同,甚至對同一研究對象的分析結果也有明顯差異。如張立新等(2008)和齊艷紅等(2012)都以黑龍江省為對象,由于時間跨度和選取的指標體系差異,得出其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40%和1.56%的不同結論。
第四,就高等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研究成果而論,大部分研究都表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作用,提倡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些研究仍有不少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其一,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本與可持續發展的定性研究,或是從宏觀層面上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定量關系,忽略了人力資本各種因素的地區差異分析,即對地區經濟的影響程度分析。其二,在實證研究中,由于人力資本度量指標的選取以及實證研究方法差異而導致結論不盡一致,尤其是人力資本指標度量問題,大部分學者都是以教育指標代替整個人力資本水平,而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其他影響因素如健康等進行綜合估計,有以偏概全之嫌。
[1]丁繼勇.教育結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J].經濟論壇,2006(11):64-65.
[2]朱宏飛,朱曉邈,李娜.高等學校學科建設與產業結構及其調整的關系[J].農業與技術,2007(6):176-178.
[3]谷建春,陳艷.湖南省高等教育結構優化對策研究——基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視角[J].云夢學刊,2008(1):86-90.
[4]楊曉明.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業高等教育結構優化研究[J].學術交流,2008(12):307-310.
[5]劉瀑.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河南省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基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視角的分析[J].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111-115.
[6]崔玉平.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估算方法綜述[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9(1):71-78.
[7]解堊.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于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分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10):74-80.
[8]胡劍鋒,魏利軍.農村教育對浙江省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方法中模型的應用[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2007(6):670-677.
[9]趙鎮.基于丹尼森因素分析的高等教育對經濟影響研究[J].學術論壇,2008(10):191-194.
[10]孫敬水,許利利.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以浙江省為例[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8(5):777-784.
[11]張曉秋,冉茂盛,徐磊.成人高等教育對重慶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研究——基于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17-22.
[12]張芳玲.重慶市教育對經濟影響的建模分析[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4):157-160.
[13]何菊蓮,李軍,趙丹.高等教育人力資本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實證研究[J].教育與經濟,2013(2):48-55.
[14]姚益龍、林相立.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國際比較:基于多變量VAR方法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05(10):26-32.
[15]龐資勝、孫強.教育產業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J].云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1):82-84.
[16]王萍,楊璠.四川省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J].統計教育,2007(10):46-49.
[17]高耀,紀燕,方鵬.中國大陸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度因素分析與集成評估——基于2000年和2010年的橫截面數據[J].現代大學教育,2013(5):44-50.
[18]李雯,查奇芬.中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多大[J].統計與決策,2006(4):75-78.
[19]張立新,王雅林.東北三省經濟增長中高等教育貢獻率的估算[J].吉首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7):108-111.
[20]武凌.基于產業結構優化的四川省高等教育結構調整研究[D].西南交通大學,2010.
[21]陳晉玲.教育層次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2000—2011年面板數據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166-172.
[22]陳晉玲.高等教育、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VEC模型分析——基于J省的實證研究[J].教育學術月刊,2012(3):44-48.
[23]吳會詠,吳茂全,斐曉雯.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教育發展方式轉變實證分析[J].沈陽理工大學學報,2012(4):27-34.
[24]崔玉平,陳克江.區域一體化進程中高等教育行政區劃改革與重構——基于長三角高等教育協作現狀的分析[J].現代大學教育,2013(3):63-69.
[25]姜巍,高衛東,張敏.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空間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J].現代大學教育,2013(1):43-50.
G649.2;F121.3
A
1007-9106(2016)07-0049-06
*本文為四川省高等教育學會2014年課題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4SC-014)。
*
藍英(1972—),女,川北醫學院管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和衛生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