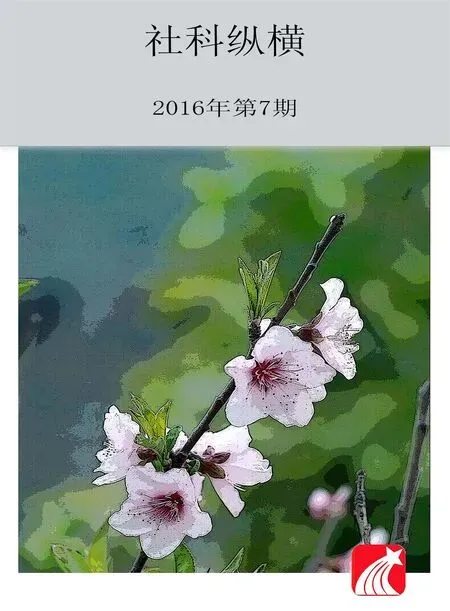中國法制史課程體例改進芻議
冀明武
(南陽理工學院 河南 南陽 473004)
中國法制史課程體例改進芻議
冀明武
(南陽理工學院河南南陽473004)
以王朝更替為線索的“斷代體例”是目前中國法制史課程內容最普遍的編排體例。從課程的教學實踐來看,它存在著論述較為膚淺、多有重復,以國家法為本位、法律視角過于狹隘等明顯缺點。而“大階段、小專題”的編排體例則可作為改進之舉,其一是以儒法思想演變為主線大階段劃分封建法,其二是以小專題的形式構建課程內容。這不僅突出了課程教學重點內容,還能宏觀闡釋整體封建法的發展脈絡。
中國法制史斷代體例大階段小專題
《中國法制史》是我國法學專業教育培養體系中的一門基礎理論學科,也是法學本科教育14門核心課程之一。從目前大多數《中國法制史》教材來看,以王朝更替為線索進行斷代體例編排幾乎成為通用的模版。“斷代體例”最大的優點就是,它可以較為全面地闡述古代中國法律制度發展演變的整體過程,能對不同朝代的法律制度做一次比較完整的宏觀描述。然而從《中國法制史》課程性質和特點來看,該體例的缺陷也是相當明顯。
一、“斷代體例”的缺陷
(一)論述膚淺,多有重復
毋庸諱言,“斷代體例”的敘述方式“很難反映法律的因循和延續性”,因為按照朝代劃分章節,不但“會造成敘述上的重復,還往往會割斷這種逐步發展和完善狀態,更難用發展變化的眼光來動態地敘述法律發展的歷史。”[1]《中國法制史》的課程內容要涵蓋新中國成立前的所有朝代,而且每個朝代的基本法律制度還都要涉及到,結果就造成了內容篇幅的龐大臃腫,目前教材一般都在40萬字以上。這種編排體例的缺陷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由于它涵蓋的范圍過于寬泛,事實上對每一個具體制度的論述只能是點到而止,往往缺乏深入全面的闡釋,使得教材內容明顯呈現出膚淺的特點,重點問題也很難講深講透。其次,它也使得課程內容存在大量重復論述的現象。客觀而言,古代社會朝代間法律制度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有些法律制度可能會延續數個甚至十幾個朝代而不改。而每一朝代都需要對其進行加以論述,因此課程內容的啰嗦重復也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比如,隋朝的《開皇律》確立了封建五刑制度,之后為所有封建王朝所沿襲。就該制度的內容來看,期間雖然也會有某些細微變化,但基本框架和理念還是被完整繼承下來的。而斷代體例下,每一朝代都對五刑制度加以闡述,這樣的重復不僅毫無意義和必要,還極易使學生淹沒浩瀚史料其中而不能把握課程最基本知識和理論。①
(二)以國家法為本位、法律視角過于狹隘
事實上,以朝代更替為劃分線索的“斷代體例”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在此思想指導下,課程內容重點集中在國家法層面之上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而對國家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形式就會有意或無意地予以忽視。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除了國家制定頒布的成文法典法之外,事實上還存在著大量的不同形式的法律,例如,禮、宗族法、鄉規民約、地方習慣、商業行會法等等。這些規范在古代社會之中對于規制人們的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方面完全發揮的是真正法律的作用。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它們不具備國家法的正式身份,在以國家法為本位的“斷代體例”下,根本沒有辦法以適合的方式對它們進行闡述和講授。這不僅會使整個課程內容選擇上的視角過于狹隘,另一重要方面,還會使得學生的視野僅僅停留在國家法這一層面上,由此很容易形成關于傳統中國社會法律現象的片面認識和推論。②
綜上所述,古代法制的發展和演變是遵循其內在規律和線索來進行的,而這種規律和線索與王朝的輪換更替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以“斷代體例”來安排章節內容的作法當然是不科學的,無疑“將削弱中國法制史學科本身的科學性”。[2]從教學效果來看,“斷代體例”對《中國法制史》的教學也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因為教學的安排一般要與課程編排體例保持一致。這就會出現按部就班向學生灌輸不同王朝的法律制度內容,這種缺乏相關的分析的單純介紹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難促使其對相關法律現象進行深入思考。

二、完善課程體例的兩點構想
(一)以儒法思想演變為主線大階段劃分封建法
學界通說認為,《中國法制史》的主干是封建法部分,具體而言,就是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由完全的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社會。在這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發展演變無疑是其中的一條主線,依據這條線索,可以將我國的封建法劃分為四大階段。③
較之“斷代體例”而言,這種大階段劃分的優勢非常明顯。首先,它可以避免課程內容啰嗦重復的弊病。就目前而言,從秦漢至清朝前半期的封建法占到課程全部內容近2/3的比重,而其中存在了大量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少有變化的法律制度。比如,宋朝的《宋刑統》基本上就是《唐律疏議》的翻版臨摹、而順治三年(1646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則完全就是“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產物。如果按照現有課程體例進行講授,必然會出現不同朝代同一法律制度的重復介紹,不僅使得學生們無法把握課程重點,還造成有限學時的浪費。相反大階段的體例劃分則可以避免該情況發生,進而提高教和學的雙重效率。
更重要的是,大階段的劃分便利于學生對封建法的整體發展脈絡有一清晰的宏觀把握。法律儒家化構成了中國封建法發展演變的一條內在主線,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呈現出一個對抗融合的宏觀圖景。具體而言,大體劃分為法家獨霸、儒家崛起、儒家一統和儒法合流的四個大階段。只有把握了這條發展主線,才能真正理解眾多獨具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比如,封建法始終面臨一個國家法與家庭倫理之間沖突的平衡難題,儒家從維護家庭內部的倫理出發,主張親親相隱的法律原則,即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藏罪行,并反對彼此相互告發的舉動。與之相反,法家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不承認親屬間相互包庇的合法性,甚至用法律手段強迫人們相互告發罪行。儒法合流前,這一難題始終不能獲得妥善解決。而儒法合流之后,封建統治者采取區分對待的辦法巧妙地加以解決,即對于十惡重罪堅持適用法家主張,實施連坐制度。而對于除此之外的犯罪行為,則采納了儒家親親相隱的法律原則。
(二)以小專題的形式構建課程內容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很多法律制度,其時間緯度可能會跨越兩個乃至數個不同的朝代。如此的法制特點,使得目前“斷代體例”編排出現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使得在任何朝代對某一法律制度的敘述往往都是片段性的,而并非是一個整體性闡釋,這對課程教學效果的提升非常不利。以封建法中的“八議”特權制度為例,該制度的淵源最早追溯到西周時期的八辟制度,在曹魏《新律》中第一次被納入律典,后《唐律疏義》對其范圍作出明確的界定和解釋,此后一直被后世王朝所承襲,一直到清末法律改革才被廢除。不難發現,這一制度的發展演變近乎貫穿了我國古代社會的始終,但是其在不同階段的地位作用并不相同,統治者對它的態度也并非始終如一。封建盛世的唐代“八議”的特權法作用獲得較好的落實,而隨著封建社會后期專制皇權的強化,它的應用范圍和落實也在不斷打折扣,最后淪落為載而不用、徒有虛名的結局。④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制度演變,以任何朝代為實例進行闡述都注定是片面的甚至是斷章取義的。而如果采取小專題的形式集中闡述“八議”制度,不僅能有效避免章節內容上講授的重復,還能全面客觀地把握和理解這一制度。
三、結語
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研讀法律的學生如果對其本國的歷史相當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的演變過程,也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對其周遭的歷史條件的依賴關系。”[3]重視歷史向來是中國人的獨特傳統,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而對本國法律史的追溯同樣由來已久,自從《漢書》首設“刑法志”后,二十四史的大多數皆專設“刑法(罰)志”之部分,集中體現出對前代法制保存的重視。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法制史》就已成為法學本科教學的重要課程,1997年又被定位成法學本科教育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該課程的內容和體例已基本完善和定型。但從目前教學實踐現狀來看,其教學體例和內容設置的問題也逐漸暴露,與新時期法學教育目標和要求間的矛盾隔閡也越來越明顯。學者張晉藩明確指出:“法制史發展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確實需要很好地總結。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總結經驗得失,要自強不息地創造新的途徑。”[4]對于一個法學和史學的交叉學科而言,“下一步怎么走”注定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其中既有學科定位、研究對象等宏觀主旨,也包含了體例編排、敘述方式等微觀細節。本文僅僅是對中法史的教學體例的改革作出一點初步的嘗試,仍有大量細節需要進一步深化完善。比如,如何實現小專題內容和部門法的有效對接,提升課程內容的當代借鑒價值和意義;如何用一條主線的方式重新劃分秦朝建立之前的法制歷史,等等。總之,如何將古代法制成功復活于當代社會、服務于當今社會,理應成為我們今天法史人不懈的追求。
注釋:
①有學者更尖銳指出,這種“單一敘述法律歷史梗概的”體例“更多的是依賴于記憶的不斷強化”,雖然它可以讓學生領略中國古代法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卻無法與他/她們在法學院中接受到的其他主流知識對接”。參見尤陳俊:“知識轉型背景下的中國法律史:從中國法學院的立場出發”,《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8年第1期。
②學者瞿同祖曾指出,研究法律僅僅限于條文是很不夠的,更要注意法律的實施問題。“條文的規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實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執行,成為具文。社會現實與法律條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導論,第2頁。對于中法史的內容編排而言,此種開放性視角的啟迪無疑是巨大的,我們不能把目光僅局限在國家法上,還應該關注其他形式的法律,如此才能最大限度還原古代法制的全貌。③類似依據某一線索來重構中國法制史教材體系的做法,已有學者進行過嘗試。比如徐祖瀾即曾以禮法關系為主線,將整個課程內容劃分為四次法制變革,分別是春秋戰國的禮法之爭、秦朝的棄禮任法、漢至明清的禮法合流、及清末的第二次禮法之爭。參見徐祖瀾:“定位與創新:中國法制史教學改革芻議”,《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④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清朝,甚至出現過直接把“八議”排除法典之外的作法。比如,1629年繼承汗位的皇太極遵循其父努爾哈赤的遺訓,強調“國家立法,不遺貴戚”的思想。在“參漢酌金”制定成文法的過程中,他雖然也仿照漢族封建法典確立了“十惡”六條,但卻始終沒有采納保護權貴特權的“八議”制度。
[1]柏樺,侯欣一.《新編中國法制史》芻議[A].載倪正茂主編.法史思辨[C].法律出版社,2004:384-385.
[2]侯欣一.有關中國法制史本科教學的幾點體會[A].法律史論集(第6卷)[C].法律出版社,2006:661.
[3][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61.
[4]張晉藩.“中國法制史學發展歷程的反思和期望[J].美中法律評論,2006(1).
G929
A
1007-9106(2016)07-0119-03
冀明武(1980—),男,法學博士,南陽理工學院講師,全國民政政策理論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