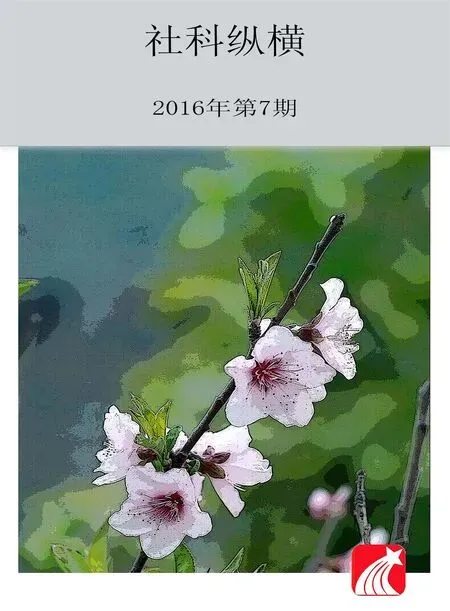試論戰后初期吉田茂內閣的對華政策
田慶立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試論戰后初期吉田茂內閣的對華政策
田慶立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天津300191)
戰后初期,日本的內外政策在追隨美國的基調上展開,尤其是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亦步亦趨。日本的對華政策在吉田茂擔任首相時期日趨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識形態因素的敵視中國的外交政策。《吉田書簡》的出臺以及日本政府與臺灣當局簽訂的《日臺和約》,是日本在冷戰體制下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的產物,阻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華外交政策的確鑿證據。
吉田茂內閣中日關系 《吉田書簡》《日臺和約》
一、吉田茂內閣敵視中國政策的出臺
戰后初期,以美國為首的盟國褫奪了日本的外交權,日本的內外政策主要基于追隨美國而展開,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亦步亦趨。日本的對華政策在吉田茂擔任首相時期日趨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識形態因素的敵視中國的外交政策。首先,追隨美國,堅持反共反華立場。1949年中國的解放戰爭即將勝利,吉田茂表示警惕和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簽訂,以及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吉田茂對此十分敏感。吉田認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其相互援助條約,實際是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并通過書信向麥克阿瑟承諾,日本支援在朝美軍。日本向美國提供橫濱和橫須賀兩港口的起重機船,以及相關的設施和勞務。[1]其次,力爭繼續維持與中國的貿易關系,這是吉田內閣對華政策的核心內容。實現貿易立國和經濟復興始終是吉田內閣追求的最大目標。吉田茂曾經指出:“對日本來說,應該恢復同中國大陸的通商貿易。日本需要輸入中國大陸的原料,中國大陸也是日本中小企業的重要市場。如果放開了這個市場,日本的復興將會更加迅速。我認為美國也不應該一味地封鎖和中國大陸的通商貿易,應該采取措施開放貿易,讓共產黨中國也得到繁榮,使中國民眾充分懂得共產主義制度是無利可圖的,只有自由貿易才能發財致富。”[2]最后,離間中蘇同盟。吉田茂主張不要一味地對中蘇采取封鎖政策,應該通過貿易手段把中國的“大陸政權”拉入到西方陣營當中,從而使中蘇同盟內部分化,以達到瓦解的目的。他指出:“現在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一起構成了共產主義軸心國家。自由主義國家應該認真考慮如何分化瓦解這兩個國家。我認為英國已經懂得了這一點。美國和其他自由主義國家也應該具體而深入地反復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在具體考慮這一問題時,應該本著這樣一個出發點:從經濟上解放中國大陸。”[3]
1951年9月4日,由美國操縱的對日和會在舊金山召開,包括日本在內的52個國家受到邀請,中國、朝鮮、蒙古、越南卻被排除在外,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和猛烈抨擊。對吉田政府而言,中日之間實際上并未結束戰爭狀態。吉田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是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日本政府最初在選擇與北京還是臺灣發展關系上,頗為躊躇。1951年10月18日,吉田在國會上就同中國締約問題的答辯充分體現了這種猶豫。他說:“目前誠如諸位所知,中共是不為美國政府所承認的國家,而國民政府又不為英國所承認。……即便(選擇哪一方的)選擇權在日本,但若加以行使,作為日本而言,也必須在認真考慮同各國的關系后再作決定。”[4](P36)同月28日,吉田又明確表示,“毋庸贅言,對于中共問題,不應拘于意識形態,而應從現實外交的視點自主作出決定,從通商貿易方面來看,可以考慮在上海設立貿易事務所。”[4](P37)吉田茂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我來說,同臺灣友好,促進彼此經濟關系,本來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進一步加深這種關系而否認北京政府。……因此,我不希望徹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權的關系惡化。”[5]
1951年10月25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在會見臺灣集團的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時說:“我國現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時機,以待日本實現獨立自主之后,研究何時同中國簽訂和約或選擇中國的哪一方問題。我國歷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只限于臺灣。”[6]同月30日,吉田在國會回答議員羽仁五郎的質詢時說:“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關于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的情形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系,不擬輕予決定。”[7]
二、《吉田書簡》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1951年12月18日,杜勒斯將日本愿意同“中華民國”締約的信件交給吉田茂,要求吉田茂簽字后寄回,后經日美雙方多次磋商,形成了所謂的《吉田書簡》,其內容為:“日本政府準備一俟法律允許就與中國國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話——締結條約,以便按照多邊條約中提出的原則,重建兩國政府間的正常關系。關于中華民國方面,這個雙邊條約的條件將適用于現在、或以后可能屬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管轄的全部領土。”書簡還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以日本為對象的軍事同盟為由,污蔑中國“正在支持日本共產黨進行旨在以暴力推翻日本的立憲制度和目前的政府的計劃”,并明確地向美國政府表示,“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締結一個雙邊條約”。[8]其中指出的與臺灣方面建立外交關系的理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目前在聯合國擁有席位及發言權與表決權,并實際上對若干領域行使著政府權力,且與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保持著外交關系”。[9]這樣日本政府即在美國的壓力下,決定同臺灣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締結所謂和平條約。吉田茂后來回憶說,作為日本政府,是想盡量防止惡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而避免過分親近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但考慮到國民黨政府是日本的主要交戰對手,現在又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尤其是為了安撫美國國會內不斷高漲的對日不信任情緒,才下定決心選擇國民黨政府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締結和平條約的對手。[10]實際上,吉田政府主要屈從于美國的壓力,明確地向美國承諾了要承認臺灣蔣介石集團并與其締結和約,還誣稱中國是“侵略者”,“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條約,從而把日本推上了同新中國完全敵對的位置上。
《吉田書簡》發表后,中國政府表示強烈反對。1952年1月23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代表中國政府聲明,認為“這一信件是戰敗后的日本反動政府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起來,對中國人民與中國領土重新準備侵略戰爭的鐵證”,是“又一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嚴重、最露骨的挑釁行為”;并指出:“日本吉田政府這一無恥行為,是和全日本愛國人民爭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戰爭狀態,恢復和平關系的愿望,絕對不能相容的。”[11](P90)
1952年4月28日,在美國的壓力下,即舊金山對日和約正式生效之日,日本吉田政府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簽訂《日臺和約》,雙方建立所謂的“外交關系”,給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日本政府事實上奉行了兩個中國政策。5月5日,周恩來在《關于美國宣布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生效的聲明》中代表中國政府嚴正聲明,中國絕對不能承認舊金山和約,堅決反對吉田政府的兩個中國政策,指出“對于公開侮辱并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由于實施這些非法條約的結果,日本就被美國拖進了與中國、蘇聯和亞洲有關國家處于公開敵對的地位,這樣便使日本在亞洲中孤立了起來。”[11](P95)這表明中國政府意識到,《日臺和約》是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的,并非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自主自愿的選擇,吉田政府是出于美國的壓力而敵視中國,是被美國“拖”進與中國為敵的境地的,因而它與美國政府是有區別的。中國政府看到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主性,所以從1952年6月開始,通過推動中日之間的民間交往和貿易往來,力圖“以民促官”,逐步達到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的目的。
1952年6月26日,吉田茂出席參議院關于“日臺和約”的辯論時,聲稱“日華條約是與臺灣政府締結的條約,它并未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權”,并解釋說《吉田書簡》的精神是:先與“現在支配臺灣、澎湖列島的政府締約”,待“中共政權改變目前做法”時,將來“再與中國結成全面的睦鄰關系”,“締結全面的和約”。[12]集中體現了吉田在處理中國問題上所體現的“兩面性”手法,即一方面與美國協調政策,視臺灣國民黨當局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為今后同中國建交埋下了伏筆。其原因在于,吉田茂充分地認識到,在冷戰的國際形勢下,除加入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中去以外別無選擇,在很大程度上要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同時為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在對華關系上又要保持一定的靈活性,搖擺與對臺關系和對華關系之間,為將來恢復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做好鋪墊。吉田認為這種戰略之所以可行主要基于三點考慮:1.對中蘇關系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認為蘇聯和中國的文明、國民性及政治狀況的差異必然導致兩國關系惡化,并力圖將中共政權從蘇聯共產主義陣營中拉出來,以改善自由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2.為保持日本的經濟發展,維持與擴大同中國大陸的關系是不可或缺的,這從戰前與中國的貿易所占較大份額中可以明顯地體現出來;3.美蘇在中國問題上的對立,給日本推行兩面政策留下了空間。
吉田政府選擇與臺灣締約,除美國政府的壓力外,也與以吉田茂為首的保守本流政治家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識密切相關。在戰后初期東西方對峙的冷戰條件下,東西方各國在處理相互關系中,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集中體現吉田茂的政治觀和反共立場的是1951年2月16日吉田茂寫給杜勒斯的一封信,內稱:“考慮到目前包括中國在內席卷亞洲大陸的共產主義勢力的進展,不但美、英、日三個國家,而且所有有關各國之間要增進對中國問題的合作,這已成為這些國家本身最緊迫的事。我們最初的工作應當從俄國人手里,把中國拉出來,使其成為自由國家陣營的伙伴。”“由于地理上相鄰、人種、語言和文化、貿易悠久的聯系,日本人發揮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適當不過的了。”[13]吉田茂處理中國問題的意圖是,在冷戰體制下兩大陣營對壘的形勢下,日本應該充當美國在亞洲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堡壘和橋梁。“從這樣的中國觀出發,當美國要求日本政府服從它的全球反共戰略,支持其把臺灣建成遠東反共基地時,吉田政府雖有過猶豫,但還是很快就同意了。戰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不論其愿意與否,都必須服從美國的對外政策,都必須以美國的意志為轉移。這也說明,一旦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調整,中日關系就必然跟著出現變化。”[14]由此看來,戰后中日關系處于非正常的敵對狀態,客觀上是在國際格局處于冷戰體制下,美國方面采取敵視中國政策的結果;主觀上看,吉田政府追隨美國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吉田書簡》及日本政府與臺灣當局簽訂的《日臺和約》,是日本在冷戰體制下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的產物,阻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尤其是在“吉田書簡”中有關“日本同中華民國的條約將適用于中華民國政府現在的統治或者今后應該劃歸其統治的一切領土”的規定,已經被國內外公認是日本推行反共、反華外交政策的確鑿證據。中日兩國意識形態的差異,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也是日本當時不愿也不能選擇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重要因素。《日臺和約》簽訂后,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正式官方關系——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起來,雙方一直通過民間交往的方式開展貿易和其它各種交流活動,《日臺和約》影響中日關系長達20年之久。
[1]袖井林二郎.吉田茂與麥克阿瑟書信往來集[M].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0:341.
[2]吉田茂大磯隨感[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9.
[3]吉田茂.十年回憶第1卷[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177-178.
[4]田中明彥.日中關系(1945—1990)[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5]吉田茂.十年回憶第3卷[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43.
[6]吳學文主編.日本外交軌跡(1945—1989)[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27.
[7]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中日關系80年之證言第14冊[M].中國臺北:臺北中央日報社出版,1974:123.
[8]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1卷1941—1960年[M].東京:原書房,1983:468.
[9]朝日新聞社編.資料·日本與中國(1945—1971)[M].東京:朝日新聞社,1972:141.
[10]吉田茂.世界與日本[M].東京:番町書房,1963:146.
[11]日本問題文件匯編(第1集)[C].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
[12]宋成有,李寒梅.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121.
[13]豬木正道.吉田茂的執政生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351.
[14]羅平漢.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對日政策與中日關系[J].北京黨史研究,1997(6).
K313.5;D821.3
A
1007-9106(2016)07-0116-03
田慶立(1975—),男,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日關系、日本外交。